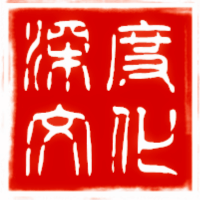1998年2月,一名警察正在黄鹤楼上执勤,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巨响,放眼望去烟尘弥漫。
据说因为发生在春节后,坊间起初便有传闻称这一事件为“烟花爆炸”,属于安全事故,但从警方的反应来看,此事绝不可能这么简单。
公安部组建了超豪华的专案组团队,我国警界赫赫有名的“刑侦八虎”一次性来了四位。专家们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现场零散的人体碎块复原成完整的遇难者遗体。

经过足足两天的努力,专案组一共拼出16具完整遗体。
此案离奇过程曲折,其戏剧化程度好似与现实脱节;即便强大的专案组仅用一个半月时间便宣告破案,但其中一些谜题却依旧没有答案。
我们不妨从头讲起。
死亡公交时值1998年情人节,不少年轻人相约逛街,这让平日里游客熙熙攘攘的黄鹤楼一带显得尤其热闹。怎料在当天10时8分,一声巨响过后,整片区域地动山摇。
人们被吓了一跳,有恰巧路过的司机好奇向远处眺望,突然感觉车子的前挡风玻璃上似乎多了什么东西,定睛一看竟是条腿。
也有顺着长江大桥遛弯的路人被巨大的震动掀倒在地,挣扎着想站起来,慌乱中摸到一些黏糊糊的东西……
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是一辆自西向东行驶且即将开上长江大桥的公交车发生爆炸,现场可谓是一片狼藉,有被当场炸碎的受害者,也有被困在车上活活烧死的,还有一些幸存者,被巨大的气浪推出车外,正躺在地上哀嚎。

当大火被扑灭后,那辆车牌号为鄂 A63538的1路公交车被烧得只剩框架,而车里到处都是受害者身体的一部分。
事发后,官方将这一事件称为“98·2·14特大爆炸案”,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安全事故,而是有人引爆炸药包导致的。
在确认这一事实后,公安部立马成立了阵容空前强大的专案组,其中包括乌国庆、高光斗、崔道植、徐利民四位在我国境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大人物,此外还有时任公安部反恐处副处长的许文荣,这说明相关部门可能曾怀疑此案是一次恐怖袭击。
警方在完成案发现场的封锁后,立马对周边群众进行走访。按说这事儿动静这么大,总该问出些有价值的线索吧?
据调查,这辆公交车虽然是个体经营,但司机罗伟和售票员彭九江都是武汉市电车公司的职员。此二人也一直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每天运营前先检查车辆状况。据他们说,当天车辆上并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因此,爆炸物一定是某位乘客中途带上车的。
然而现场的目击者,如司机、路人、清洁工等,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许多,但大多是描述场面之惨,真正有用的信息寥寥。问了一大圈,警方一无所获。
奇怪的乘客眼看调查要陷入僵局,有个参与调查的警察随口吐槽道:当时他正在黄鹤楼上执勤,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借着地动山摇,尘土沙粒噼里啪啦砸了他一脸,感觉还挺疼的。
这话令专家们灵光一闪:会不会有一些东西被炸到了很远的地方,被遗漏了?
警方旋即扩大搜索面积,果然有所收获:他们在距现场西南方31米处和东北方26米处分别发现一些碎块,经辨认,它们属于“第10号”、“第11号”两位遇难乘客。
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多伤亡者中,这二位显得最为奇怪:他们的身体受损尤其严重,胸部以下被直接炸碎。两人的残肢被炸飞到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这说明当时二人中间即是爆炸中心。
爆破分析专家高光斗确认爆炸物是硝铵炸药,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炸药,一般的小磕小碰无法将其引爆,需要雷管和引信。

经过反复测量与计算,高光斗推断出爆炸中心应该在公交车左侧倒数第二排。
此案的22名伤者中有个姓杨的年轻姑娘,她是湖北经济管理大学的学生,当天从1路车始发站上车准备返校。爆炸时,她直接被震出车窗,虽然摔得不轻,但也因此幸免于难。
被问起当时的状况,小杨立马提出一个疑点:当时,车上有个农民工模样的男子,提着一个大编织袋,里面似乎装了什么重物。他神色慌张坐立不安,看起来很反常。
更奇怪的是,与此人随行的是一个长发男子,此人白净文气,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两人身份气质相差巨大,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但彼此看起来却是十分亲密,小杨纳闷他们是怎么混到一起的。
在幸存者的帮助下,警方绘制出了当时车内乘客的位置图,经对比,小杨所说的那一对怪人恰好坐在高光斗推测出的爆炸中心的座位上,如果不出意外,此二人就是元凶。
到了这一步,调查者们脑海里不由浮现出可怕一幕:两人在挤满人的公交车里,确认没被注意到后,一人帮忙把风,另一人则慢慢蹲下,悄悄点燃引信,随后他们假装什么都没发生,静静等待死亡降临。
眼看案情有了巨大突破,可专家们再次遭遇戏剧性挫折。
寻人很快,警方就确认了绝大多数遇难者身份,唯独“第10号”、“第11号”的身份成谜。唯一的线索是,调查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张身份证残片,它的主人名叫“汤喜林”,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人。
带着这个名字,警方查遍了全武汉各个场所,终于在硚口区一家旅馆中找到了“汤喜林”的登记信息;与他一同居住的,是一个名叫“齐杏献”的男子。
警方感到更困惑了:两人开的是一间大床房——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彼此身份相差巨大,却亲密到能睡一张床?
接下来,专案组委派30多名干警奔赴江西武宁,调查汤喜林和齐杏献的身世,不料这两人居然都还活着。

汤喜林表示,几年前自己的身份证弄丢了,他猜可能是被小贼摸走了。齐杏献在武宁县一家食品加工厂上班,他告诉警方,此前曾有个叫曹军的工友,两人关系还不错,他把身份证借给对方了。怎料没多久,曹军就辞职了。
齐杏献的描述令警方振奋不已:他说曹军压根就不是个打工的料,他留着长发,像是个艺术家,会画画,写得一手好字,闲时还写两首小诗。
不过,这曹军也有奇怪之处:他不爱讲话,从不谈他的个人信息,如年龄、老家等。齐杏献说,跟他相处很不自在。
经过一番地毯式调查,警方终于在武宁县一家小旅馆里再次找到了曹军的信息。
“你说那个人啊!”提及此人时,旅店老板娘变得异常健谈,“还有那个跟他住一起的邹昌力……”
失魂的躯体曹军早就想死了。
因家境贫寒,他很早就辍学,没有学历只能进厂打工。然而,曹军很讨厌这种劳苦的现实生活,他热爱艺术,总梦想着能举办一场画展,一举成名。
在武宁县一家罐头厂里干了不到两个月,曹军就辞职了。他靠攒下来的一点积蓄在全国各地游历,当到安徽时,他被黄山的壮美景色所吸引,但美景带来的欢愉退去后,曹军突然很失落。

他总以为自己天赋异禀,能画出惊世骇俗的作品,可想靠卖画谋生的他,在路边摆摊,作品压根就无人问津。
眼看就要到奔三的年纪了却一事无成,曹军并没意识到他只做梦不愿吃苦,反而觉得老天爷瞎了眼,整个社会都在针对他。
有那么一瞬间,他想从黄山顶上跳下去,面对悬崖绝壁却怂了。
后来继续耗尽,曹军只好回到老家,找了一家小旅馆打工。
旅馆里另有一个打工者,模样邋遢,整天顶着个苦瓜脸。曹军跟他聊了一下,两人立马一见如故。
那人名叫邹昌力,总说活着没意思:“没钱,没女人,活着没劲儿。”
危险念头原来,邹昌力曾在武宁县一家钨矿当苦工,认识了同村姑娘邹道花,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情愫。后来,邹昌力去女方家里提亲,怎料自己打工攒下的钱,连彩礼的一半都不够。
没钱怎么结婚?办法倒也不是没有:邹昌力决定去女方家当“上门女婿”,彩礼钱就省了。不料邹道花嫌丢人,不拒绝,但也不答应,一直拖着。
邹昌力提了几次结婚的事儿,对方一直不给个正经话。三番五次后他烦了,干脆撒起泼来:“要是让我伤了心,就有好多人要死!”他威胁说要去炸火车,炸不了火车就炸汽车,反正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邹道花见状,赶紧好生相劝。此时她觉得对象说的是气话,没料到邹昌力却是认真的。
回到家里,老母亲也数落他,嫌弃他没本事更没出息,竟然要倒插门。母亲说,就你这样别想追人家了,人家肯定要跟别人结婚。

邹昌力一听又火了,把自己关进屋子,隔天就离家出走,去县城找了家旅馆打零工。
认识曹军后,两人一见如故,照着旅店老板娘的说法,两人天天形影不离,住一间大床房里,估计睡觉都恨不得搂在一起。殊不知在聊天中,两人对社会的怨念不断加深,很快便达成一种共识:是老天爷不让他们活,但死前一定要“快活一把”,也不能让别人太舒坦。
正巧,邹昌力在矿上干活时当过一段时间的爆破工,知道怎么引爆炸药,一个邪恶的念头便诞生了。
邪恶计划1999年2月7日,两人来到矿上,从保管员葛运春手里买走10公斤硝铵炸药,装进一只大号编织袋里,大摇大摆地带回家藏了起来。
2月10日,他们在天亮前悄悄离开打工的旅馆,带着炸药乘车来到大城市武汉。
2月14日,两人起了个大早,在1路车的始发站上了车。上车后,邹昌力选择了左侧倒数第二排单独的座位,将装有炸药的编织袋放到座位底下;曹军则坐到了最后一排。
10时8分左右,公交车即将开上长江大桥,远处黄鹤楼的拱顶依稀可见。眼看车上座无虚席,一些乘客只能站在车厢里,邹昌力觉得时候差不多了。他把编织袋从座位下拉出一点,同时向曹军示意。后者从座位上站起来,小心翼翼蹲下并点燃了引线……
警方从两人在武汉的宾馆房间里找到一截引线,在曹军于武宁的寓所中搜出一个雷管,这些足以证明专家推理的合理性。此案从发生到告破,共耗时45天。

不过话说回来,对案件而言,凶手的动机可谓至关重要,但由于曹、邹二人已经死亡,他们此举真正的目的无从得知。
犯罪心理专家认为,曹军生前创作的现代诗中,有大量提及“自杀”的字眼,这表明他有着强烈的自我毁灭倾向。结合两名凶手失败的人生,他们既想要了断,同时又想释放内心的压力,选择这种手段并不难理解。
但也有另外的解读:失败情绪只是诱因,但不是导火索;同时,对社会的愤恨可能也另有原因。
未决的谜题从二人的表现来看,他们的关系显然超出了正常“友谊”的范畴,彼此可能发展成了一对恋人。
也许正是如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样的关系很难被民众接受,两人可能在交往的不到一年时间里频频遭受非议甚至排挤。久而久之,两人的心态发生扭曲,在对人生的悲观主义情绪的加持下,他们最终选择用某种方式报复社会。
两名凶手将作案时间选在情人节当天,这足以说明问题。
究竟什么说法对,我们很难说清。
当然,相比于真相水落石出,这些并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