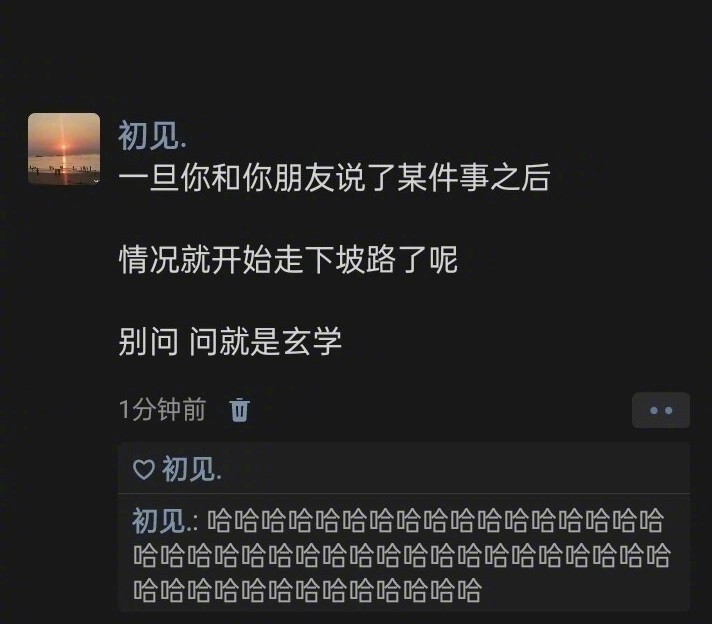《公主应未眠》
作者:苏幕幕

简介:
司妤为长公主,却也是将亡国的长公主。
江山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对她来说,只要能匡扶社稷,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更何况是委身权臣。
两年前,高盛于乱军中苦战,损兵折将、身负重伤救下公主,却只得公主遥遥一眼,只因出身微薄,升官加俸全与自己无关。
两年后,他大军压境,公主星夜来见,主动在他面前解下披风。
他想,公主婀娜,若得江山,赐公主个妃位也未尝不可。
司妤想,权宜之后,势必诛杀乱臣贼子,夷其九族。
精彩节选:
建和二年,为大兴立国第二百个年头。
春日已过,正值初夏,荒废十年后,皇室再办亲蚕礼,因皇帝年幼并无皇后,太后抱疾,大礼由长公主司妤主持。
自长生教作乱,各地争战,朝廷日益羸弱,先帝驾崩后,便只剩孤儿寡母,性命尚且难保,更不用谈皇家尊荣。
似今日这样万千仪仗的排场,似乎好久不曾有过了。
司妤身着黄罗鞠衣,从凤驾中下来,领着后妃与命妇,步行至蚕坛,六肃、三跪、三拜,再至桑田采桑,一旁随侍的乐人宫女便在此时齐唱采桑曲。
这一片采桑景与歌声振奋着人心,似乎这一年终于要风调雨顺,男耕女织、天下太平,百姓终能安居乐业。
有随同的老臣甚至低头拭泪,昔日强盛的大兴,绵延两百年,十多年动乱,如今竟还有如此盛大而又庄严的一幕,这是否是个好兆头?
繁复的亲蚕礼下午才结束,司妤在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中回宫。
她身着鞠衣,戴九花树冠,罗衣金饰下,是一张倾国倾城的美人脸。
司妤是先帝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朝霞漫天,又有倾世的美貌,自然被奉为大兴的一颗明珠,哪怕如先帝那般宠幸术士、不理朝政的人,也独爱这个长女。
但上天给她的一切尊荣,止步于两年前。
回宫,司妤换下鞠衣,换上常服,至长乐宫拜见太后,禀告亲蚕礼事宜。
太后点头,怜惜道:“这两日辛苦你了,既回宫,便好好休息吧。”
司妤道:“祭蚕神,何谈辛苦,是儿该做的。”
太后回:“愿今年年成好,百姓丰收。”
说完,太后沉默一会儿,开口道:“还有一事,高太尉已率军回京,今日傍晚能至京城外,明日进京面圣。”
司妤脸上猛地一白,整个人都崩紧起来。
高盛,他要回来了……
“是,儿知道了。”司妤用尽全身力气,在母后面前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拜别太后,离开长乐宫,司妤只觉全身无力,脚步似乎飘在云端。
五日前说他得胜,原以为回京还有几日,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若没有他,她是尊贵的大兴公主,若有他,她只是……玩物。
高盛在第二天一早进宫面圣,司妤在后宫中得知,他又被封了广平侯,兼太尉,统兵三十万。
广平侯,已是开国功勋级别的爵位,食邑四千五百户,放眼天下,能有他这等爵位的没有他这等军权,有他这军权的没有他这爵位。
但她做皇帝的弟弟有什么办法?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傀儡,京中军队和朝政,已经让高盛和他一手扶持的严尚书把持了。
司妤放下手中的书,透过漪兰殿的花窗,看向遥远的天际。
宫人来报这消息没多久,又有人过来禀报道:“公主,高太尉府上随从在殿外求见。”
司妤神色微变,转过头,她身旁宫女如缨已经开口问:“那是什么人,谁将他带到公主寝殿外的?”
那宫人连忙跪下,低头颤颤巍巍道:“他……他有太尉腰牌,说,说是太尉口令,我等……”
司妤心中了然,这些宫人,许多人曾亲眼看见高盛在未央宫大殿上杀朝臣,也知道吴贵妃就是被他缢杀,谁又敢驳他的令?
就算是她这个公主,还真敢不让那人进来不成?
她开口:“准见。”
“是。”宫人于是慌慌张张下去了,不一会儿,带来一人。
那人不过是个仆从模样,看上去也是出身行武,到了漪兰殿中,虽也算恭谨,但明显不懂进宫见贵人的规矩,脚下鞋履将地板踩得“哐哐”作响。
漪兰殿中众人听得皱起眉头,却无人敢呵斥。
隔着珠帘,那人在外向司妤见礼,然后道:“小人朱勇,为高太尉府上随从,得太尉之令,命小人进宫来请公主,请公主即刻往太尉府上一见。”
如缨脸上震怒,想发火却又不敢,只能看向司妤。
司妤心中既是屈辱,又是愤怒,忍住情绪,微恼道:“本宫今日疲惫,出宫之事,明日再说。”
“但太尉交待,此事不容有失。”朱勇说。
如缨忍不住驳斥:“公主说了,明日再说!”
朱勇也强硬道:“太尉之令,小人不敢含糊,誓死也要遵从。”
这意思,是今日要么死,要么请出司妤?
如缨怒了,恨不能当即就叫人将此人拖出去砍头。
可他们谁敢砍高盛的人?
沉默一时在殿中蔓延开来,高盛不在此,却似乎提着剑看着这里。
司妤终究答应道:“好,待我更衣便去。”
“那小人在外等候。”朱勇说。
朱勇出去,如缨已红了眼,朝司妤道:“高盛怎敢如此,对公主太不敬了!”
“正是因为如此我也无可奈何,所以他才敢如此。”司妤道。
大概,在他眼里,她早已是他的禁|脔吧。
如缨拭了拭泪水,泣声道:“那,真要去高府吗?让人知道,公主的颜面置于何地?”
司妤紧捏着手上的书,深吸一口气:“我扮作太监,随赵敬一起出宫。”赵敬是漪兰殿的管事太监。
“那……”让公主扮太监,何其委屈,可若乘着宫中舆轿出宫,谁都知道公主进了高盛府上,那更无尊严。
如缨无奈,点点头。
司妤去了头上珠钗,拆了发髻,换上小太监的衣服,在赵敬带领下出了宫。
等出了宫门,赵敬才赶紧找了辆马车,载着司妤往高府去,到了高府,又按司妤的意思,绕到了后门。
朱勇立刻下马,让人去通传,与后门的仆人道:“禀告太尉,贵人已接到了。”
那仆人随即离去,随后回来道:“太尉正在厅上宴客,请贵人先进后院休息。”
就这样,打扮成小太监模样的司妤被领进了高府后院,绕过一道□□,一条长廊,到了个寝房,下人将她领到房中,便带上门出去了。
司妤知道,这原本是开国功臣、清阳侯张淼府?,奈何张家人烟凋零,所以渐渐败落,也失了这宅子,如今竟为高盛所得。
张家大堂之上有副牌匾,上书“力挽狂澜”,为高祖皇帝御赐,表彰清阳侯曾苦战三日,救高祖突围的赫赫功绩,如今这里住的,却是高盛……
司妤在房中坐着,偶尔能听见外面的宴饮之声。
有丝竹声,有男人的笑声,大约能猜出,在外面喝酒的正是高盛手下那一干将领。
不知等了多久,到天色渐晚,夕阳西下时,外面的宴饮声停了,门外有了动静,司妤心中一紧,猛地坐直了身体,一抬眼,就见高盛从外面推门而入,魁梧的身形如山一般挡住大半的夕阳。
她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看向他。
高盛关了门,大步走到她面前,站定,将她上下打量一眼,开口道:“公主穿的这是什么?”
司妤回答:“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太尉突然约见,只能如此。”
高盛笑了一下,神色带着几分不悦:“下次还是不要了,我可不愿和阉人同床共枕。”说话间,挑起她下巴,定定瞧了一眼,审评道:“大半年不见,公主似乎更好看了,莫非这就是别人说的,长开了?”
说着露出满意而欣赏地一笑。
司妤不说话。
他直接将手往下。
司妤呼吸一窒。
转瞬间,衣衫已被扯掉,他自上而下看着她,发出一阵满足的慰叹。
看着屋顶,司妤咬着唇,想起两年前。
父皇驾崩,国师吴弼与吴贵妃弄权,意欲杀太子,扶其子上位。
为震慑朝臣,吴弼召来凉州刺史管洪,让其进京扶三皇子平州王为新帝。
生死存亡之际,舅舅给母后出主意,说吴弼虽兵多将广,但其手下大将有一人名叫高盛,骁勇无敌,若能策反高盛,则吴弼可除。
舅舅说,高盛曾在酒后放言,天下女子,不过一具娇好皮肉,他不感兴趣,所以攻城掠地得到美人,尽数分给手下将士,他觉得尚能一看的,唯有长公主。
此话大不敬,但天下大乱,朝廷连叛军都无能为力,又怎么惩治这样的悍将?
但这话却给了舅舅灵感,他提议,由她这个长公主亲自去见高盛,赐他骠骑将军大印,说服高盛反吴弼,扶太子登基。
那时她才十七,忐忑而又无奈地拿着大印去了,说是“赐”,其实是“献”,将大印呈给他,同时献出的,也有自己。
高盛答应了,对她也并没有一点客气。
那一晚,她大概会记一辈子吧。
做了十七年公主,尊贵无比,高高在上,但那一刻,她只是一具任人摆布、供人随意发泄的皮肉。
有一度,她甚至觉得自己活不到明天。
后来她自然活下来了,被抬回皇宫,也在那一日,高盛杀了管洪,收编管洪的队伍,进宫缢杀吴贵妃,处死吴弼,软禁平州王,扶了她弟弟做新帝。
他做得干脆果断,时至今日,她也不知舅舅这主意是好是坏,是不是他们此举,反而葬送了大兴的江山,因为高盛显然比管洪更可怕。
管洪死了,高盛却把控了京师,再无退出的迹象,而她,也成了他的所有物。
在那一晚后,京师局面控制,他便时常出入皇宫,向皇帝觐见后便要转道漪兰殿,在她寝宫待上大半日或是一整夜才走,而今日这番,直接让人去叫她出来,还是第一次。
这不是最后一次,也不是最过分的,这只是一个信号,告诉她,平叛得胜归来的高盛,日后会更加猖狂。
翌日清晨,高盛才放司妤离开,并同她交待,以后不许作这副打扮,他不喜欢。
司妤想为自己遮上最后一块遮羞布,迟疑半晌,却也没能同他辩驳,最后沉默离开。
仍是穿着那身太监服,拖着无力又酸痛的身躯往高府后门走,她深深埋着头,狼狈得像个被召进府中陪侍的妓女。
妓女尚且能光明正大,她连妓女也不如。
行至屋外几株花树旁,迎面撞见一人,白面有须,紫袍玉带,由仆从领着往这边来,抬眼一看,似乎是尚书令严淮。
严淮是先帝时旧臣,当时官至给事中,司妤也曾见过,如今在此地再见,既是难堪,又是尴尬,连忙垂下头,连步子都迈得急了一些,唯恐他认出自己,恨不能化为无形,飞出院墙外。
严淮却已朝她看来,再靠近几步,神色一愣,显然认出了她,连忙抬手欲行礼,到胸口,却又迟疑一番,此时她已随朱勇往这边而来,朱勇朝他道:“严令君。”
严淮连忙退让,避至一旁,让他们先行。
司妤仍旧垂着头,跟着朱勇往后门而去。
司妤能感觉到背后的人久久看着自己,随后隐隐听见一阵叹息声。
她心中一怔,忍不住回过头,就见严淮神色无奈又悲戚地摇摇头,又往高盛房中而去。
似乎,他也不忍见堂堂公主,却被召进府陪侍。
直到严淮背影远去她才回头,继续往前去,到后门,乘上了回宫的马车。
至宫中,漪兰殿内已弥漫着药味。
司妤一边进浴房,一边由人脱下小太监的衣服,步入浴池中,宫女已经端来了那碗药汁。
她接过药碗,别无二话,一口饮尽。
这是一碗宫中秘药,用来让人避孕的,她从两年前就开始服用。
如果有一日,她怀了那人的骨肉,生下他的孽种,她无法想象自己要怎么面对那孽种,又如何处置孽种。
所以不发生这样的意外,是唯一的选择。
宫女马上递过来饴糖,让她含服,她摇了摇头。
药很苦,一口气灌入空空如也的腹中,也很难受,几乎要忍不住吐出来。
但她要自己记住这苦的滋味,要加剧身体上的痛楚,好让自己时时清醒,以免有一日失去了斗志,忘却不甘,真的做一个任人摆布的玩物。
皇上今年满了十三,还有五年他才十八,如果他争气,是个睿智的明君,也许只用十六岁……
到那时,皇帝亲政,也许将有力量诛杀高盛这样的佞臣。
所以,她至少还要熬三年,也许是五年……
如此想着,她问:“皇上在做什么,知道吗?”
如缨回道:“皇上昨夜偶感风寒,有些不适,似乎被太后娘娘接去了长乐宫。”
司妤一惊,忙问:“严重吗?有没有让太医看过?”
“看过,应是不严重,是坐着肩舆去的。”如缨说。
司妤松一口气。
皇上不能出事,他是她与太后的倚仗,若皇上出事,还不知这江山会怎样。
终究是不放心,她道:“待会儿我去长乐宫看看。”
如缨担心:“公主不休息一会儿?”
她摇摇头。
才经历完昨夜,她怎么能睡得着呢?她就盼着有点什么事,好冲淡自己对昨夜的记忆。
待沐浴完,她就梳妆打扮,去了长乐宫太后寝殿。
皇上果然在此处,盘腿坐在榻上,正在喝汤膳,司妤向他请安。
皇上连忙叫她起身,看着她,欲言又止。
他已十三岁,知晓男女之事,却又知道得不多,心里知道他们这几人的命是由姐姐的牺牲保全的,也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牺牲。今日一早,他就听闻高盛竟胆大包天,叫皇姐这个长公主出宫去,皇姐又能如何,只能出宫,到现在才归。
他是皇帝,原本应该号令天下、给母亲和姐姐无上尊荣的。
此刻他怜惜皇姐,却不知说什么,司妤也看出幼弟的局促,主动问他:“听闻皇上偶感风寒,现在怎么样了?”
皇上回:“好多了。”
一旁太后也说:“一早咳嗽,他还坐那肩舆吹了风,好在到我这里喝了姜汤便好多了,鸡汤也是温补之药,再喝一碗休息两日也就好了。”
这一边皇上已喝完了面前的鸡汤,太后让人送来果子给他,又给司妤送了一份。
司妤看着面前的五色果子,却是一口也吃不下,看看弟弟,又看看母后,终于开口道:“母后,皇上若好了许多,就让他回未央宫读书吧。”
太后道:“但一早已让先生回去了。”
司妤立刻道:“就算先生回去,也可再召,先生一时半会儿来不了,皇上也可自行温书,总比在这儿好。”
太后满脸心疼:“皇上还咳呢,读书也不在乎这一日两日,万一熬坏了身子……”
“母后,我们等得,大兴的江山可等不得,京中的高盛,京外的各方刺史,还有四处作乱的长生教,这些都等着皇上去收服、去平定,母后莫非想皇上做大兴的亡国之君?”
太后被她这话问得陡然一震,半晌才回过神,下意识反驳道:“你这话也太不该了,这不是诅咒我大兴么,那又何至于?”
司妤深吸一口气,无从解释心中的难受。
怎么会何至于,当一个小小刺史敢盘踞京城、不将皇帝放在眼里;当叛军打到京城,朝廷无力抵抗;当皇室的亲蚕礼,连仪仗队都凑不齐,这一切离亡国还远么?
这时皇上开口道:“皇姐说的是,是朕不该,朕这就回去温书,并召先生进宫替朕讲课。”
司妤欣慰地看向他:“皇上,姐姐只是不想大兴两百年基业,毁在我们手上。”
皇上点点头,放下果子,揭了腿上的薄毯,下榻向太后辞别。
太后叹息一声:“那你便去吧,晚上记得喝药。”
“是,孩儿去了。”皇上离开长乐宫。
太后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司妤也看着。
她自然怜惜弟弟,可她也知,有些能人悍将,在治世便是能臣,在君主羸弱的乱世,那便会成为大奸臣。
譬如高盛,明里说是护卫皇上,带兵剿灭长生教,平定了歧州,事实也是趁机把控兵权,初入京时他尚且听命于管洪,两年之后的今年,京城已无人能遏制他。
谁能知道他对她的污辱只是猖狂忘形,还是真的已视司姓皇室如无物?
两日后,宫中举办晚宴,犒赏高盛及此仗立功的凉州军士。
犒赏得胜武将,是大兴旧例,但至先帝一朝,因鲜少有胜仗,宫中已多年不曾举办了,如今高盛得胜,是由尚书府提议的,宫中照办。
司妤猜测,高盛此举,是为增加自己的荣耀与威信,同时也昭告天下,自己是天子近臣。
皇帝年幼,她与太后也会出席。
晚宴当日,司妤着五彩烟霞般的大袖披衫,梳着端庄宽广的云髻,遍插六对金银镶宝石钗子,一如往日,华美如仙娥。
她到时,武将们已坐在下方桌案旁,见她来,齐道“公主千岁”,尽管她不曾移目,却也知道所有人都低着头,独有一人目光肆意看着她。
那自然是高盛。
她于皇帝宝座下首坐下,正好与高盛相对。
高盛的目光,有一种把玩与欣赏,理所当然,她本就是倾城之姿,盛妆之下,没有人不会惊艳。只是旁人不敢表露,他却敢。
她到没一会儿,太后与皇帝便一起到了,所有人一齐离座,向皇帝见礼。
十三岁的小皇帝在龙椅上正襟危坐,开口道:“众卿平身,赐座。”
待重新入席,皇帝道:“此番剿灭歧州叛乱,高太尉与众将士劳苦功高,今日朕设此宴,以嘉奖诸位忠肝义胆,奋勇卫国。”
高盛道:“身为大兴子民,抵御敌匪,保护京师,是臣等职责。”
皇帝道:“诸位杯中之酒,为宫廷应功酒,名曰,‘气吞山河’,先帝朝时所酿,今夜众爱卿肆意畅饮,尽兴而归。”
众将士齐道“谢皇上”,然后便开始宴饮,俨然一副君臣同欢模样。
看着这场景,会让人恍惚觉得安宁盛世,歌舞升平。
然九州之内,长生教仍四处作乱,各地军阀各自为政,大小争战不停,可谓民不聊生。
高盛有万夫莫挡之勇,他是那个荡平天下的能臣么?
司妤抿了一口酒,见皇帝也饮下酒,明显不习惯,只是微微皱眉。
这酒是犒劳武将的,性烈,皇帝也才刚学饮酒,不适也要忍着。
歌舞起,没一会儿,高盛杯中酒尽,一旁宫女要替他斟酒,他却示意宫女停下,看向司妤,开口道:“公主??”
司妤没想到他会提起自己,只能将目光投向他,正色道:“高太尉。”
高盛脸上带着几分轻佻的笑:“公主自进大殿,便不曾正眼看过微臣,莫非是嫌微臣行武之人,粗鄙不堪?”
司妤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却也能从眼角余光中瞥见他身旁的宣武将军卢慈微低了头,嘴角浮起一抹笑。
她与高盛的关系,说隐秘也隐秘,从未公之于众;说不隐秘也不隐秘,因为许多人都知道高盛为何倒戈,也知道高盛常宿宫廷。
卢慈是高盛手下一名悍将,对其忠贞不二,当然知道这事。在他眼里,这便是高盛与长公主之间的调情。
但司妤却只觉双颊滚烫,心中梗塞。
她依然只能装模作样,温声回道:“自然未有此事,太尉多虑了。”
高盛便道:“既如此,那公主可否替臣斟一杯酒,好让臣沾一沾天家贵气?”
所有人都看向这边,原有的喧哗此时都安静了几分。
他是真的不准备给她留一丝体面。
他要拿她当玩物,也要让所有人知道她是他的玩物。
严淮坐在司妤旁边,此时开口道:“子阳说笑了,公主金尊玉贵,哪里能斟酒,不若我给你斟酒,你我二人喝一杯吧。”
说着要起身,高盛摆手,“你也知公主金尊玉贵,你可不能和公主比。”说着看向司妤,脸上那抹轻佻没了,换来一阵凝视,带着压迫,似乎这杯酒,她非斟不可。
“高太尉就算为得胜之师,也是大兴臣子,公主皇室血亲,焉有替臣子斟酒之理?我看太尉未免太狂妄了些。”
说话的正是郭循,也是太后之兄,司妤的舅舅,皇帝登基后,领了郎中令之职,统管宫廷禁卫。
此时高盛还未说话,他身旁的卢慈便道:“好一个‘得胜之师’,轻飘飘四个字,就掩过了我们流过的血,死过的弟兄,郭郎中倒是不狂妄,怎不见你带兵平叛?”
此话一出,满座西凉武人皆笑。
郭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先帝朝时,因先帝宠信吴弼与吴贵妃,封吴弼为大司空,领郎中令,郭循当时为大鸿胪,掌外宾事宜,不领兵权。
到新帝登基,高盛入京,太后趁机封郭循为郎中令,总算将禁卫军权捏在了自己手里,但如此仓促升任的郎中令,自然比不过场上这些十几岁便在战场厮杀的武将。
郭循被笑话,冷声一哼,不屑道:“武夫之见,怕是在足下眼里,世人只有拳脚之强弱,诗书礼义都不放在眼里,敢问,这与牲畜何异?”
说话间,自然带着一种世家大族的傲气。
卢慈与高盛为同乡,同是西凉边境草莽出身,此番被嘲笑不懂诗书礼义,先是大怒,面红耳赤,随后大笑,回道:“要不然,明日郭郎中便去商州念诗好了,那商州剌史不听调令,拥兵自重,我倒要看看,郭郎中如何将他给念死了!”
场上又是一阵哄笑。
郭循越发生怒,却无以言对,不禁斥声道:“武夫,草莽!难怪狂妄自大,不尊天子,我不与你们动嘴!”
此时高盛一把抽出身旁佩刀,厉声道:“我等草莽也不会动嘴,只会动刀!”
郭循看着那刀,一动未动,倒是小皇帝没料到有此一出,吓得往后一躲。
郭循怒目而视:“太尉在殿前动刀,惊扰君上,是何意思?”
一旁严淮道:“二位息怒息怒,子阳,大殿之上,你这是做什么?”
此时太后道:“喜庆日子,就不要争论了,妤儿,高盛为有功之臣,你便替他将酒满上吧。”
事已至此,剑拔弩张,谁也不知高盛还会干出什么事来,有母后发话,司妤也自知皇室无权,无法抗拒,只好起身去给高盛斟酒。
郭循冷哼一声,拍案而起,转身气冲冲出了大殿,就此退席。
司妤看看离去的舅舅,无可奈何,只能到高盛身侧,蹲下身,执起酒壶替他倒酒。
没想到此时,高盛放在桌下的手竟探进了她裙下。
她不由一震,既悲又愤,脸欲滴血,忍不住将茶壶捏紧,迅速替他将酒壶倒满,起身回席。
直到她坐下,只见对面的高盛施施然拿起方才探入她裙底的手,意味深长捻了捻手指,随后才拿起酒杯,看着她,怡然自得地饮了一口酒。
他人没注意这其中猥|亵之意,司妤却是再清楚不过,移开目光,不再看他。
在场的确都是一群莽汉,喝起酒来便失了礼数,声如洪钟,大吆小喝,太后与皇上在酒过三巡便离席了,司妤也一同离席,只留文臣武将仍在宴饮。
殿外凉风吹得人清醒,但哪怕清醒,司妤也不知日后该如何是好。
她想,高盛今日此举,是为立威,从此他在朝中威信更上一层;而如果她不斟那杯酒,又会怎样?
他真会动刀杀舅舅吗?
司妤不知道,尽管高盛若杀了舅舅,势必惹怒朝中公卿,但她不敢去赌,若失了舅舅,他们便彻底没人了。
她往漪兰殿去,没走几步,有宫人过来,呈给她一张纸条,说道:“公主,郭郎中让呈给公主的。”
司妤接过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字:忍。
这也是他们之前所想的,先让高盛以朝廷名义平乱,等到皇帝长大亲政,再将其赐死。
这其中最需要忍的便是她。
她撕了纸条,攥在手中,沉默着回了寝宫。
时候已不早,宫女替她拆下发髻钗环,还在沐浴,便听外面有异样动静,只听宫女声如蚊呐道:“太尉,公主还在沐浴。”
这话音还没落下,高盛便挑帘进来了。
一旁宫女都吓了一跳。
司妤保持着平静,开口道:“你们先下去吧。”
倒不是她冷静,而是她不想此时的不堪被更多人看到。
宫女退下了,高盛走到浴池边来,蹲下身抬起她下巴:“还是第一次看见公主沐浴,可真美。”
“殿上那么多人,太尉却要当着他们的面差使我、来后宫,太尉是存心作践我么?”她问。
高盛反问:“这么说,做我的女人,是被作践?”
司妤既然要忍,就不至于惹恼他,便攀上他的脖子,笑道:“太尉何止手中之刀利,嘴也利,我说不过太尉。”
“是吗?”高盛笑道:“我最利的,可不是这两样。”说完,将她从水中捞了起来。
他一开始,便是无休无止,毫无顾忌,司妤几乎要将嘴唇咬破。
好在比之前高府那晚好,夜至三更,他停了下来,揉着她身躯,满意道:“公主封号永宁?”
“是,父皇所封。”司妤说。
高盛看着她道:“太过平庸,我记得以前还有个永宁王,要我说,公主这般姿容,该取个,比如……倾城,还有些什么词,‘如花似玉’?对,似玉……”
他抚着她柔嫩的肌肤,说道:“我若为帝,就封你个玉妃。”
司妤本已疲惫至极,春泥一般躺在他怀中,此时一听这话,不由一震。
高盛之前喝了不少酒,此时又是纵欲之后,得意忘形,所以说了这话,但他的手就覆在她腰上,自然也能感觉到她刚才的变化。
她也猜到他大概觉察到了,便抬头嘟唇,不悦道:“怎么是妃,不是皇后?这么说,太尉有了我,还想着其他女子?”
高盛笑了,“倒还没见到比公主美貌的女子。”
司妤道:“我若是为帝,就给太尉取封号叫……巴蛇。”
高盛好奇:“巴蛇,那是什么?不像什么好话。”
司妤回答:“怎么不是好话,巴蛇为上古传说之蛇,青黑色,身形巨大,能吞象,力大无穷……而且,蛇好淫。”
高盛显然很受用,大笑,一把掀了她被子,覆上她身道:“它不淫,生来做什么?”
她似乎打消了他的疑虑,但也勾起了他的欲望。
只是她已然在心里确认,高盛此人,就没准备做大兴的忠臣,他的确早有异心,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篡位。
他们在等皇帝亲政,但他们忘了,高盛可不傻,他怎么会让皇帝亲政?
翌日一早,高盛离去,司妤便想去见太后,思虑片刻,又觉得太后少谋断,和她商议也是无用,反而容易走漏消息,还不如直接同舅舅商议。
于是下令召舅舅入宫。
郭循入宫,司妤屏退左右,与郭循道:“舅舅,我确信,高盛有不臣之心。”
郭循倒不算太震惊,问:“如何?”
司妤神色微敛,而后才轻声道:“昨夜他又到了我这里,得意之时,他说,他若为帝,要封我为妃,竟还真替我想封号……舅舅,可想而知,他有谋逆之心,而非做大兴的忠臣。”
郭循神色凝重起来,点头道:“从他当初自封太尉,大权独揽,到昨日大殿上的狂妄,有此心,也不奇怪。”
司妤连忙问:“那舅舅觉得眼下我们该如何?”
郭循满面愁容,不出声。
司妤急道:“总不能一直等着,等他权势日益壮大,那不是坐以待毙?那吴弼与吴贵妃虽说也是失道寡助,但他们的下场,也许就是我们的明日!”
郭循也是一惊,起身踱了几步,沉思道:“昔日霍光以臣子身份,先立刘贺为帝,再废其帝位,改立刘询,如今高盛杀了吴氏一族,软禁着平州王,以后说不定也会先杀我等,废皇帝,改立平州王!”
“若等那时,我们更无力量与他抗衡。”司妤说。
随后她恨声道:“昨日他进漪兰殿,我真想唤侍卫来将他乱刀砍死,可他武艺高强,普通人哪里是他对手!”
郭循突然停了踱步:“我倒想起一人。”
“谁?”
“左中郎将吕骞!”
司妤想了想:“吕骞?舅舅上次好像说过,他与吴弼交好,并不服您?”
郭循道:“他的确不喜欢我,可他更恨高盛,此人武艺高强,手下也有一众悍将,我回去后寻机与他交谈,或许能说服他出手对付高盛。”
司妤听出了其中意思,问:“舅舅是想,借刀杀人?”
郭循未料司妤反应这么快,点头道:“正是,此人曾在青阳山中徒手打死猛虎,若好好筹谋,寻得机会,一定能手刃逆贼!”
司妤不曾与吕骞接触,不知他性情,但她相信舅舅,便正色道:“若舅舅觉得可行,那一定可行,此事就拜托舅舅了,若有用得上我的地方,舅舅尽管说。
“另外,今日这番话,我只与舅舅说过,母后与皇上那里我不准备提,母后胆怯,皇上年幼,不一定藏得住事。舅舅也须谨慎,若让高盛知道我们有此心,一定不会放过,他杀起人来可毫不手软。”
郭循立刻道:“我自明白,此事我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我出去了,你便在宫中等我的消息。”
司妤道“好”,目送郭循离开。
看着舅舅去远的身影,她在心中祈祷但愿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