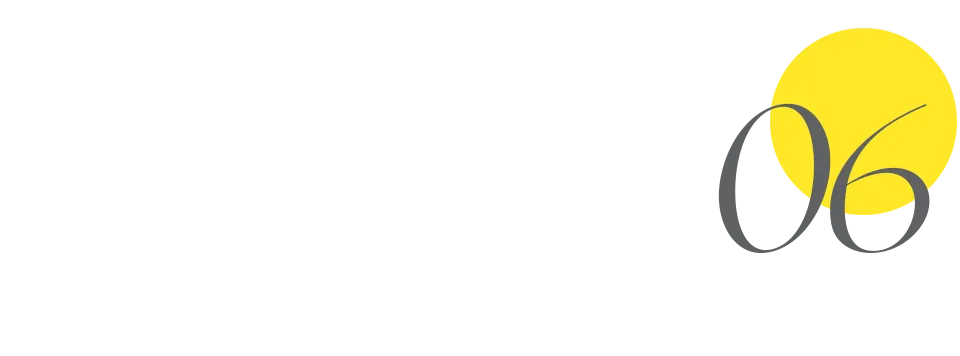上个世纪40年代,杭州有两次大型画展,主办方都向一个画家发出邀请,希望能展出他的作品。
这个画家也没有拒绝,每次都挑选了几幅作品参展。奇葩的是,两次参展作品都被偷了,画家得知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暗自高兴,因为连小偷都喜欢他的画。而他接下来的做法,更是叫人大跌眼镜。他在报纸上公开表示,偷画不算偷,爱画者大概算是知己,可直接上门,免费题款。这则公告一出,人们惊讶不已,而他,依旧安安静静做自己,画可爱的画,做可爱的人,过充满趣味的生活。这位画家,就是丰子恺。他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他还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清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看这世间,大多可爱。


丰子恺,原名丰润,又名丰仁。1898年11月出生于浙江石门镇。丰家是当地大户,家里开有染坊,所以丰子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颜色的世界里。他的父亲,对家族生意不感兴趣,一心读书科举,1902年,终于考上了举人,可是母亲去世,他丁忧在家,三年之后,丁忧结束,延续了千年的科举也废除了。没办法,只能在家乡开办私塾,丰子恺就是他的第一个学生。不到六岁,丰子恺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了一生的学习,从《三字经》到《千家诗》。在父亲为他选择的课本上,每一页都有一幅配图,丰子恺对这些图画比对文字更感兴趣,但他觉得黑白的图不太好看,想给它上点颜色,就从家里的染坊里拿来颜料,认真地给画上色。薄薄的纸张,被颜料浸透着,父亲见了,一顿责骂。但丰子恺并没有被吓到,那天晚上,他拿着颜料,继续给画上色。有一次,父亲晒书,丰子恺在父亲的藏书里看到一本“图画书”,就是《芥子园画谱》。9岁的丰子恺,如获至宝,他照着书中的画临摹、学习,画得越来越好,画得越来越像。他的画,成了家里独一无二的装饰品,被挂在卧室,他画的灶神被贴在厨房。后来,父亲因病去世,丰子恺被送去了另一个私塾,正式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1910年,石门镇推行新式教育,私塾变为学堂,课程设置更加现代化,还增加了体育、音乐等课程。但丰子恺最喜欢的,依然是画画。他逃避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课程,一门心思投入自己喜欢的画画和做泥塑,自己给泥塑上色。然而,比起泥塑,他最喜欢的还是画画,学校里,老师不准画,他就偷偷地画,有些书不准看,他就偷偷地看。画着画着,他开始给同学们画像。后来,老师发现了,画得真好,就叫他照着孔子的像画一张更大的,挂在学校供学生膜拜。此后,他获得了一个“小画家”的绰号。大多数人小时候的梦想,都很简单,不是房子车子票子,不是名利富贵,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大多数人长大了,就忘了。他们的心变得复杂,生活也就变得复杂了。

丰子恺慢慢长大,丰家渐渐没落,不再如之前那般受人尊敬。丰子恺的母亲,像许多传统的父母一样,希望儿子能靠读书出人头地,博取功名。然而,科举没了,怎么办呢?丰子恺成绩优秀,可选择的学校和专业都很多,但母亲和老师商量了一阵,觉得教书胜过其他职业,就让丰子恺报考师范学校。多年后,丰子恺感叹:“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我的母亲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说师范好,所以我就进了这里。”1914年,16岁的丰子恺,带着母亲的殷切希望,搭上了前往杭州的船只,成了师范学校的一名寄宿生。他不喜欢学校的那些规矩和限制,但他默默地忍受着,努力学习,堪称学习模范。初冬的一天,课都上完了,国文老师看见丰子恺还在教室里学习,很是赞赏。师生长谈,老师越发欣赏这个学生,甚至还给他取了一个笔名:“子恺”,意思是安乐的人。从此,丰润成了丰子恺。

此时的丰子恺,学习刻苦,名列前茅,又听话,就是老师眼中的模范生。但丰子恺有一个同学,名叫杨伯豪,此人特立独行,鄙视学校繁琐的规章制度,更是时常打破这些规矩,他对同学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一群鸡或鸭。朝晨放出场,夜里关进笼。”这样的人,与规矩、听话的丰子恺,完全就是两类人。但丰子恺喜欢这个同学,喜欢他的独立自由,喜欢他的特立独行,得知丰子恺来师范,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遵母命,杨伯豪痛斥丰子恺,只知道服从母命,完全不顾自己的内心和理想。杨伯豪不遵守学校规矩,不想上的课,坚决不上,而是看自己喜欢的书,老师给他记过处分,他不在意,甚至不屑于用生病之类的借口请假。最后,全校盛传,杨伯豪神(经)(病)了。杨伯豪也因不堪忍受而离开了。人生就是一场旅程,大多数人都只是路人,但有些人来了,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光,让你看到一些从前不曾看过的东西。

和杨伯豪的交往,让丰子恺看到了人生不一样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不应该总是忍受,而是反抗。但此时的丰子恺,还没找到反抗的力量,他郁闷、痛苦,却不得不继续忍受。杨伯豪的话,时刻在他耳边回响,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屈服,要反抗,多年后,丰子恺回忆那种震动,他说:“他的话刺激了我,使我突然悟到自己,最初是惊悟自己的态度的确不诚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觉得刚才对他夸耀我的应试等第,何等可耻。”他感到,学校的教育只考虑将来怎样谋生,是一种明显的功利主义。那样的人生,一眼就看到头了,他不愿意那样过完一生。但人生该怎样呢?该做什么呢?他感到恐惧和迷茫,面对未来不知所措。就在他人生最困惑的时候,学校新的音乐老师和美术老师,再一次给丰子恺的人生带来光。这位老师,就是李叔同。

在李叔同的教导下,丰子恺进步神速,李叔同对他说:“你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任教,没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以此为业。”这几句话,影响了丰子恺的一生:“当晚李先生的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这一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几十年来一直未变。”因为李叔同,迷茫中的丰子恺,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如同在寒冷的冬夜,感受到了灯塔的引导。从此,丰子恺将更多的精力都放到了绘画上。人生很长,在这条很长很长的道路上,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方向,是很难的。但一个人一旦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能忍受世界的很多东西。


我常觉得,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唤醒人的灵魂,让人更好的靠近自己,走进真正的自己。因为李叔同,丰子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他要画画,当艺术家。李叔同告诉他,要善于观察,要多观察。丰子恺就去学,他常常因为痴迷于观察、描绘颜面和姿势,忘了周围的一切,甚至有时候还在无意中冒犯了别人。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他傻了。但丰子恺并不在意,他观察路上的行人,观察卖东西的小贩,观察工作的售票员,他在寻常处收集人生的美好。他说:“时人不识予心乐。自己快乐,自己知道就行。”1918年,李叔同落发为僧,法号弘一。出家前,李叔同还告诫丰子恺:“你在艺术技艺上已大有长进,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最后要告诉你的,是一个比艺术技巧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颗艺术家必须拥有的艺术心灵。”他解释说:“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的人,虽然未尝描画吟诗,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为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而没有艺术之心,其人不啻一架无情的机械了。”1919年,丰子恺毕业了,他想继续深造,学习画画。可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响亮的一巴掌。早在几年前,家里就给他定了一门婚事,毕业前夕,就在母亲的安排下完婚了。眼看家中经济日益困难,他还有妻子需要照顾。一句话,再也不能随心所欲了。但他依旧想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点可能,所以,他拒绝了家乡稳定的工作,远赴上海,希望能找到一条脱离困境的路。人生很多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我们就总有抵达的可能。


来到上海,他一边教书,一边画画。有一次,在一堂写生课上,他把一个青皮橘子放在桌子上,让学生照着画。可是突然,他感觉自己就是这一个青皮橘子,半生半熟,带着青皮被卖掉,给人家当作学画的标本。他决定,无论多么艰难,都要出国留学。于是,他东拼西凑,到处借钱,终于凑了一笔钱,飘洋过海,前往东京。在东京的前五个月,他上午学画,下午学日语。后五个月,他放弃了正规的日语学习,转而学习音乐和英语。当然,画画是不变的。他常常请假,参观美术展览,看演出,在图书馆大量阅读。他喜欢逛二手书店,有一次,他看到著名插画家竹久梦二的作品,西方的构图,东方的趣味,简练,优美。恰如竹久梦二说的:“从我记事起,我渴望的世界可以不‘真’也可以不‘好’,但一定要‘美’。”由于没钱,丰子恺的留洋生活,也早早地结束了,前后不到一年。回国后,他继续当老师,一边还债,一边养家糊口,此时的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多挣一点,他同时在两所学校兼课。后来,他应夏丏尊之邀,前往春晖中学担任老师。丰子恺住在白马湖边的一个院子里,他在院子墙边种了一棵杨柳树,便将自己的居所称为“小杨柳居”。这颗杨柳,成了他画中经常出现的景物,婀娜多姿,诗人俞平伯开玩笑说丰子恺是“丰柳燕”。他和朋友们就在这里饮酒聚会,丰子恺和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经常在白马湖相聚,有人戏称“白马湖四友”。这四位,都爱酒,而且最爱绍兴花雕。经常买来一壶酒,边喝酒,边聊天。白马湖的冬夜,松涛如吼。感受过自由,再回到讲台,板起脸来做先生,对丰子恺来说,是一件挺难受的事情,因此,他经常画画。他经常将自己喜欢的古诗词,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说这是“翻译”,有一回,夏丏尊看了丰子恺的“翻译”画,立刻被吸引了,高兴地说:“好!”

随后,朱自清也发现了,有一回,丰子恺和朱自清共赏画册,朱自清说:“你将来也印一本。”朱自清没想到的是,他这句话,就是丰子恺的将来。此时的丰子恺,不停地画,他的画展现在一些杂志上,郑振铎见了,很是喜欢,他说:“子恺不惟复写那首古词的情调而已,直已把它化成一幅更足迷人的仙境图了。”

1925年,郑振铎请丰子恺为《文学周报》定期供稿。郑振铎眼光独到,他选来做插画的作品,风格更加独特,他将其称为“子恺漫画”。从此,漫画一词,渐渐普及开来。丰子恺的画,也越来越动人,朱自清说:“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可是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看了丰子恺的画,觉得很奇怪,因为丰子恺画中的人,有些没有眼睛,有些四个手指头粘在一起。还有人评论说:丰子恺“不要脸”。对于这些人,丰子恺也不理会,不解释,他继续读自己的诗,画自己的画。他画《无言独上西楼》,画上一个穿着大褂的现代人,有人说:“这人是李后主,应该穿古装。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丰子恺说:“我不是作历史画,也不为李后主词作插图,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体感的。”

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得有趣味,人的生活,应该由趣味维持,否则,就变成了单纯的生存了。所以,他喜欢孩子们,因为孩子们的生活,完全以趣味为原动力。孩子做什么,都是因为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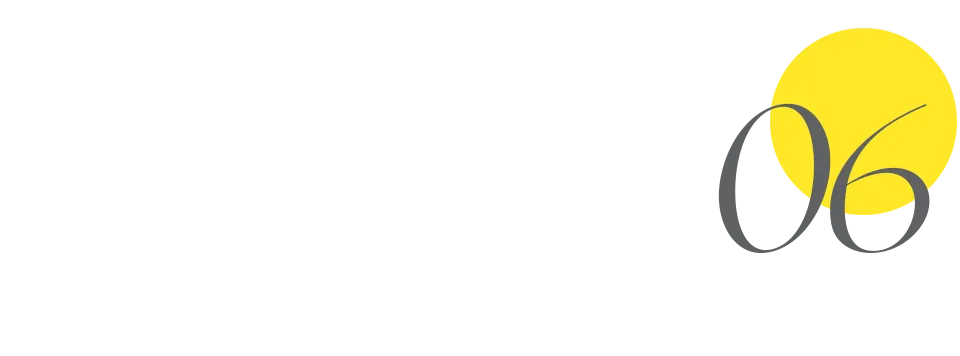
1927年,丰子恺年近30岁。岁月流逝,社会浮躁,丰子恺觉得自己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情感上,都和童真渐行渐远。“人生好比喝酒,一岁喝一杯,两岁喝两杯,三岁喝三杯……越喝越醉,越喝越痴、越迷,终而至于越糊涂,麻木若死尸。”已经三十岁的丰子恺,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他意气消沉,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彼时,世界一片混乱,而生命,又在快速流逝,最终的结果都是死亡,生存的欢乐和悲哀之下,是死亡的结局。这年9月,丰子恺请求弘一法师给他主持皈依三宝的仪式,从此成为居士,法名婴行。他出家做居士,却并不是与世隔绝,脱离尘世。因为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不能抛家舍业。他只是要给内心找一个归宿。丰子恺说过:“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年纪越大,他越喜欢孩子,他说:“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他和孩子们玩,他们看什么都那么有趣,他们的真实纯洁天真,让他感动。而长大了的人,年既长,物欲蔽其真。他为孩子们画画,简直成了一个儿童崇拜者。越是看到这个世界的虚伪和矜持,他越是喜欢孩子的真性情。

渐渐地,他试着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去看世界,并将之画出来。每天下班回家,妻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孩子在门口等他回来。一看见丰子恺,那高兴的喊叫,那么动人。“我看见世间的大人都为生活的琐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记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们保住天真,独具慧眼,其言行多是供我欣赏者。”他也反思教育,觉得有些教育方式就是扼杀儿童天性。1933年,他回到老家,自己设计房子,房子建完后,取名“缘缘堂”。此后,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定期外出旅行写生,画画。在这里,他创作了大量的画,写了很多文章,这是他的高产期。古人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丰子恺相信这句话,他觉得,所谓无益之事,就是感情、意气、趣味的要求而做的事。这些事不一定能带来现实的利益,但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像自己,而不仅仅是一个机器一样的存在。


平静美好的生活,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1937年,日本鬼子对浙江发动空袭,浙江危机重重,丰子恺被迫逃亡。这一年,丰子恺年近40岁。他本想寻求一处‘桃花源’,隐居避世,可他担心没有劳动技能的自己,无法适应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于是,他放弃了这种打算。在他逃亡的过程中,缘缘堂也毁于一旦。

一边逃难,一边画画,一边养家。有时候,他不得不重执教鞭,走上讲台。他在画画上,也提出了7个原则:一、不避现实;二、不事临画;三、重写生;四、重透视;五、重构图;六、有笔墨趣;七、合人生味。画画,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卖画,成了他养家糊口最重要的手段。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丰子恺高兴,他立即画了一幅画,庆祝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他再次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奔赴江南。这又是一次逃难,很多人都不理解丰子恺为什么要这样,但他说:“全为实利打算,换言之,就是只要便宜。充其极端,做人全无感情,全无意气,全无趣味,而人就变成枯燥、死板、冷酷、无情的一种动物。这就不是生活,而仅是一种‘生存’了。”

重回江南的丰子恺,成了有名的“三不先生”:一不教课,二不演讲,三不宴会。他拒绝做官,不参与政府差事,宁愿卖画谋生。人活着,不能没有物质,但人生,不能只是为了物质而活着。


特殊时期,他被迫做公开的自我批评,对此前创作的作品全部进行否定。丰子恺照做了。他谴责自己,从三十岁以后,就没有稳定的工作,从不关心政治。他说自己过去写作,看重趣味,兴之所至,不问归处,而今回顾,就是个人主义。他否定了过去的自己,本以为能够就此过去,可事情没有过去,而是一系列灾难的开始。为了能为人民服务,五十多岁的丰子恺,开始学习俄语,进行苏联文化翻译,很少画画,1953年,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出版。他把大部分精力用来翻译,因为相对来说,翻译不容易引起争议。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66年,丰子恺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个人产业,让他被定性为地主,他的资产被冻结。已经长期患病的丰子恺,被要求每天去汇报思想总结。他的脖子上挂着吊牌,被写大字报。他的《护生画集》,本意是弘扬生命,使人向善,却被说成宣扬反动思想。他翻译的《猎人笔记》,被说成“歌颂沉溺于宴饮和打猎的地主阶级”。他翻译的《源氏物语》,被说成“津津乐道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细节的黄色小说”。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他被要求进行体力劳动,清扫大街。

丰子恺的心灵,饱受摧残,然而,他没有为痛苦屈服过,他把这些苦难和不合理,看成一种修行。被关在牛棚,他觉得是参禅。被游街批,他当成是演戏。


有一次,刚被批完的巴金,被放出来时,看见丰子恺。巴金想,我都受不了,丰先生那样淳朴、善良的人怎么办?为纪念母丧,丰子恺留了长长的胡须,被剪了,他满不在乎地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一次写书面检讨,他都认认真真,书法漂亮,这些检讨,被喜爱他书法的人偷走了。有时候,被带到公众场合游街,路人跟他友好地谈话,他高兴不已。一天晚上,他被拉过黄浦江游斗,在旁人看来,丢脸而痛苦,他却开心地说,这是黄浦江夜游。他和美术理论家邵洛羊被关在一起,两人谈论美术,谈论佛教哲学,纵论古今。觉得美中不足,原来是差了酒,于是,放开胆子让家里送来酒,被发现了,就说是治病的药酒。那段艰苦的时间,丰子恺每天都按时“上班”,久而久之,身体竟然更好了。他给儿子说:“我因天天上班而身体健康了。近来只觉得烟、酒、饭,都味美,此即健康之证。”他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学习毛选,学习语录,抄写思想交代。但他总是想方设法搞“地下工作”,在花园中浇灌花草,写一点散文。有时候,以学习毛选为幌子,偷偷写古体诗。谈到这一切,他幽默地说:“好在我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足以抵抗。”

1975年,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手臂麻木,低烧不退。随后,被诊断为肺癌,已经转移到脑部,所以,他半边身子都不能动了,说话都困难。这年9月15日,丰子恺离世,享年77岁。世俗很无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无趣。然而任何时代,都有人活得有趣。


人生若如丰子恺,生活处处皆可爱。丰子恺一生都在追寻趣味,想要活出真正的趣味,所以,他宁为无益之事,宁做无用之人。他的生活,是有趣的。他把这种有趣,诉诸笔下,所以,在他笔下,凳子怕脏,天真的孩子就给凳子穿上可爱的鞋子。

天上的云,会变成美好的形状,给人安慰。

孩子们在乱涂乱画的时候,猫咪就在旁边安静地欣赏。

那些寻寻常常的小事,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变得非常有趣,可可爱爱,有了欢喜。他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觉得人生太难,他就说:“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他的一生,有许多苦难,但他都坦然面对,他像大人一样求生存,教书,卖画,都是为了生存。但他却像小孩一样生活,看这世界,总是可爱。

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太难,太复杂,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利益,都是生存,我们总是在权衡,却忘了欣赏,看云时,我们觉得云不能吃;读书时,我们会想着能不能赚钱。我们只看到有用之用,看不到无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