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尊临入涅槃,文殊大士请佛再转法轮。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说一字,汝请吾再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邪?”
——《五灯会元》第一卷 释迦牟尼佛
白话直译:佛陀即将圆寂,文殊菩萨请佛陀在最后时刻,再为大众说一次法。
佛陀严斥道:“文殊啊!我于世间教化众生长达四十九载,实则一字之‘法’亦未曾言说。现今你请我再度宣法,难道我曾经有说过法吗?”
 鉴赏评说:
鉴赏评说:佛陀在悟道之后,其往后余生皆投身于说法与度人的事业之中,然而他自身却言:“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说一字。”此等言辞,着实令人费解。
若要解开其中的困惑,关键之所在便是这个“法”字。
在佛陀住世的四十九载岁月里,回应了众多信众的诸多问题,亦成就了诸多事宜。然而,以其视角审视,此等种种皆为自然而然的寻常之事。
何为自然而然的寻常之事?理所应当之事,没有选择之事。就如《金刚经》开篇所记录的那样:
“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佛陀身着衣装、手持钵盂,步入城中行乞得食物,而后返回祇树给孤独园,用膳、收纳衣钵、洗净双足安坐下来。
当须菩提问起“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之时,佛陀就开始回答这个问题。

这一切的言行都是自然而然的举动,在佛陀看来,自己有说法吗?当然没有,这都是无比平凡的日常。
而在佛陀以外的众人看来,佛陀的回答问题就是“说法”,他的行为是“无言之教”。总之,在佛陀的言行之中有意义、有道理,人们就把这些所谓的意义概括为“佛法”。
“法”只是人为的定义、概念,只存在于人的思维、意识、观念之中,而不是一个独立自性的客观存在。
“法”是人对自己以外的一切存在的认识与解读,“佛法”就是信众们对佛陀言行的归纳与总结。
既然是出自于人的意识、思维,当然不是客观存在,当然不是恒定不变的真相。从这个层面来说,佛陀当然未曾说一个字的佛法。如果执于佛陀所说为佛法,是“以指为月”,是对佛的诽谤。

《金刚经》中是这么说的:
“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在世人看来,每一次集会,佛陀是说法者,大家是听法者,佛陀所说就是佛法。而佛陀是已经亲见实相的觉悟者,破除了“人我见”、“法我见”,已不执着于人相、我相、法相等等区别。
这就是“三轮体空”,没有说法的“我”,听法的“你”,所说的“法”,“人、我、法”全空。
在他眼中只有“自然而然”,“应该如此”。没有谁刻意要说什么、也不是一定要说给谁听,也没有什么是必须要说的,一切皆是当下的现量显现而已。
“无为而无不为”大抵就是如此吧!
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大抵也是如此。天地之间的一切,无论有言还是无言、有情还是无情,无一不在诉说着那言语难以触及的诸法实相,实则皆为真如本心的外显。

如果定要说天地一切都在“说法”,这又是诽谤,本来显现的真如本心即随之无影无踪了。正所谓“一叶落大地秋,一尘举大地收”,就在那一念升起的同时,真心即为妄心,已然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了。
佛陀是“无念”的,没有刻意,只有眼前;凡夫是“执念”的,应有尽有,唯无当下。佛陀活在当下之中,凡夫生在意识之内。
“念”即对当下的总结,对眼前的了别,已然是“事后”了,在事前有什么?前面一句为何?这才是修行者要着力的地方,而不是在“后来之事”上耗费力气。
也可以说,佛陀是活在当下的人,凡夫是活在过去的人,因为念念生起皆慢了“半拍”。佛与凡夫同为人,只有心境有所差别而已,佛的心不离当下,如如不动;凡夫则心随境转,时时处处。
当下不空,只是“无念”的有,非空非有。

所以,如果说佛陀未曾说一字,一法未说,这还是在谤佛。如果佛陀一字也未说,那住世四十九年都在干什么呢?
哪怕就是临近涅槃,也在说法啊!就如现在,佛陀斥责文殊菩萨:“文殊啊!我于世间教化众生长达四十九载,实则一字之‘法’亦未曾言说。现今你请我再度宣法,难道我曾经有说过法吗?”
这句话算作说法还是不算说法呢?在这最后时刻,佛陀答应了文殊的请求了吗?且看古时大德是如何评唱的:
“老汉生平太脱空,将无作有诳盲聋。临期一语方真实,也是阇黎饭后钟。”
“末上何曾转法轮,只今再转谩劳神。路行人不知天晓,犹把灵符执夜明”
“四十九年打之绕,下梢大作师子吼。虽然未始转法轮,毕竟分疎成应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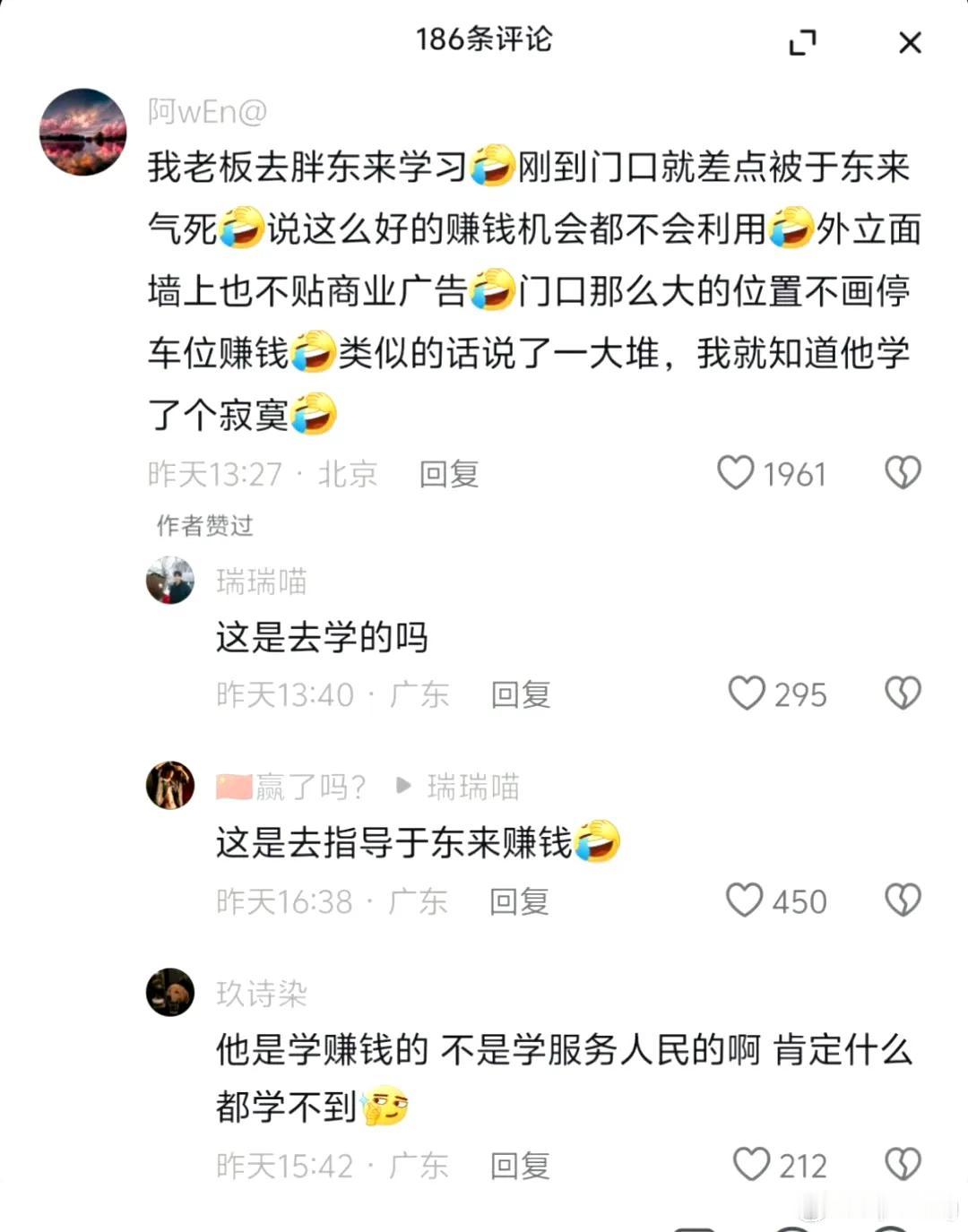



南無阿弥陀佛
汝既知三轮体空,奈何不知当下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