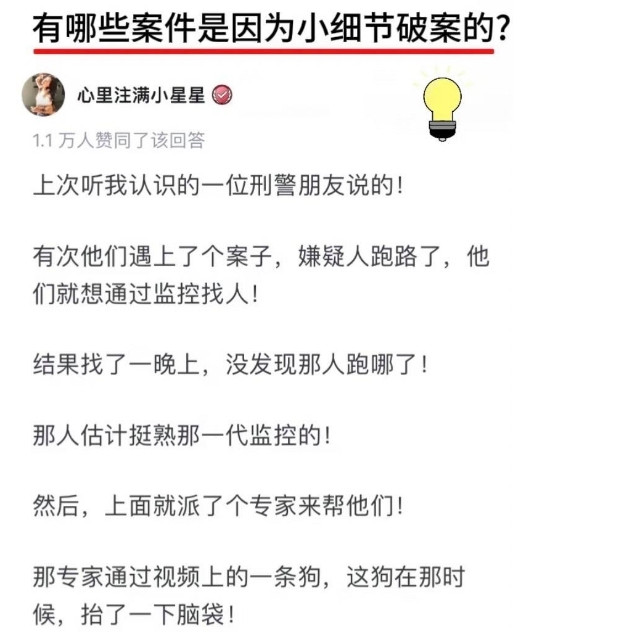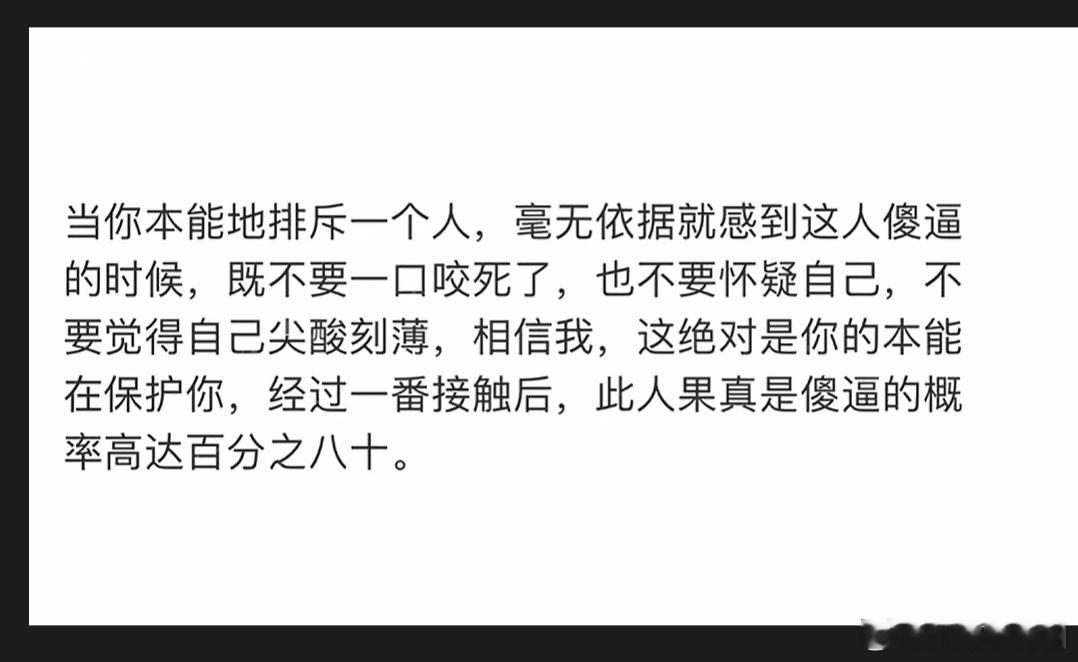"三十八块钱?就这点工资,我闺女能过上好日子吗?"岳母把户口本往桌上一摔,茶碗里的水都溅了出来,几滴水珠溅在我的手背上,凉丝丝的。
我叫张德明,82年从部队转业到派出所当警察。
那会儿正赶上改革开放初期,城里人看不上当警察,农村人挤破头都想进城,可我偏偏选了这个工作,差点让我和巧云的姻缘断送在这三十八块钱上。
那是个闷热的夏天,蝉鸣声吵得人心烦,空气里飘着槐花特有的甜腻香气。
我和李巧云谈了快一年对象,她在纺织厂上班,是个出了名的女工标兵,每个月能拿到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在当时也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记得第一次见她,她穿着件白底碎花连衣裙,头发扎成马尾,站在纺织厂门口等班车。
阳光透过梧桐树叶,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一瞬间,我的魂就被勾走了。
她总是穿着一尘不染的白布鞋,鞋帮上还绣着一朵小红花,走路时带着一股青春特有的活力。
"小张,你说你当兵那会儿当连长,多威风啊!咋就转业当个小警察呢?"岳母孙桂花坐在家里的竹椅上,一边剥花生一边说。
花生皮随手丢在地上,那架势像是在给我这个准女婿一个下马威。

屋里闷热得很,电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可还是挡不住汗水往下淌。
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可还得赔着笑脸:"阿姨,这工作挺稳定的,组织分配..."
"稳定?"她抬起头,眼神里带着讥讽,"我刘婶家闺女找了个供销社的,月工资六十多,年底还有奖金呢。"
"你这三十八块钱,够买啥啊?连个彩电都买不起!"她说这话时,眼睛瞟向墙角那台已经开始发黄的收音机。
巧云在厨房里听见了,赶紧跑出来打圆场:"妈,德明人实在,工作也认真,以后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注意到她的手上还沾着面粉,想必是在揉面团,这姑娘一直都是这样,心细如发。
"实在有啥用?你看看杨寡妇家闺女,嫁给邮电局的小张,都搬进单位分的新房子了。"
"你要嫁给他,以后住哪儿?派出所那间破平房?"岳母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失望。
我低着头,手心全是汗,说实话,这些话真不好听,可人家说的也是事实。
那会儿我和巧云商量好了,先租住在单位附近一间平房,等有了钱再想办法。
巧云从不嫌弃,她总说:"咱们年轻,有手有脚的,干啥不能干?慢慢来,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结婚头一年,日子过得真是紧巴巴的。
那间平房十来平米,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房顶是石棉瓦的,下雨时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每到下雨天,巧云就得在屋里摆满脸盆接雨水,那声音听着让人心烦,可她总是笑着说:"好歹不用去挑水了。"
巧云从不抱怨,每到月底,她总要精打细算,把三十八块钱掰成两半用。
让我没想到的是,婚后岳母来得更勤了,每次来都要数落一通。
"看看隔壁王寡妇家闺女,人家女婿都买上电视机了,你们呢?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巧云啊,你这眼光,真是瞎了心了。"每次听到这话,巧云就低着头,假装在擦桌子。
我知道她心里难受,可她从来不在我面前表现出来。
巧云心疼我,背着我去街上摆了个烤红薯摊。
那天我下班巡逻,远远就闻到甜丝丝的香味。
走近一看,是巧云蹲在街边,正在翻烤红薯,她的脸被炭火映得通红。
她见了我,眼圈一红:"德明,对不起,我..."
我蹲下来,帮她扇炭火:"有啥对不起的,咱们一起干。"

从那以后,我下班就去帮她,顺便帮街坊邻居调解些小纠纷。
慢慢地,街坊们都说,德明这警察贴心,办事也利索。
有时候半夜接到警情,我不得不把巧云一个人撇在家里,每次回来,都能看到她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个馒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84年春节前,巧云怀孕了。
那天她兴冲冲地从医院回来,脸上的笑容像冬日里的暖阳。
岳母知道后,又是一通数落:"这日子还没个着落,急啥要孩子?以后奶粉尿布钱从哪来?"
可天有不测风云。
巧云怀孕六个月那会儿,赶上一场大雨,她去上班的路上摔了一跤。
等送到医院,孩子保不住了。
我守在手术室外面,听着里面传来的哭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
巧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谁劝都不听,她总是抱着那件给孩子织到一半的毛衣发呆。
岳母倒是不说风凉话了,可看我的眼神里全是责怪。
就在这时候,我在值夜班时碰上个被小偷光顾的批发部老板马洪福。
这人是下海经商的第一批人,在我们片区开了好几家店。
案子破了后,他特意来派出所送锦旨,还请我去他家吃饭。

那天晚上,马洪福喝得脸红脖子粗,说起他准备开保安公司的事:"现在搞活了,个体户多起来了,安保需求可大着呢。"
"德明,你当过兵,懂这行,要不要来帮我?工资比当警察高多了。"
我心动了。
这些年,看着巧云省吃俭用,看着她失去孩子后的痛苦,再看看岳母那看不起人的眼神,心里不是个滋味。
辞职那天,我的手在辞职报告上颤抖了好久。
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张啊,你好好想想,这份工作多稳定啊。"
我知道稳定,可我更知道巧云眼里的期待。
下海的日子比想象中难得多。
开始那会儿,就我和几个转业军人,风里来雨里去地跑业务。
有时候一天跑十几家店,说得口干舌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巧云这时候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忙里忙外帮我。
她学会了打字,帮我整理资料,有时候还给客户送茶水。
"德明,咱们一起熬,一定能熬出个好日子来。"她总是这样鼓励我。
眼看生意有了起色,可祸不单行。
岳母突然查出肝病,医院要求先交五千块住院费。
那可真是天文数字,我和巧云这些年的积蓄加起来还不到三千。

巧云咬着嘴唇跟我商量:"要不,咱们找人借点?"
看着她憔悴的脸,我心疼得不行。
我二话没说,把刚赚的钱全拿去交了医药费。
那天晚上,在医院的走廊里,我看见岳母偷偷抹眼泪。
她悄悄拉住我的手:"对不起啊,德明,这些年,是我眼光短..."
她的手粗糙得很,满是老茧,我突然明白她也不容易。
转眼到了95年,公司规模越做越大。
我们不光做安保,还开始承接一些大型活动的保卫工作。
巧云也当上了公司的财务主管,每天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去上班。
记得第一次发年终奖那天,我拿着一沓红票子回家,岳母正在我家包饺子。
"妈,这是给您的养老钱。"我把钱放在她手上。
她愣了好一会儿,手抖得厉害:"不用,不用..."声音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巧云在一旁笑着抹眼泪:"妈,这些年苦了您,以后有德明在,您就安心养老吧。"
岳母低着头,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当年是我眼光短,看不起人..."说着就要给我鞠躬。
我赶紧扶住她:"妈,咱们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做啥?"
看着她花白的头发,我突然明白,人这一辈子,不光是为钱活着。

就像当年在部队学到的,做人要有担当;就像在派出所体会到的,帮人比算计人实在。
更像是这十多年来,我和巧云一起熬出来的日子,酸甜苦辣都是一笔财富。
昨天,我又给岳母送了个红包。
她什么也没说,就拉着我的手哭。
这一回,是喜极而泣。
看着她满头的银发,我忽然想起那年的烤红薯,外头烤焦了,可里头是甜的。
日子,不就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