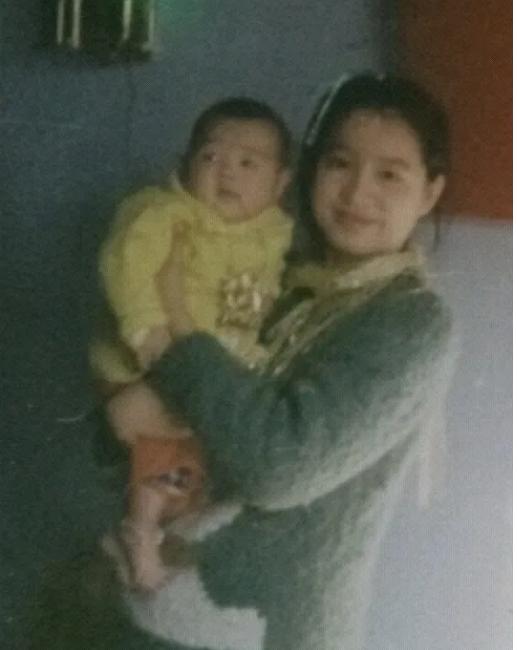“你还记得她吗?那个你说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人?”电话那头的老张语调平静,可话一出口,却像一颗石子砸进了心湖,激起一圈圈涟漪。我的手顿在半空,握着听筒半天没说话。
“哎呀,不说算了。”老张叹了口气,声音有点低沉。
“记得。”我终于开了口,声音不自觉有些哽咽,“怎么会忘呢?”
挂了电话,我点了根烟,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天空。冬日的杭州,天是灰蒙蒙的,风吹过,带着一股凉意。远处的江水缓缓流淌,像极了那条陪伴我青春的长河。
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可闭上眼,仿佛还能听到长河上撒网的声音,还有她清脆的笑声。
1970年,我十八岁,刚从中学毕业。当时响应号召,满腔热血地跟着插队知青的队伍去了北方。火车开了整整三天三夜,从南到北,一路颠簸,我的心情却越来越兴奋。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整整八年。
我们被分配到一个叫长河镇的地方。那里人不多,靠着一条长河,冬天冷得刺骨,天一黑,村子里就静得出奇,只有风拍打着窗户的声音。刚到那会儿,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南方来的毛头小子很好,分粥送菜,还帮我们铺炕。可谁也没想到,那段日子比我们想象的要苦得多。
我是个南方人,习惯了温暖湿润的天气,到了北方,干冷的风吹得脸生疼。可就在我快要适应的时候,认识了刘叔一家。他是渔队的队长,能干又热心,家里有两个女儿,大兰和小兰。大兰十八岁,稳重能干;小兰十五岁,活泼开朗。

那天刚到村子,刘叔就带着两个闺女过来帮忙。我记得特别清楚,小兰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递给我时,笑着说:“喝吧,南方来的哥,喝了这碗汤,保准你不怕冷!”她的笑容像北方难得的阳光,暖暖的。
从那以后,我就和刘叔一家亲近了起来。刘叔是个热心肠,教我们撒网、织网,还讲打鱼的规矩:“上船不能乱跳,撒网得顺风,鱼头朝左是吉利……”他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
小兰呢,总是跟在他身后,跑前跑后地忙活,偶尔还爱逗我们:“你们南方来的,怕不是连鱼都没见过吧?”那时候,她总是笑得很大声,像个没心没肺的孩子。
。织网的时候,她总是抢着干最多的活,别人夸她手快,她就嘿嘿一笑:“我天生会这个。”大兰却不一样,她显得更稳重些,总是默默地做事。
插队的日子很苦,尤其是冬天,河面冻得比石头还硬,冷风吹得人直打哆嗦。可春天一到,渔队就热闹起来。那是我第一次跟着刘叔下河打鱼。船刚划到河岔口,刘叔指着江面说:“看这水波,下面肯定有大鱼。”果然,一网下去,捞上来十几条活蹦乱跳的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我出事了。
那天,天蓝得像一块布,我站在船头试着撒网,脚下一个不稳,整个人直接摔进了冰冷的河水里。水下的寒意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我拼命挣扎,却怎么也浮不上来。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只大手抓住了我,是刘叔。他和另一个赫哲族的兄弟硬是把我从水里拽了上来。

那次我在炕上躺了整整一周。小兰每天都会端着热汤来炕头照顾我,嘴里还不忘调侃:“哥,你这水性还不如条鱼呢!”她说得轻松,可我知道,她担心得不行。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和刘叔一家关系更近了。我叫刘叔为叔,叫刘婶为婶子,大兰是大姐,小兰是小妹。乡亲们都说我像刘叔的干儿子,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对小兰的感觉不一样了。
197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刘叔在河边补渔网,小兰端着饭菜过来,非要喂我吃。我有点不好意思,可她却笑得特别灿烂:“哥,你吃一口嘛!”我瞪了她一眼:“用不着你喂,我自己来。”她撇撇嘴,坐到一旁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全是小兰的影子。她的笑声、她的眼神,甚至她端着饭碗站在夕阳下的模样,都一遍遍地在我眼前晃。我突然明白了,她不是小姑娘了,她是一个让我心动的姑娘。
可我不敢说出口。
1974年的夏天,小兰终于忍不住了。她跑到河边,拉着我的袖子问:“哥,你是不是喜欢我?要是喜欢,就明说啊!”我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她又问了一遍,我才低着头小声说:“我喜欢你,可是……”她打断我:“可是什么?”
我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说:“我爸妈不会同意我留在这儿,他们希望我回南方。”小兰听完,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消失了。她什么都没说,转身跑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像被刀扎了一样。

后来,小兰渐渐疏远了我。我试着去找她,她却总是笑着说:“你忙你的吧,我挺好的。”可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难受。
1975年冬天,我被调到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离开渔队的那天,刘叔拍着我的肩膀说:“娃,去吧,好好干。你婶子和小兰都会记挂着你。”我点点头,却不敢回头看小兰一眼。我怕看见她的眼泪。
几年后,我考上了师范学校,离开了长河镇。走的那天,小兰没有来送我。听刘婶说,她嫁给了村里的一个小伙子。我心里像空了一块,却又松了口气。
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就是三十多年。2009年,刘叔去世了。我赶回长河镇,见到了小兰。她老了,头发也白了,可笑容还是那么熟悉。我们聊了很久,她说自己过得挺好,儿女都孝顺,还让我别挂念她。临走前,我偷偷给她留了一些钱,可她却塞回了我的包里。我没再坚持,只是笑着说:“小兰,咱们这辈子是没缘分了,下辈子吧。”
她也笑了,眼角却湿润了。
每次想起她,我心里都会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那条长河,那个笑得像太阳一样的姑娘,成了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记忆。
“喂,老李,你听着没?”电话那头的老张还在喊。我回过神,轻轻地说:“记得,怎么会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