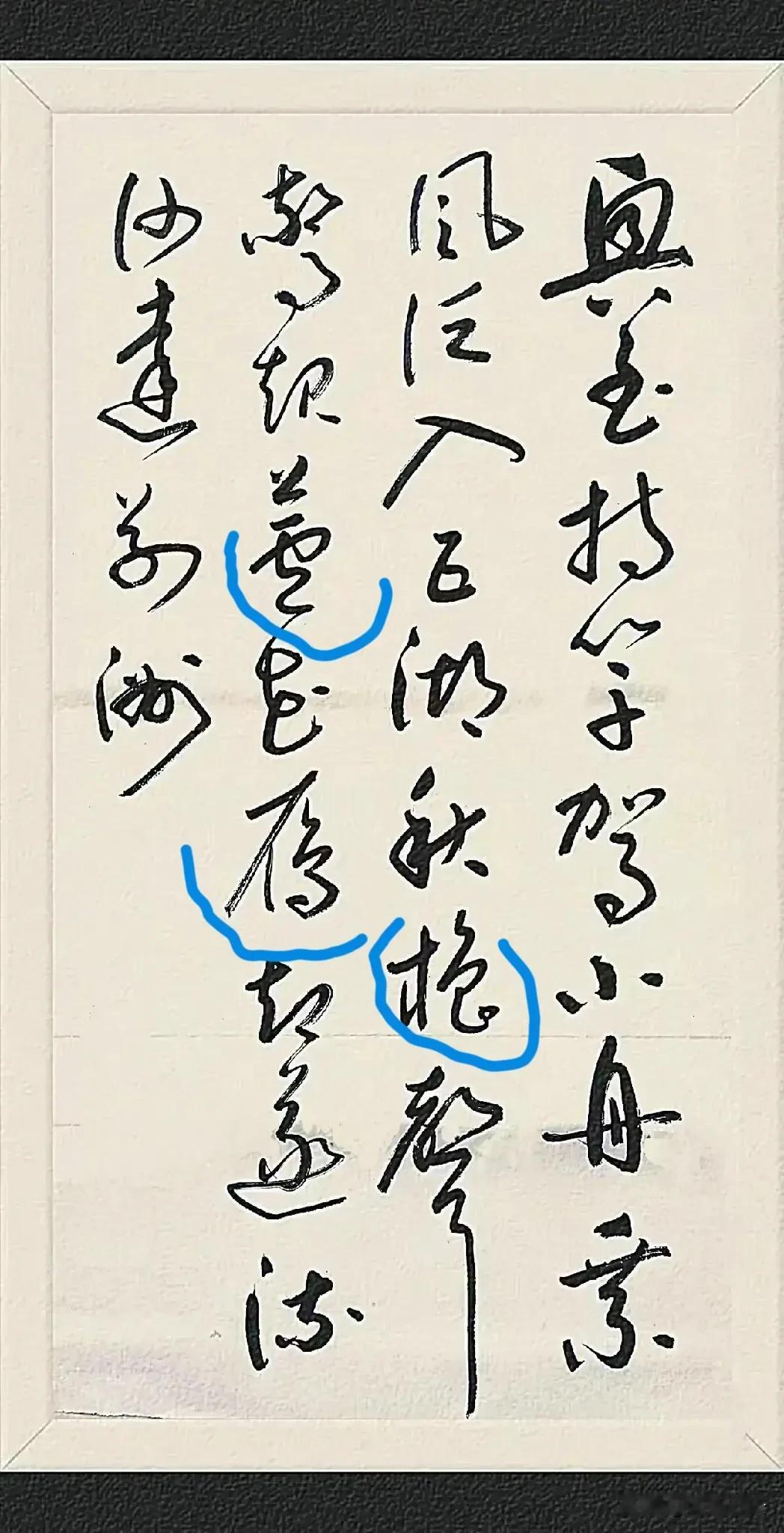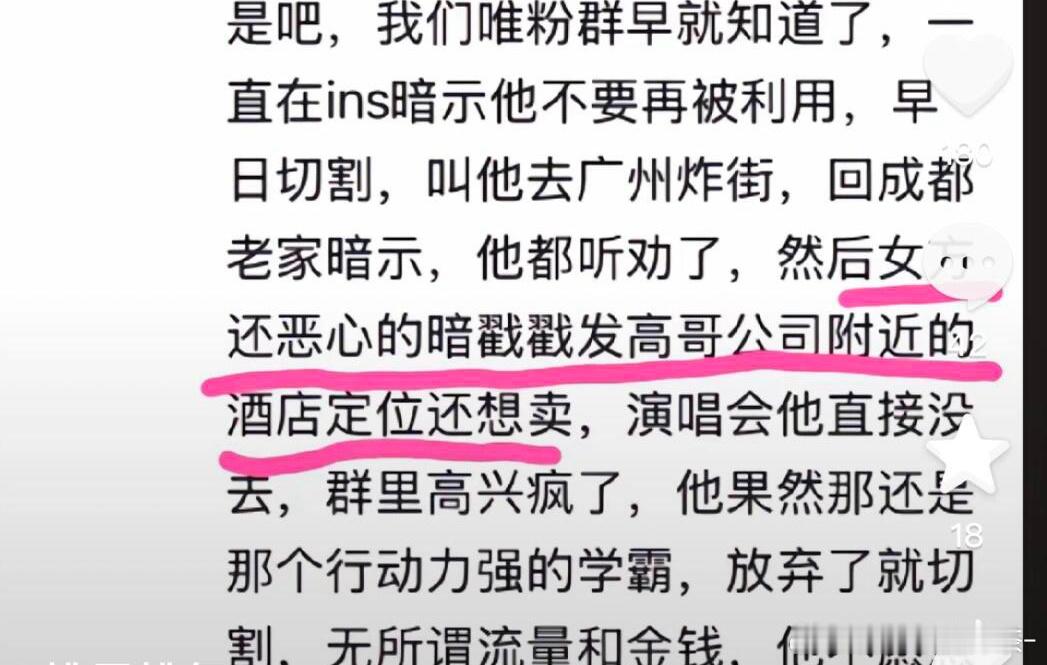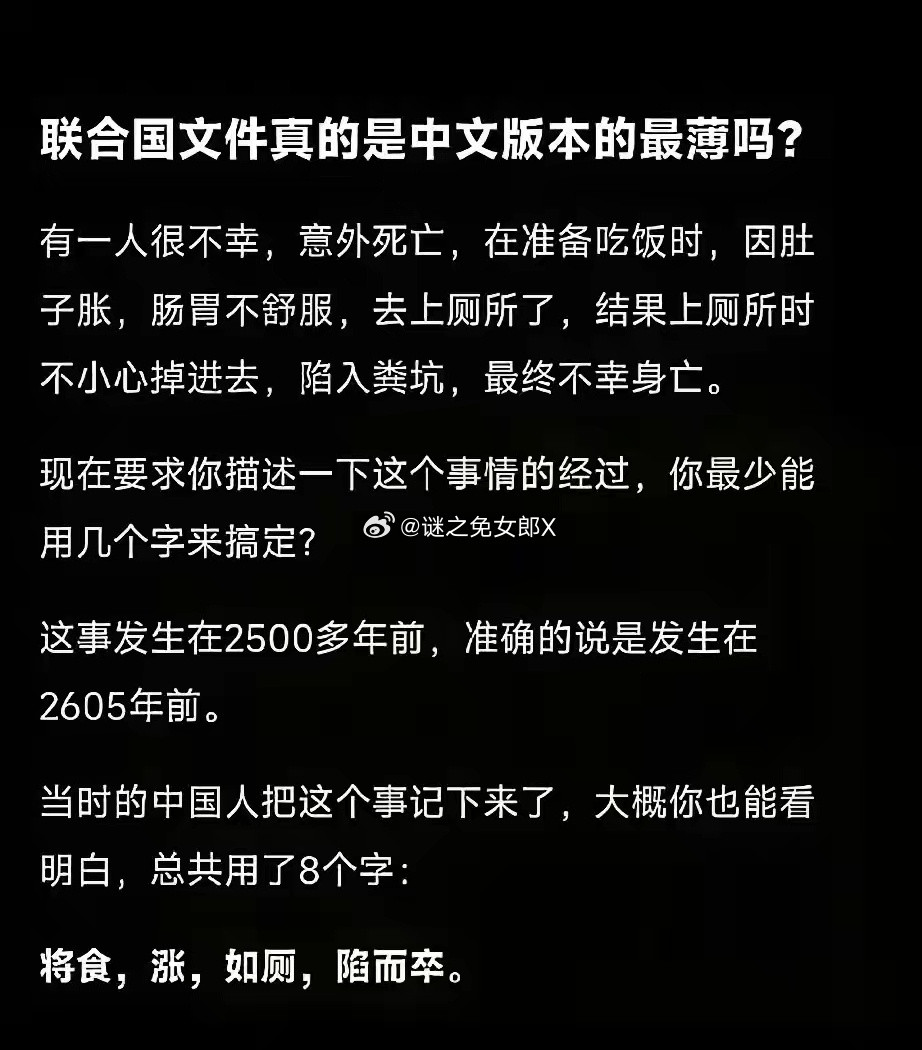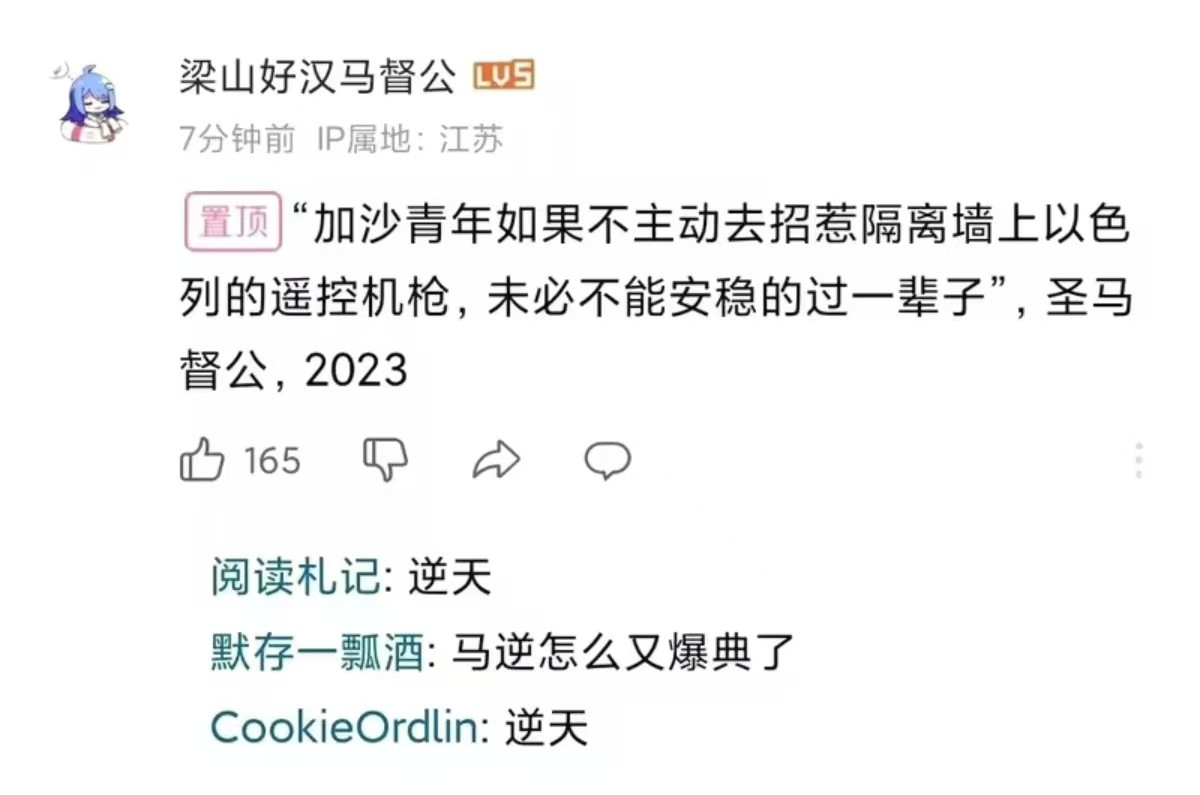简介:女主是皇族公主,她对男主一眼万年,男主本是世家子弟,后被诬陷全族被流放,但是女主把男主保全了下来,男主心里其实恨皇族中的每一个人,但是在和女主相处中却慢慢的对女主动了感情,却没有对女主坦白,只是默默的一直暗恋女主!而且甘愿沦为女主的棋子,为女主扫平一切障碍!
【文章片段】
夜色茫茫,孤月高悬,回廊下花灯如海,谢鸳携织春穿过长廊,谢润嘉立在石阶下看着她,眉眼温润柔和,笑容温文尔雅,“九妹。”
谢鸳忽然顿住脚步,沉默地站在游廊上看他,许久后才轻拍了下织春的手,独自上前,“太子哥哥。”
谢润嘉温柔地注视着她,“腿上的伤好了吗?”
他从袖中取出翠绿玉瓶递去,“孤知道你爱美,昨夜孤才从长河县赶回来,这是特意寻名医为你找的膏药,涂上半月便能祛除腿上疤痕。”
风声微微,灯火摇曳,老虎状的灯影朦胧地印在谢鸳额头上,她垂着眼眸,并没有伸出手去。
“太子哥哥,林魏死前曾告诉我,关外的冤假错案,是你在背后为他们撑腰。”
她倏而抬头,烛火映出一双安静漆黑的眼。
“是吗?”谢鸳的声音很轻。
灯影长长,人影斜斜,谢润嘉的唇角挂着温和笑意,“人无完人,谁能无过,九妹,此时天下安乐,你已经杀了林魏,就不要再生祸端,无事生非只会乱了这盛世。”
谢鸳眼睫微颤,紧紧盯着谢润嘉,像是第一次认识他。
太子一袭长衫,眉目如玉,周身温雅的气质仿佛还是那个不顾生死去救她的仁义少年。
“你所谓的盛世不过是眼皮下被林家伪造的方寸之地,你可知关外有多少平民尸骨未寒,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你既然自诩慈悲心,能渡林家这些罪恶滔天之人,为何不能渡那些枉死的冤魂?”
字字铿锵,句句响亮,她的眸光锐利似刀,无声地割着他的皮囊,谢润嘉恍若未觉,淡笑依然,“关外远在万里,你口中的假案冤情,孤从未见过。”
谢鸳愣住,难以置信地瞪眼,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凝固了般,垂在袖袍中的手攥紧,指节用力到发白,她怒道:“你看不见,你也听不到吗?本宫所言句句属实,谢润嘉......”她颓然地摇头,“本宫从不知道你会是个装聋作哑的无耻小人。”
“九妹。”谢润嘉一贯温和的笑容里渗出几分凉意,“孤决不允许有人破坏大晋的太平盛世,也不会让人动乱民心。”
晚风瑟瑟,两人互相对视,长久的静默后,谢鸳突然抬步上前,逼视着他的眼睛,“若本宫偏要与你作对呢,之前本宫已向父皇求得皇太女之位,你我相争,江山社稷必然动荡,民心一乱,盛世将倾。”
谢润嘉怔住,脸上的笑意渐渐隐去,面色慢慢变得苍白,“九妹......你是想与孤......夺皇位?”
“如果本宫说是呢,你会为了你的太平盛世让位于本宫吗?”谢鸳莹白的面庞上半是讥讽半是苦笑。
一阵相顾无言,谢润嘉轻轻垂下眼,他握着手中的玉瓶,只觉得瓶身冰凉刺骨,冷的他手脚发抖。
他无母族依靠,也无帝心偏宠,若非是谢鸳指他为太子,他现在还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大皇子,如何能争得赢有数万顾家军的谢鸳。
“九妹,孤......孤......”谢润嘉胸膛剧烈起伏,握瓶的手背青筋凸起,他勉强平息了情绪才缓缓抬起头,“若天下能安定,皇位还给九妹.....又如何。”
话落,谢鸳轻笑出声,只觉得眼前惺惺作态的人令她陌生恶心。
谢润嘉母亲过早离世,谢鸳怜他出生可怜,从小受尽欺凌却有颗慈悲向善之心,从不去报复欺辱过他的太监宫女,朝夕相处后,谢鸳恻隐之心钦点他为太子,后来她又亲眼见证自己选的少年成长为被百官称赞和百姓拥戴的菩萨太子,她如何不引以为傲。
只可惜一切都是黄粱一梦。
“谢润嘉,当初是本宫被猪油蒙了心,选错了人,你常年在外,并非不知那些穷民过得是怎样水深火热的日子,你只是害怕惹祸上身,害怕多生事端得罪权臣,害怕民间不稳威胁到你的太子之位。”
说这一番话,谢鸳情绪异常平和,声音却尖锐地能将人心上戳出几个窟窿,谢润嘉那双看似平静的眼眸之下风云涌动。
谢鸳朝他走近,他下意识退后两步,却不想谢鸳只是擦着他的袖子走了过去。
“你这慈悲心骗本宫也好,骗他人也罢,别连你自己都骗了去。”
谢鸳头也不回,声音随着背影消失在漆黑的深夜。
风声簌簌,织春不明所以地追上谢鸳,身后风碎玉裂,谢润嘉手中的玉瓶猝然坠地,摔得四分五裂。
.
小径幽僻,草木无声,谢鸳步履如风,柔软娇美的小脸在月色的辉映下如美玉一般冷。
“公主,那好像是沈公子?”织春匆匆跟着她,转身间冷不防瞥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惊愕出声。
闻言谢鸳脚下骤停,抬头望去,只见清澜水榭之上,一袭白衣青衫的沈浮白冷冷清清地立在柱石边,周遭围着几个衣着华贵的纨绔子弟。
“听说你就是九公主废了好大劲从犄角旮旯里带回来的人?”
“你真是九公主相好?还负心于她?”
“年纪轻轻做小白脸,你可真不要脸皮。”
“以色事人能得几时好,九公主无情无心,等将来被她嫌弃还不如现在投靠我们。”
“沈白脸,说话。”
沈浮白不动声色的目光从几人脸上扫过,陌生,冲动,愚蠢的脸,一看就是谢鸳给他招惹来的祸事。
前脚从太子虎穴出来,后脚被劫到狼窝,他有点怀疑跟着谢鸳进京是不是错了。
“老大,这人被我们堵了一刻钟都没开口,该不会是个哑巴吧。”身材肥胖的王早斜眼瞅着沈浮白,他身旁站着位身穿蓝色锦缎长袍的男子,手握象牙折扇,衣冠楚楚,风度翩翩。
“没用的东西,都给本公子滚开。”
瞬间人群作鸟兽散,张邈反手甩扇,不疾不徐地走到沈浮白身前,上下打量后用扇顶抵住他的下巴,“长得还行,挺讨人厌,识相点就告诉本公子谢鸳有什么把柄落在了你手上,否则你今日走不出这榭水亭。”
张邈的语气吊儿郎当,最后几个字又极为冰冷。
“老大,今日是盏灯节,不能——”一旁的王早轻声提醒,张邈却猛然转身踹了他一脚,“闭嘴。”
“哦。”王早痛得嗷嗷跳起,满腹委屈咽了回去,张邈转过头去,冷眼看着沈浮白,威逼道:“你若说得好,本公子赏你个小官做,你若说得不好......”
凛然的杀意直逼沈浮白,他垂下眼帘,眸中寒意浓烈,而后在众目睽睽下问了一个怪异的问题。
“你是几品官?”
“老大可是正六品,你现在跪下求饶还来得及。”狗腿子抢先开口,马屁拍的张邈得意忘形地昂着头,他自然也就错过沈浮白眼中那一闪而过的冷意。
“正六品啊......打的就是你。”话音未落,沈浮白突然抬脚,一脚将毫无防备的张邈踢出了榭水亭。
众人目瞪口呆,彻底傻在原地,只有王早反应极快地扶起趴在地上的张邈,紧张地心提到了嗓子眼,“老大,你没受伤吧。”
张邈推开他,沉着脸往地上吐了一口血沫,“敢踢老子,我让你瞧不见明日的太阳。”
他盯着沈浮白,握紧的拳头发出咯吱声响,一步步逼近。
千钧一发之际,那挥在半空重重砸向沈浮白面门的大拳被一只纤纤细手轻松拦下。
“是谁?”张邈勃然大怒,两眉竖起,咬牙切齿地转头,只见一位身穿粉衣宫裙的圆脸丫头甩开他的手,然后咧着大白牙冲他挑眉一笑。
实在嚣张,气得很张邈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
“你个贱婢,你不得——”话音未完,身后又有人朝他的腿窝补上一脚,张邈膝盖顿时一痛,狼狈地跪倒在沈浮白面前。
“嘶”他一面疼得冒汗,一面暴瞪双眼,“我□□十八——”
张邈那双盛着滔天怒气的眼睛在回头望见谢鸳时,忽然浑身一哆嗦,“九......九公主。”
谢鸳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然后不紧不慢地抬头与沈浮白幽深的眼眸对上,片刻之后,她唇角向上弯起,杀人诛心般扫视着亭中众人。
“藐视皇权,亵渎皇室,有人告诉本宫该当何罪?”
狗腿子面面相看,吓得浑身筛糠,惊慌失措地跪了一地。
谢鸳懒洋洋地敛目,轻慢道:“张公子认为呢,这罪是大是小,该如何判?”
张邈的脸唰一下白了,掌心浸湿,惶恐不安地咬紧后牙,“不敬皇室该......满门抄斩。”
心跳声如擂鼓,气氛凝固,谢鸳一个眼神,雨棠兴冲冲地上前钳住张邈的下巴,迫使他屈辱抬头。
谢鸳眉梢微扬,似笑非笑地盯着他,“张邈,你知道上一个得罪沈公子的人是什么下场吗?”
张邈茫然地摇头,谢鸳俯身,嘴角噙着笑,声音异常温柔,“阜城的裴诏,被人千刀万剐,裴家的灭门惨案,可有所耳闻?”
霎时四周寂静,虫鸣声也没了,亭下的湖水无声流淌,沈浮白默不作声地扫了谢鸳一眼。
张邈等人面色剧变,怀城裴家,关外土皇帝,陛下都拿他没办法,谁人不知?
他们齐齐转头去看沈浮白,眼中既震惊又恐惧。
月色如银,月下公子长身玉立,面容平静,半分看不出是杀戮深重之人。
“所以啊……”谢鸳轻叹,话锋骤然冰冷,“谁给你们的胆子欺负本宫的人?”
张邈几人吓得跪成一团,身体忍不住发抖,守在亭外的织春忽然出声,“公主,君臣宴快开始了。”
谢鸳瞥了他们一眼,吩咐雨棠道:“盏灯不宜见血,既然今日祸事起于张公子口舌,你留下让他的嘴长长记性吧。”
雨棠跃跃欲试地搓手,看着张邈的眼神极其火热。
托七公主谢明珠的福,她最近手痒的很,张邈既是对谢明珠言听计从的狗,打他正好解心中闷火。
没人注意到,谢鸳走出榭水亭时,嘴角有笑意一闪而逝。
她刻意将裴家灭门的事说给张邈听,谢明珠可千万不要叫她失望啊。
.
波光粼粼的湖水之上,数朵烟花在漆黑的天幕之上炸开,一朵朵璀璨夺目的花朵点亮了整个夜空,通往章华台的拱桥上,谢鸳与沈浮白前后脚并行。
“原来克己复礼的沈家人逼急了也会动粗。”
“公主为何要提起裴家?”
两人异口同声,谢鸳弯眉笑了笑,眸光流转,声音慵慵懒懒,“为你。”
烟光万顷,烟气漫天,纵使耳边烟花声震耳欲聋,沈浮白的心跳声却越来越清晰,他瞳仁里的光芒散开,眼底晕染了看不清的种种情绪。
“公主好算计,提裴家,又借我提沈家,故意让人误会我与公主的关系,如此费尽心思,真的是谋区区一个我吗?”
“沈郎何必自谦,本宫所谋自然唯你一人而已。”走到拱桥最高处,谢鸳忽然停下,她笑意盈盈地转过身,头顶烟光流光溢彩,她的瞳仁熠熠生辉,仿佛倒映着万千星光,星光之下,沈浮白的身影清朗如月。
“沈郎不愧是本宫的知音,不用言语也能和本宫心心相印。”
春风乍起,吹灭了半湖烟火,灯影斑驳晦暗,这方天地骤然安静下来,沈浮白莫名走了神,他想起离开沈府的前夜,沈浪敲响他的屋门,他站在檐下的阴影里对他说,“浮白,你运筹帷幄,算计谢鸳替你除去裴家,可你有算到今日你会被她威逼进京?”
面面相看,沈浪探究着他的双眼,一种不安在心底慢慢滋生,他道:“我知道你志存高远,有千般算计,可你能算过人却算不过天,沈湛老祖便是前车之鉴,我只害怕你算到最后,把自己赔了进去。”
沈浮白站在谢鸳下方,他阖上眼,沈浪的脸逐渐模糊起来......
“沈浮白,你我心知裴家灭门之因与沈家脱不了干系,本宫主动向张邈提及你,当然是想让人去查此事,裴家因叛国被本宫灭门,可偏偏前夜本宫又救了假叛国的沈氏一族,你说他们若查到这些,岂不有趣?”
沈浮白抬头看向谢鸳,少女居高临下,笑容充满恶意,但不知为何,他竟觉得那双带着挑衅的眼眸在烟火下如同潋滟的湖水。
“你不觉得你有些无耻吗?”他道。
谢鸳眨了眨眼,颇为认同地点头,“不瞒你说,本宫总想对你耍无赖,若不无耻些,沈郎又怎会答应本宫上京做官,你说你当初不在沈府门口演那出断腿苦肉计,上京路上还能少吃些苦头。”
不等沈浮白开口,她又道:“沈郎是个聪明人,朝堂站队尤为重要,你这回是选择直接站在本宫这边还是同以前一样,先吃点苦头然后再站到本宫这边来?”
沈浮白盯着明眸皓齿的谢鸳,微不可察地在心底生出一点憋屈来。
幼年至今,他在关外见过许许多多难缠之人,有商贾有刁民有权贵,但这其中都比不上谢鸳,她简直是他翻遍古今书籍都找不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奇女子。
明是非不讲是非,心地软狠心辣手,明明身娇体弱,畏冷怕寒,却能徒手陪孩童挖雪埋尸,明明害怕血腥尸体,又能亲手杀去那些贪官污吏,他实在看不透她。
沈浮白不开口,谢鸳便耐心等着,终于,她听见他那冷冽如雪的声音。
“朝廷并不需要公主,我何须站队?还是说公主您......并非只是公主?”
“知我者,沈郎也。”
谢鸳凝视着她,嘴角慢慢上扬。
她懂沈浮白言下之意,沈浮白亦明白她真正所求,前朝与后宫,是男主外女主内,凡家国大事,女子不能插手,只能做依附男子的菟丝花,可所有人都忘了,大晋的开国皇帝可是那位始乱终弃了沈湛的女帝谢舒。
女子不如男就是这世上最大的谎言。
谢鸳俯身朝他靠近,闻到一股药香,凑到沈浮白耳畔,一字一句道:“女皇谢舒统治乱世,本宫便要做这世间的第二位。”
声音轻慢,却掷地有声,沈浮白淡薄平静的神情骤然变得惊愕,眉峰微皱,一时竟被她的狂言震住。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当今女子,需遵三从守四德,其中又以相夫教子为楷模,谢鸳若真要这样做,那便不仅仅是与天下人为敌,更是与这世道为敌,而她口中的谢舒早些年被人口诛笔伐,帝王情,刀下魂,世人为沈湛不平,口舌相传之下,几乎人人都视谢舒为大晋之耻。
但是谢鸳只是轻轻地笑了一声,朝他伸出手,逆光而站,眼眸里的光亮几乎比肩苍穹上的日月。
谢鸳说了一句话,沈浮白浑身一震,下意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少女转身离去,灯火下,她的背影纤瘦而坚韧,像带着孤注一掷的意气,沈浮白立在原地,眼底情绪翻涌,呼吸声被湖水里生起的风搅的乱七八糟。
他望着谢鸳的背影,她的话犹在耳边,“沈浮白,做本宫的谋臣吧。”
少女天真的邀约,胜过妖精刻意的蛊惑。
月色如水,花灯如山,章华台上觥筹交错,谢鸳姗姗来迟,在众人推杯换盏间,悄然落座。
君臣宴开宴后,太子率先起身向皇帝敬酒,众臣紧随其后,一时间筵席上热闹非凡,君臣和睦友好的表象之下,风起云涌。
李福全端着圣旨走到章华台中央,四周窃窃细语骤停,瞬间鸦雀无声,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昌乐公主谢鸳,年岁过十,理当出宫,故撤去封号,搬离未央宫。但因谢鸳为皇后首嗣,聪慧过人,得天庇佑,朕在梦中得先祖点拔,是以授如懿令,立为皇太女,钦此。”
满堂哗然,众人脸色大变,无数的惊呼如沸水般沸腾起来。
“如懿令!世间竟然真有这东西。”
“荒谬,女子参政,简直是伤风败俗,有辱风化。”
“女主内,男主外,此乃天地之大义,九公主身为皇族,更应要维护世道常理。”
“陛下糊涂,糊涂啊!女流之辈,不堪大任,如此便是给蛮夷可乘之机。”
“一定是那顾家在背后煽风点火,狼子野心,其心可诛,可怜太子殿下为大晋鞠躬尽瘁,到头来还比不上一个胸无点墨的九公主。”
......
一时之间,各种猜测愤怒、阴谋叹息纷沓而来,无人不侧目去看筵席中的太子。
谢润嘉坐在案桌后,神情平静无澜,没人发现他拢在袖间的手掐出了血。
浓云遮住孤月,天地骤沉,李福全将众人反应尽收眼底,心中喟叹:九公主虽有顾家军,但太子背后站着宗法制度,自有天下人为他为撑腰,两人相斗,胜负难料,大晋往后的安定日子怕是一去不复返啊......
“九公主,接旨吧。”
李福全高喝,望着谢鸳的目光复杂而敬重,今日起,再无尊贵无双的昌乐公主,往后大晋王朝会多一位传奇还是皇位下多一具血淋淋的尸骨,谁也不知道。
在数道视线的凌迟之下,谢鸳神情自若地起身,走到前面跪地抬手,“臣女领旨,谢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