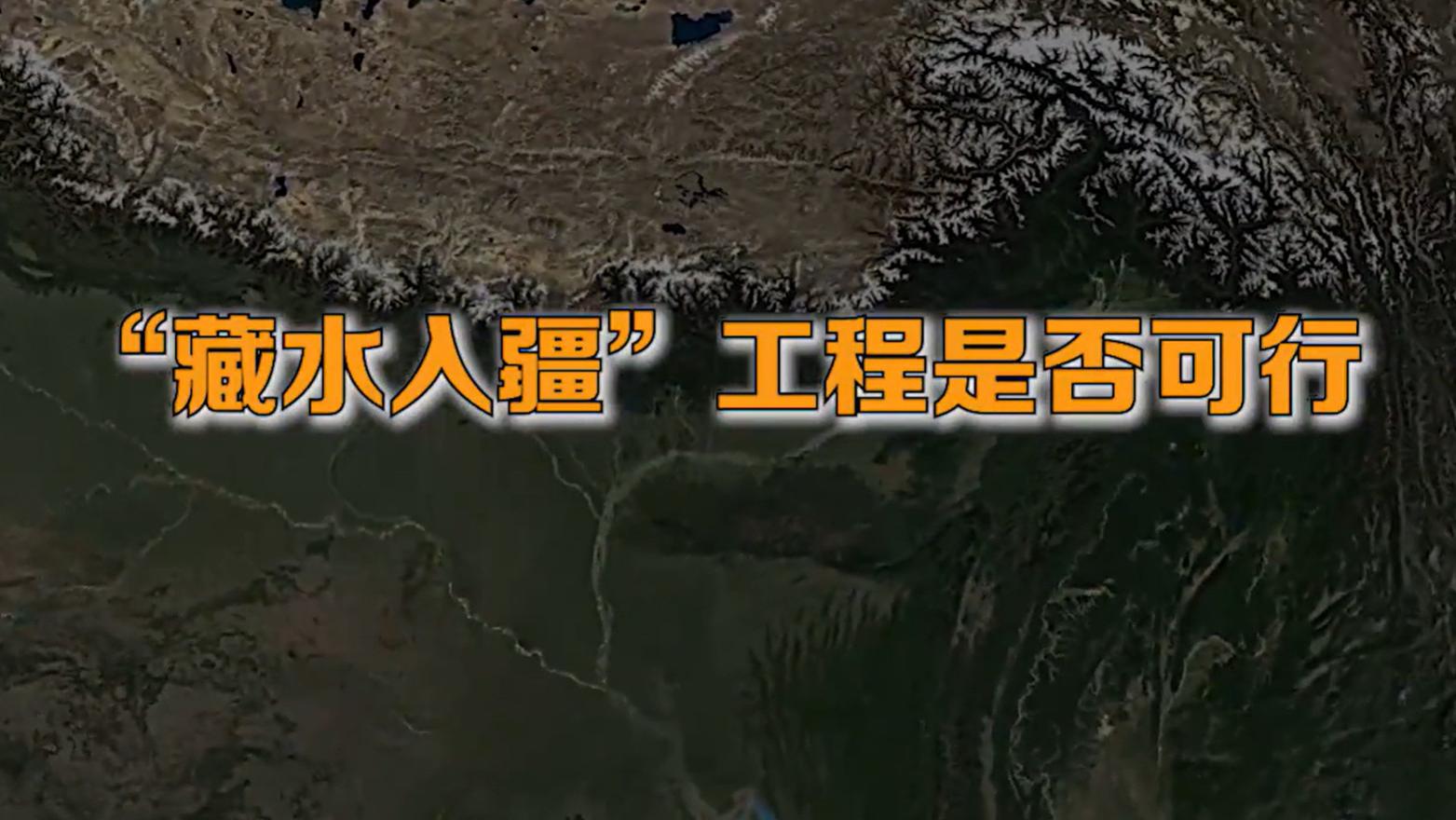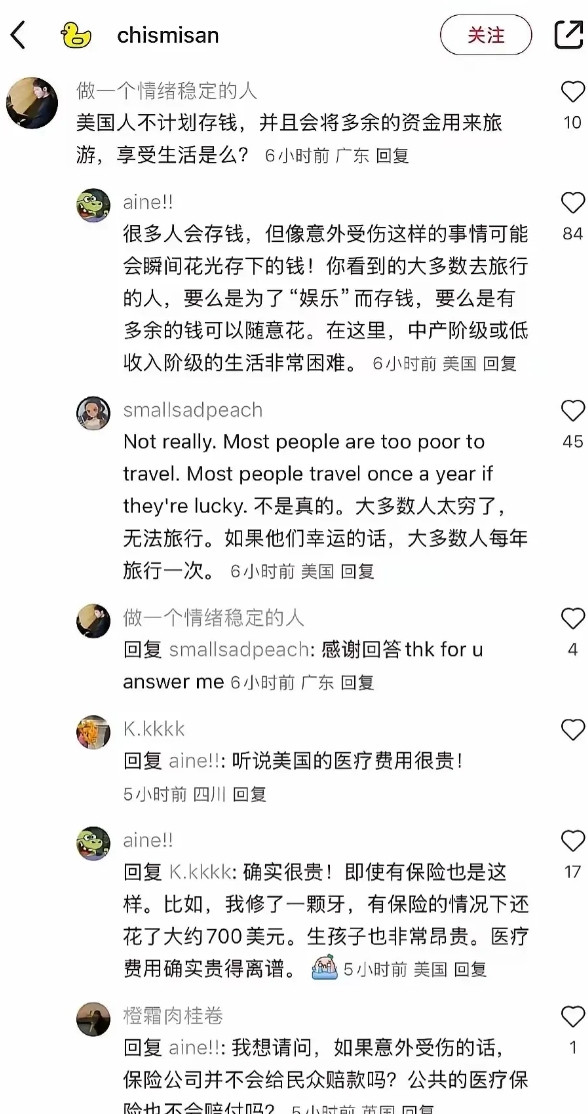讲述人/魏开谈
整理/温暖的时光
新疆阿克苏的红旗坡,驻地处于天山南麓一块平坦的冲积平原上,是孤立的一个营地,视野开阔。
极目远眺:北望,天山山峰叠嶂,尽收眼底;南观,一座因水得名的城市阿克苏市时隐时现,故道上的驿站,又是龟兹文化的发源地。

这里天蓝、水清、一条河、一座城,素有塞外江南的美誉。驻地依偎着它,提供生活的补给、便捷的交通,又远离喧嚣的市区与居民点,环境幽静,有塞上桃花园之美景。
离开红旗坡已四十多年了,每当提及它,仍是令我向往、怀念。
驻地原是部队一座营地。俗话说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兵撤了,留下这偌大的营房。
1978年底,从喀什迁来地质大队及两个兄弟单位(管子站、固井队)与留守的雷达连为邻相伴,这一下人声沸腾了,营区又恢复了昔日的热闹。
我是1980年初结束航空遥感工作分派来队的,历任大队党政领导有贾润胥、蒋炳南、陈飞鹏、康玉柱、张平举等。
这里集中了大队机关、野外分队、汽车队及个别随队眷属。几年中,职工有调换单位及调回家的,但院校分配及地方调入的人数还是挺多的。
女同志来队更成为青年人追逐的目标。全队总数保持在百余人左右,大队任务集中在地面地质工作,地质分队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区域构造分队,以后又组建了东疆分队。
我来队首次接受的任务,是带领人员赴乌鲁木齐石油地调处收集资料,入住明园达一个多月,文字都是手抄,图是透绘的,效果不好。

以后还去库车、泽普看石油部钻孔岩芯、岩屑,以及库车河、石四厂地表地层剖面。1982年后,我任分队长,两年完成了两项专题地质报告。
1983年大队部及分队调回乌市,汽车队仍留守红旗坡,1983年我改行做了党务工作。
红旗坡住房条件不错,分队同志都是住单间房,有的还是内外套间,既可住宿又能办公。
记得初来队上,每人发一个水桶、一把折叠椅、一个热水瓶。入冬时,各住房都烧煤灶,靠火墙取暖。
拜城拉回的煤堆在住房前,供大家使用。晚上入睡前要盖好炉盖,以防一氧化碳中毒,还得会埋火、压火才得以保持到第二天炉煤不灭。
每天要捅炉子、掏炉灰是免不了。有一天晚上,我的火墙突然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弄得满屋炉灰和碎砖块。
同住在一排的邻居才仁东智是位藏族中专生,也是从青海入疆的地质人员,后来又在同一分队工作过。
他生活习俗完全汉化,为人直率、随和、嗜酒。我对藏族风俗很有兴趣,常问他一些“人死了怎样天葬、农奴生活、婚丧嫁娶”之类的话题。
他从不忌讳,对我无话不说。后来他从青海探亲带回两瓶青稞酒送我品赏,因为我曾询问过他青稞酒味道之类的问题。
我说者无意,他却听者有心,铭记在心里。仅此一例,可见他为人诚实、对人重义气。后来他调回青海,还给我来过信,说他上兰州民族学院深造,现在海西州任副专员,我为有这样一位藏族好朋友感到高兴。

当时,除大队部有一台电视外,各家都没有,音响之类的物件,只有黄有元有一台砖头大的盒式磁带机,从他屋里经常传出郑绪岚唱的《太阳岛上》,悦耳动听,令我羡慕不已。
双职工及几户家属都没有冰箱,就在房前屋后挖了菜容,贮藏土豆、大白菜之类的冬菜。有的人饭后到地里摘苜蓿饲养鸡兔,生活过的简单,但都很惬意。
每当夜幕降临,三三两两人群聚合在一起,闲谈聊天,队上有什么情况一下就传开了。
也有下棋、上图书室、串门的,有时也组织篮球比赛,业余生活虽然单调,但人际关系却很融洽。
迁入城市住进楼房后,下班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关起门来自成一统,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年的场景,再也没有了,怎不令人怀念呢。
红旗坡多为晴天,气候干燥。令人讨厌的是刮风,甚至连刮几天都不停,狂风肆虐,黄沙尘土遮天蔽日地扑来,躲都无处躲,房内也是一层沙土,吸入鼻子呛人得很,那日子真是不好过。
当年,人们最大兴趣是看电影。工会姜景芳同志热心地为大家服务,不辞辛苦去租片,然后在驻地放映。
如有新电影上映,就组织大家去市里观看。一般都是安排在晚上,看电影的人总是满满载着一卡车,车下坡要走一条“之”字型的陡坎山路,才能下到宿阿公路上,三十几分钟就入市区了。

人民电影院是一个诺大的露天广场,摆着长条木板凳,不对号,随意坐,工会发的票几毛钱一张,每场都容纳好几百人。
队上两种人最受人器重:一是炊事员,二是司机。他们在队上地位高,受人尊重,尤其是炊事员,谁也不敢怠慢。当时生活供应不充足,一日三餐全靠食堂,粮食有定量,实行饭菜票制,先购票,后到食堂打饭菜。
后期实行登记制,月底结算付款。每次开饭前,早有人排好了队,一旦去晚了,就买不到好菜了,甚至买不到菜。此时,就看你平时的关系了,若与炊事人员关系好,或许会给你再炒一份菜,否则,只好啃馒头配咸菜了。
曾绍银是四川人,当兵出身,大家都不喊他姓名,管他叫“小老大”。也许是他个子小而又资格老吧,他算是地质大队“元老级”的人物,当了几十年的食堂内管,可以说为大家的饮食、生活服务了一辈子。
因为他为人随和、不记仇,大家都喜欢跟开他玩笑。他工作勤快、为人耿直,对不合理的事不管是谁敢于直言,在大家心目中有很好的口碑。
除了分内的事之外,他还为大家办了许多诸如解决子女户口、为余木银同志找对象、办家宴之类的事。
我有晨练的习惯,每天清晨一个人跑到驻地南面一块开阔地锻炼。此地西侧有一条名叫多浪的河穿过,把这块平地切成一处高出河床的阶地,一道陡坎成为驻地西边一条天然的屏障。
在这里,北望是雄浑巍峨、白雪皑皑的天山主峰7435米的托木尔峰,山下编延着郁郁葱葱的防护林带,而东边是硕大的苹果园林,空气清新、和风习习,面对这一派田园风光,总有一种情不自禁之感。
我时而仰天高亢几句与大地回应,时而俯首低吟,哼着小调抒发内心的情结。一首新疆民歌常挂在我嘴上:“天山路啊,长又弯,你总把我的思绪牵……”进到城市后,这种心境再也找不到了,真有点“能不忆江南”之感。
当年地质人员大多是二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充满朝气与激情。他们不把野外工作看作是一种负担,而是当作融入大自然,放飞自我,饱览西域风光,接触民情风俗的一次极好机会。
每个分队十几人不等,配备有账房、行军床、炊具、电台及大小汽车,汽车多为解放牌及八座后开门的北京吉普。
出野外工作一般在两三个月左右。中途也有派人回大队联系,大队也常派人前往看望,有时带去电影片。
野外人员最盼望的是信件,有的人一次能收到好几封,信件是读了一遍又一遍,非常珍惜这迟到的家书。只有身在野外离家千里的单职工才真正体味出“家书抵万金”的含义。
每当九、十月份,分队陆续收工,驻地又热闹起来了,大家相互交流野外生活、趣闻轶事。
这时人们都在忙碌两件事,一件是紧张地整理资料、尽快完成编写地质报告任务;另一件是企盼一年一度的探亲尽快来临,并在筹划着带什么土特产回家。
一年一度的探亲对内地的单职工来说,个个归心似箭。可是从驻地回鸟市要走两天的路程,也是异常难熬的。车是大队租的,人和行李挤得满满一车,使你动弹不得。
那些年冬天特别寒冷,既使穿上羊毛大衣及皮靴,脚都冻得发麻。中途用餐只能简单地对付,还得在库尔勒住宿一晚。

第二天汽车翻越干沟是最难走的一段,路面不平,弯多、坡陡,一路上总会看到几处翻车事故现场,令人不寒而栗,天黑时赶到乌鲁木齐。
记得有一次大家集体住在西大桥边的小旅店。我归心似箭,当晚去火车站购票,那时不能享受卧铺,都是硬座,甚至站在车厢内,坐在过道里,三天四夜才到达上海。
不顺利的话,在上海、杭州、鹰潭站还得换两三次车。折腾一星期才能回到福建老家。自1978年至1985年长达八年的探亲,我都是这样过来的。真是往事历历在目啊!
(图片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参考书目:《火红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