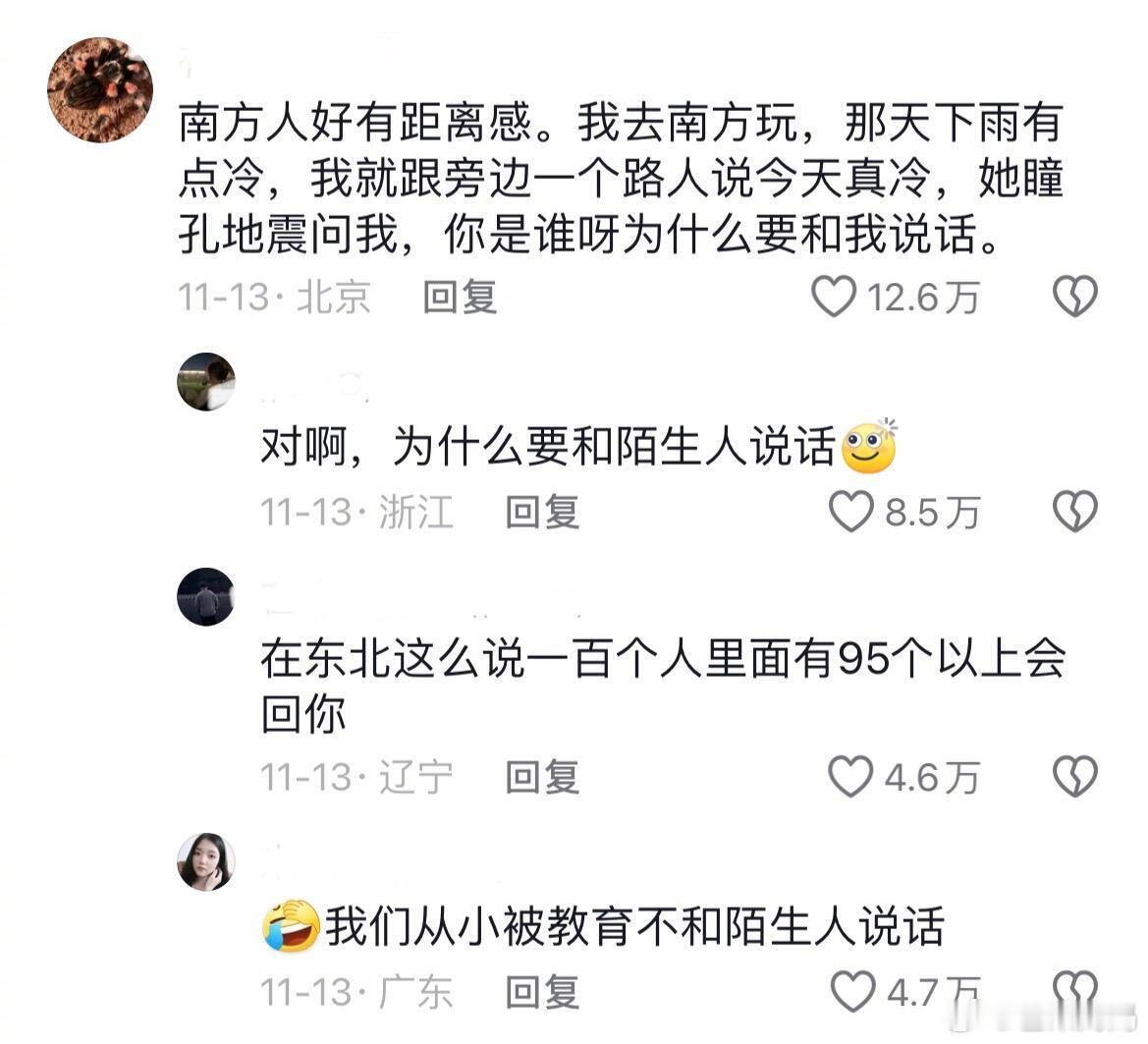简介:
醒来已是百年后,他不知道世间已是何等模样
一场灾难降临,她不得不寄人篱下
他说,百年若是等待的时长,林花倒算是个不错的礼物。
她说,毕竟他能出现就是不易,也已经耗上我一辈子的运气。

精选片段:
蝉闹。
热浪排开窄窄的巷道 ,穿过低矮的屋檐。阳光下透过树荫,拥抱郊外这一片翠绿。
一小束阳光透进纱窗,受到点困阻,不显得那么通透的落在他白皙如玉的手臂上。
他面容白净,目光沉静如水,表情自然而舒展,盛夏里着一件白衫,平整带着点檀香的幽香,袖口处有些翻折的痕迹,轻巧的握着笔的手在米黄的纸张上更衬的透明如琼玉。
听到叩门声,他放下笔,回过身站起来,目光浅浅,“请进。”
门开了,是一位手持木盘的小僧。木盘上盛了几个新鲜的桃子,桃边还有一封对折的纸张。
“方丈说盛夏桃子熟了,命我摘两个来给王公子,尘世难舍,王公子可以再考虑考虑带发修行的事,这封信是方丈写的,你看了再做答复也不迟。”
他点点头,拿起纸张拆开来细细过目,看完后,他垂下眸,沉吟许久,又抬起头,将纸张放进盘中,将桃子掂起来,放进衣袖。
“方丈说的不错,王祝虽一心向佛,但总归是属于这个尘世的。这几日,搅扰了。”
小师傅点点头,双手合十鞠了个躬,将门轻轻阖上走了出去。
燥热的盛夏。
森林里有衔枚疾走之声,风过树叶沙沙,翠绿的森林里不时有鸟被惊的飞起,汗水顺着他们的脸留下来,一些咸黏的汗流进眼睛里刺痛难忍,拿手背随意抹一把汗,汗水顺着手背滑下来打湿了睫羽,脸上斑斑驳驳都是灰色的水印。他们统一着黑色,左肩纹了一个水流型的“川”字,给他们领队的是一个中年男人,队伍中有渐渐透支的,领队似乎已经习惯于这样长时间的追踪和奔跑,虽过去了2个时辰,速度到也还是掌握的恰到好处,不远不近的跟在前面正在奔跑的人身后。
他一身白衣,足尖点地,迅速的掠过树木与丛林,衣袂飘扬,身后紧追不舍的人们只能瞥见他单薄的身形和一晃而过的身姿,深林深处,杂草已经长得很高,他不躲不闪,兀自钻进丛里,像一只游鱼进入了大海,转瞬不见了踪迹,留给身后的只是风中一声低笑。
领队的速度放慢了,他举起右手,示意身后的队伍停下来,疾走之声骤停,只隐约可闻微弱的呼吸和浅浅喘息,领队左右环视了一会儿,在右前方山路上瞥见白衣一闪,重新举起手,毫不犹豫的钻进了丛里。
过了一会儿,领队又不紧不慢的跟在白衣男子后面,穿过又一片密林,领队身后很多人被树枝阻碍不得不放慢了速度,领队咬着牙,用手不断折断面前的树枝,眼睛紧紧的黏在前方的白衣上,但还是无法追上飞一般自如穿梭的白衣男子,只能睁睁看着了距离越来越远,领队咬着牙加快速度,身后的随从们已经略显疲态。
穿过密林,眼前豁然开朗,白衣男子背对着领队一行人在断崖前站定,衣袂飘扬在风里,在夏日里落进眼里生不出一丝燥热之意,领队向前走两步,用手背擦去了额头上的黏汗,微不可闻的舒了口气,“王公子,身体近来可好?”
王祝转过身来,眉目如墨,唇色浅浅,嘴角勾成戏谑的笑意,“林将军实在太抬举我了,到如今还唤我一声王公子。”
林将军像是没听到,镇定自若,“想必王公子今日知晓我们来此的目的吧。”
王祝波澜不惊,“知道又如何?”
林将军拳头在底下渐渐握紧,“假如王公子不配合,那就怪林某无礼了。”
“无礼?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王祝眼底的笑意渐渐抽离,目光沉了下来。
林将军拔剑上前,有些隐忍,“王公子,我姑且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出兵符,”他顿了顿,“我权当没有今日之事。”
王祝的怒气瞬间被挑起,“呵,好一个没有今日之事,我王祝的命,我不给连天都不敢收,今日有胆的站出来,我王祝敬他是个好汉,留他个全尸。”
队伍里噤若寒蝉,一双眼里的笑意一闪而过。
“好,好一个连天都不敢收!王祝,事到如今你还当你是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无冕战神?今日我李仁就要看看,你王祝能插翅飞到哪里去!”
队伍里走出一个面容清秀的少年,身着将军服,英挺俊秀,只是眼底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戾气。
王祝眼底沁着丝丝凉意,“我也看看,无谋无勇的毛头小子借着天子余威可以逞能到几时,假如能死在我手上也算是苍天有眼让人快慰。”
话毕,寒光乍现。
李仁的眼睛里已经凝聚了浓浓的风暴的怒气,手中的剑在太阳底下发出渗人的寒意,“今日必让你王祝命丧断崖。”
王祝“铿”拔出剑,“死在我剑下也不枉你在人世盲走一遭。”
李仁一声暴呵冲上来,两人的剑纠缠在一起难舍难分,李仁的招式凌厉直接招招直击要害,剑花飞旋,银光在阳光下飞舞闪烁,李仁招式大开大合,王祝一时无法接近,只得步步后退,李仁手腕翻转,剑身像活起来的银色小蛇发出丝丝寒意迅速贴近,王祝侧身冲向前拿剑柄一架,李仁运剑方向一偏,脚下错开几步,卖了个大破绽,王祝提剑直击李仁面门,李仁猛然往前方扑滚堪堪避过一剑,王祝剑在李仁的各大要害部位游走,每次都是显显躲过,李仁恼羞,一张脸憋成猪肝色,眼睛里黑色的火焰就要扑出来,大吼着冲上来,猛利的剑气倏忽而至,王祝侧身躲闪,李仁手里的剑就像是长了眼睛,黏住了王祝,一时间两柄寒剑就像是两条挣扎扭打的蛇,铿铿作响。不知不觉中,两人已经打斗至悬崖边,李仁和王祝在崖边周旋,队伍里有宵小之辈怕李仁不敌王祝,扔出暗器,王祝侧身避过频频飞来的暗器,脚踝被击中,脚踝一崴踩中碎石,底盘不稳右肩结结实实中了一剑,剑透过肩胛穿透了肩膀,一时间血流如注,松了王祝冷汗涔涔,咬牙没出声,左手拔出了肩头的剑,站起来,看着李仁嗤笑,“这等宵小之辈还不配和我王祝过招。”
李仁大怒,扭头,“是哪个龟儿子扔的暗器!再有手痒的拉出去剁手!”
王祝偏过头嗤笑一声,声音里都是冷的刺骨的寒意,“惺惺作态果然就是你们李家的作风,背后弄权杀尽王家忠良,却说是斩除佞臣,不入流的子弟李家还真是人才辈出。”
李仁气得发抖,“我李仁行的正坐得端,王家有罪就当诛,再不交出兵符,新仇旧恨合一合,我今天就在这里结果了你!”
王祝眯着眼睛,听到“有罪就当诛”猛然呕出一口鲜血,“好一个有罪当诛,李家竟欺人至此!李家这梁子王家必千倍万倍讨回来!”
王祝站起来,白衣被鲜血染红大半,触目惊心,李仁拿剑直指王祝,王祝右手轻颤,已然握不住剑,颓然一笑,“王家灭门,索性有我王祝活着,你们杀我父母杀我胞弟,引你们来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王家最后一条命你们还不配拿走。”
话音刚落,王祝转身跳入断崖,血染白衣,飘然下坠,消失在层层白云间。
事情发展的太快,李仁还在怔忪间,队伍的人也沉默了,李仁神色复杂,望着断崖,眼底翻起波浪,慢慢的归于沉寂。
“王家这般气度果真骇人,今天万幸是我,李谷心慈,假如是他今日可能就不能肃清王家余孽了。”李仁轻叹,眉宇间戾气稍霁,随即神色一变,脖间一阵凉意。
寒光乍现,伴随一声底笑,银剑架在李仁脖子旁,像在耳旁吐着信的蛇。
“肃清?呵。”
十年一瞬,百年成空。
霞红漫天。徐徐晚风拂过,落英满潭,潭边树木郁郁,巧兔丛中栖,霞光滴进灵珠潭里化作星星点点的小鱼,映在石上漾着温暖的波光,鸟儿借着绯芒归巢,潭面偶有泡泡浮出,惊了岸边懒散爬行的小虫。
林间石阶上,一个约莫十七八岁布衣小村妇背上扛着布袋与竹篓,双手拽着两只鸡的翅膀,迈上石阶,她肤色偏黑,眉眼清秀,鼻子小巧挺立,酡红脸色,嘴巴里呼呼的发出喘声,两条腿在石阶上下不停抬动,虽额上鼻尖都汨出汗珠,但黑亮湿润的眼传递不出半点疲态,手中的鸡每隔一会儿就会继续负隅顽抗,惨叫啼鸣,无奈缚鸡之人对此无零星回应,闯入者携哀鸣者进入林里,惊扰了林里休息的飞禽。
这已经是她物色的第5个住处,她环视潭边,坐在潭边巨石上呼了口气,手捧着清凉的潭水喝了一口,在潭边洗了洗脸,用细绳捆好鸡,打开了布袋。布袋摊在土地上,一件件物什陈列在眼前:斧头,榔头,锅碗瓢盆,针线,几个黄面馒头,十来个鸡蛋,几件粗布衣服,几双草鞋,还有一些调味罐,一袋米,简单且实用。她怔怔的坐在石头上,过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眼睛里有着单纯的坚定和一点迷茫。
简要收拾了一下潭边的杂草,她在潭边搭了一个木屋,和鸡鸭拥挤的度过了一夜,沉静的夜里,星空满布,一颗一颗,近得一伸手就碰得一手荧光,鸡鸭耐不住寂寞,在小屋内鼾声震天时,摇摆来到潭边,鸭子喜水,见着水立马扑了上去,凫水好不欢乐,鸡在潭边踱步,湿了爪子,黏哒哒蹲在灌木丛下休息,鸭突然受了惊,叫了几声,从潭里挣扎着上了岸,小屋里没了声息,似乎是嘟囔了些什么,翻个身,鼾声又起。
夜色静谧。晶莹的灵珠潭水冒了几个水泡,又沉寂下去。
小村妇在这里住了几日,潭边慢慢有了浓郁的生机,搭成的小木屋慢慢的像模像样起来,每到饭点,半山腰总会飘起似有若无的炊烟,小村妇早出暮归,一天内总能有所收获,竹篓里有着新鲜的野果和蔬菜,有时候还能抓回一只野鸡或者野兔,喜欢的话就想办法养着,模样长的不够赏心悦目的就杀了炖一炖,小日子过得倒也算的算热闹舒心,暮色四合,趁着霞光泡进清凉的潭水里,汗涔涔的躯体在潭中慢慢放松下来,潭水清冽,清凉慢慢透入肌理,渗入骨骼,尽扫一天疲态,披上衣服钻进木屋里,结束了一天的生活,小村妇日子过得舒心,只是有一点纳闷,为何这喜水的鸭子一直不肯下水好好玩一玩?小村妇也尝试过把鸭子扔进水中,只是鸭子一入水就挣扎着要游出来,小村妇也无可奈何。
清晨,树林还笼罩在幽蓝的日光里,小鸟还在羽中酣眠,小屋中鼾声渐消,天空刚刚破晓,公鸡中气十足的蹄声唤醒了山间浅眠的人,小鸟睁开乌麻麻的圆眼,啁啭着,扑腾几下翅膀飞出林间,开启了清晨觅食之旅,小虫在地上爬行,慢慢悠悠,像是刚刚睡醒提不起什么精神,懒懒散散,剔透亮泽的露水从树叶上滑落,惊吓了眯着眼睛的小虫,四处逃窜。
灵珠潭水泛起了层层微波,水泡渐渐上涌,水泡渐渐变大,咕嘟咕嘟起着泡,一个巨大的白色身影从潭底立起,溅起巨大的水花,公鸡被水花泼了一身,惊吓的四处飞跳,啼鸣不已,鸭子摆着身体从潭边快步走过,幸灾乐祸的叫个不停,白衣男子站在潭里,面色苍白,头发衣服上挂着水珠,眉目如墨,清秀的像是一幅明晰的山水画,打湿的睫羽粘成一块,水汽蒙蒙的眼底隐约可见怒气在慢慢凝聚。
扰人清梦。
小屋内,小村妇坐起了身,迷迷蒙蒙抓了抓胳膊,披上外套提着裤子,推开门走到草丛里,环顾四周,顿了顿,又进了木屋,再出来时已经穿戴整齐,离开了潭边,约莫一刻钟,小村妇又回来了,生起火,下了一点儿素苗条,呼哧呼哧的吃上了。
王祝坐在潭边光滑的石头上,沉默的注视着小村妇,面目表情,直到她回到木屋里,拿着斧头离开潭边才有些松动。
烈日当空,王祝身上的衣物渐渐干透,王祝站起来,眼睛微眯,有些晕眩,大步跨入小村妇的木屋,狭长的眼睛眯起。
木屋很小,内部结构还算清晰收拾也算干净,进门就是一张铺在地上的小床,被单上绣着大红花的图案,底下鼓鼓囊囊,不知道盖了什么东西,王祝挑了挑眉,一把掀开被子,里面赫然躺着8枚鸡蛋,王祝一怔,拽着被角的手都忘记了放下,一个鸡蛋左右晃了晃,蛋壳破开了一个洞,洞慢慢变大,一个湿漉漉的小脑袋钻了出来,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的张望着世界,转头转脑,雾蒙蒙的小眼神锁住了面前的王祝,不动了。
王祝怔怔的看着面前的小黄鸡,下意识的转身大步离去,飞快逃出木屋。
王祝坐在石头上,望向潭水,目光浅浅,阳光在他的眼睛和潭面来回跳跃闪耀,天已经大亮,鸟儿吱吱喳喳的鸣唱,潭边小草还带着湿黏的泥土的清香,脚边轻柔的触感唤回了他的迷思,小黄鸡摇摇摆摆来到他的脚边,身上的水渐渐干去,毛茸茸像团鹅黄色的小云朵,黑亮的带着湿意的眸子一动不动看着王祝。
王祝神色微动,伸出指节分明的手,往小黄鸡额上不轻不重的一点,小黄鸡向后退了几步,额头上湿漉漉的,是一个手指的印迹,进入王祝触感里的,是新生命灼热和鲜活的温暖。小黄鸡上前几步,又贴上来,在王祝脚步摇摇晃晃踱着步,王祝轻轻点住小黄鸡的额,小黄鸡和王祝就以这样一种奇异却可爱的姿势暂定不动了。
小村妇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只灰毛的野兔,背上扛着一大捆干柴,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来到木屋前,把柴火往木屋后一扔,野兔的腿一绑,一屁股瘫坐在木屋前,拿袖子擦了擦汗,去潭边舀了点水痛痛快快的喝了一会儿,随即从背上的竹篓里拿出斧头,麻利的砍下了距离潭边空地较远的一棵树,坐在潭边削起了鱼叉。
这头,王祝和小黄鸡就像是被点了穴一般在石头边呆坐不动,手指触摸着小黄鸡软软烫烫的额头,竟喜欢的无法缩回自己的手,而小黄鸡懵懵懂懂的看着王祝,眼睛里都是信任和好奇,而另一边,小村妇削鱼叉活动进行的风生水起,木屑飞舞,斧头在树枝上上下翻飞,偶有停下来擦汗的时候,只是一擦完汗,小村妇马上就投入到了削树枝这项活动中。
慢慢的,小村妇的速度慢了下来,精神上也有些力不从心,削着削着就停下来沉默一会儿,过一会再接着削,约莫过了一刻钟,小村妇放了手里的鱼叉半成品和手里的斧头,轻轻的探了口气,扭头看向王祝。
“我说这位公子,小鸡刚破壳不能这样玩,再玩会死哩!”
王祝扭过头, “你看得见我?”
小村妇脸红扑扑的,在太阳底下呈现健康的苹果色,头上有汗,拿手背一抹,“为啥瞧不见?”
王祝一怔,看着小村妇,又下意识的看看自己,小黄鸡向前拱了拱他的手指,王祝扭头,心里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抬头看了看潭上,只见断崖面长满高耸郁郁的树木,遮蔽了从断崖直射下来的烈日光,无法透过层层树叶看清断崖全貌,王祝收回目光,轻柔抓住小黄鸡放在手心,颀长手指在小黄鸡身上下意识的摩挲,目光不着痕迹的在小村妇身上转了一圈,“你是何人?”
小村妇有些困惑,还是老老实实的,“我叫林花。”
林花?王祝顿了顿,“我的意思是,你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到这里,或者说,”手指在小黄鸡身上点了点,“你来这里,是不是为了找什么人?”
林花爽快的摇摇头,裂开嘴笑起来,牙齿白的晃人眼睛,“找啥,我躲人还来不及哩!”
“躲人?”王祝拖长了声音,像是一条无形的线,幽幽的挂住了林花的注意力,“姑娘所躲何人?”
“躲我爹呗。我爹在村里给找了个对象,是个杀猪的,我没从,就躲山上来了。”林花言语里警惕渐渐淡去,握住斧头,低下头继续削,“你呢?你干啥到这山上来?”
王祝语气淡淡,话锋一转,“你爹给你找好了婆家,为何要躲他?莫非你爹对你不好?”
“我爹对我是挺好,但我外婆嫁给杀猪的,我妈嫁给杀猪的,我可不想再嫁给杀猪的了。”林花没有抬头,手握斧头忙个不停,木屑飞舞,“倒是官人你,好好的日子不过,到这山上受苦干什么。”
“性情使然。”王祝一句话掐断了两人继续聊天的心思,王祝阖上眼睛,不知道在小憩还是在假寐。
天上的云朵变幻着形状,太阳慢慢升上了最高点,日光像从天上倾泻下来的大水,让人避无可避,林花手里拿着削完的鱼叉和斧子站起来,摸了摸有些酸了的腿,乌黑的头发被晒的滚烫,掸了掸自己身上的木屑,转身走进了屋里,乒乒乓乓响了一会儿。
须臾,林花手里拿着锅具从小屋里出来,蹲在草地上生起了火,舀了一些潭里的水,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林花煮了一点野菜和面条,在锅边上又生了一堆火,随手在树上折下几个树杈子,架在火上,开水褪了野兔的毛,串在树杈上在火上烤,不停的转动着,撒上点作料,不一会儿,香味弥漫整个山腰。
王祝的眉毛跳了一会儿,慢悠悠的睁开眼,“林花?”
“做啥?”
“野兔盐搁少了。”
“嗨,不可能,我一洒一个准。”
“盐少了。”
“真没少,不信你尝尝?”
王祝站起来,悠闲的拂了拂衣服大步走到野兔面前,手指掂住野兔肋骨旁一块烤得脆脆冒着油的兔肉,在林花发出“小心烫”的惊呼之前巧妙的一撕,在嘴边吹了吹,放进了嘴里。
林花抬头看着他,王祝站的位置逆光林花看不清他的表情,更不用说看不见他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不得不眯着眼睛问他,“怎么样?”
“盐少。”
“真的?”
“嗯。”确信的,云淡风轻的口气。
林花弯腰拿了盐罐,要往野兔上洒盐,却王祝轻巧地按住了。
“或许单单只我吃的地方味较淡,野兔腹部的肉较难入味,我尝尝。”
王祝伸手,被林花抓住了。
“公子在逗我哩?明明是想吃了不好意思说,客气甚,想吃就一起吃呗。”林花憨态的脸上露出促狭的神情来,王祝被说得一怔,点点头,“那就叨扰了。”
“客气,客气。”
王祝在林花旁边坐下,自然风流里带着点潇洒和落拓,林花有点儿不好意思,“公子你是想吃点野菜面还是野兔肉?”
“不劳烦了,我自己动手。”
“行,这样自然是最好的。”
林花点点头,自己忙活开了,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林花把野菜放进水里烫了烫用筷子夹了出来,环视四周找不到碗,拿手肘捅捅坐在边上撕兔肉的王祝。
“你帮俺去屋子里拿口碗呗,野菜不出锅一会儿要烂哩。”
王祝点点头,站起来闲庭信步般往木屋走去,过了一会儿,一手抓了几个碗出来,“这个?”
“对,放前边。”
王祝搁下碗,林花把野菜往碗里里一铺,端起来递给王祝,“公子给你吃吧。”
王祝咬了一口,默默的把野菜吐了出来,“无盐?”
“自己加吧,盐罐子在边上。”
王祝手指掂了点盐,举高撒在野菜表面,翩翩公子动作优雅风流,只是粗盐稀稀拉拉的落在碗里,完全没有均匀二字可言,林花给自己捞了点面,端着碗,另一只手伸进盐罐里抓了一把粗盐,一个淡淡的视线锁住了她的手。
只见林花食指和中指轻巧的用力,向左右一捏,一抿,粗盐沙沙落下,成为细盐,像一阵烟雾一般撒在面条上,落在面条上有如雪花落在地面消失了踪迹。
收回目光,王祝神色淡淡,咬了一口野菜,在嘴巴里细细咀嚼良久,吞咽了下去。
林花放下碗到木屋里取了两双筷子,递给王祝一双,王祝点头致谢,接过筷子放在碗上。
林花拿筷子,麻利地搅拌着面条,余光里见王祝已经吃完了野菜,扬扬手里的碗,“再来点儿面条不?”
“腹中空空,就不推辞了。”递上了自己的碗。
“客气了,出门在外总有难事,能帮上忙也是我的福气。”
林花往王祝碗里拨了大半面条,自己随便吸溜了一会儿,撕了一条兔腿就端着碗离开了。
王祝吃了面条,把碗往边上一放,挑了个阴凉的地方坐下,双手置于脑后眯着眼睛渐渐睡着了。
醒来已是霞光漫天。
王祝悠悠转醒,忽觉口渴,踱步至潭边,见潭水清冽,双手捧了浅浅喝了几口,觉得舒服不少,王祝望向山下,炊烟缓缓从小镇向上升起,鸟儿归巢,樵夫负柴回家,身边跟着一只狗兴奋地吠了一路。王祝闭上眼睛,进入了遐思。
脚步声惊扰了他的思绪,鸟儿从林中飞起,林花沿着山路喘着粗气回到潭边,身上扛着体积远超过她的柴火,脖子上挂了一条用于擦汗的粗布。放下柴火,林花发现了站在树下的王祝。
霞光映红了王祝如玉的脸,王祝站在翠劲树下,眉目如墨,衣袂轻扬,身材颀长,气质清朗,分明是幽静如画景色,却在霞光映染下像是一幅带着生机山水画。
景致是自然天成,人也是自然无暇。
“公子住在哪儿?离这里可近?眼见着天色不早了,再不回,山路难走,一会儿怕是不好下山哩。”
王祝没有回答,垂眼,侧身望向渐渐红润云彩,绛红色火烧云上如同奔腾着一只烈焰燃烧中挣扎前蹄高高腾起的骏马,云朵慢慢推移变幻,王祝岿然不动,只留下一个清润舒朗的背影。
林花见他没有回答也不惊扰,自顾自把鸡鸭赶到木屋前从布袋里掏出谷子一边撒一边唤鸡鸭来吃食,忙活了好一会儿,鸡鸭吃得饱饱的,打着满足的饱嗝走开了,林花走进木屋里拿出锅具,重新生起了火,林花手里拎着两尾从潭里叉起的鱼串在木枝上烤了起来。
太阳喷薄出消亡前最璀璨的一抹如血流金,慢慢淹没在无尽变幻的厚重云朵里,暮色四合,在静谧的暮色里能分辨的只有虫鸣与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王祝在灵珠潭边石头上坐下,半边面容湮没在暮色里,一半被火焰照亮,光在沉静的面容上跳跃,王祝垂眼,长长的睫羽在眼底扫下一大片阴影,林花只瞧上这么一眼就怔怔的忘记了自己要做的事。
王祝斜了一眼呆愣的林花,嘴角勾起意味不明的浅笑,光彩在他黑亮的眸子里流转,“姑娘看着我作甚?”
林花见王祝看向自己,有点不好意思的偏过头,视线扫及手里的烤鱼,“公子还未吃饭吧?我这里还有条鱼。”
“承蒙照料,王某不客气了。”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林花往左边挪了挪,腾出块儿地,让王祝坐,王祝倒也不讲究,大大方方坐在林花边上,颀长手指过林花手里的鱼吃了起来。
“公子为什么不回家?”
“无家可回。”
“为啥不下山呢?”
王祝如同没有听闻一般,垂眼自顾自颔首吃鱼,林花又问了一遍,还是没有回应,过了半晌,“姑娘为何不早日回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本就是女子归宿。”
林花也不答,权当没听到自顾自吃鱼,过了一会儿还是开口,语气里竟是满满的疲态,“谁说不是呢……”半晌,又道:“我明天下山看看,我爹身体不太好,这几日我不在家,怕是很操劳哩……”
王祝沉默了一会儿,才幽幽答道,“趁父母亲健在多尽尽孝道,日后才不会后悔莫及。”
林花微一颔首,站起身,收拾了碗筷,在木屋里忙活约莫一个时辰,林花出了木屋,走到王祝面前,递上一个布包。
“这是条薄布,晚上冷,披上了也防蚊虫。”
王祝接过,“多谢。”
林花转身进了木屋,木门轻轻阖上,发出悠长的一声“吱呀”,像一声浅叹。
王祝披着薄布在树下斜坐,阖上眼,浅浅小憩,木屋内没有任何声息,鸡鸭被关进了鸡圈里悄然如梦,蝉鸣渐渐褪去,夜深了。
月明。
王祝忽闻身旁有窸窸窣窣的响动,一瞥,身旁一只小黄鸡在王祝身上找到了最佳入寝位置,把头埋进王祝胳膊内侧,惬意睡去,王祝摸了摸它小巧的脑袋,阖上眼。
木屋内偶有啜泣声,只是声音太轻,还没来得及飞,就在拽进夜空,就在紧紧拽住被角的拳头里消失了飞行的力气。
一宿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