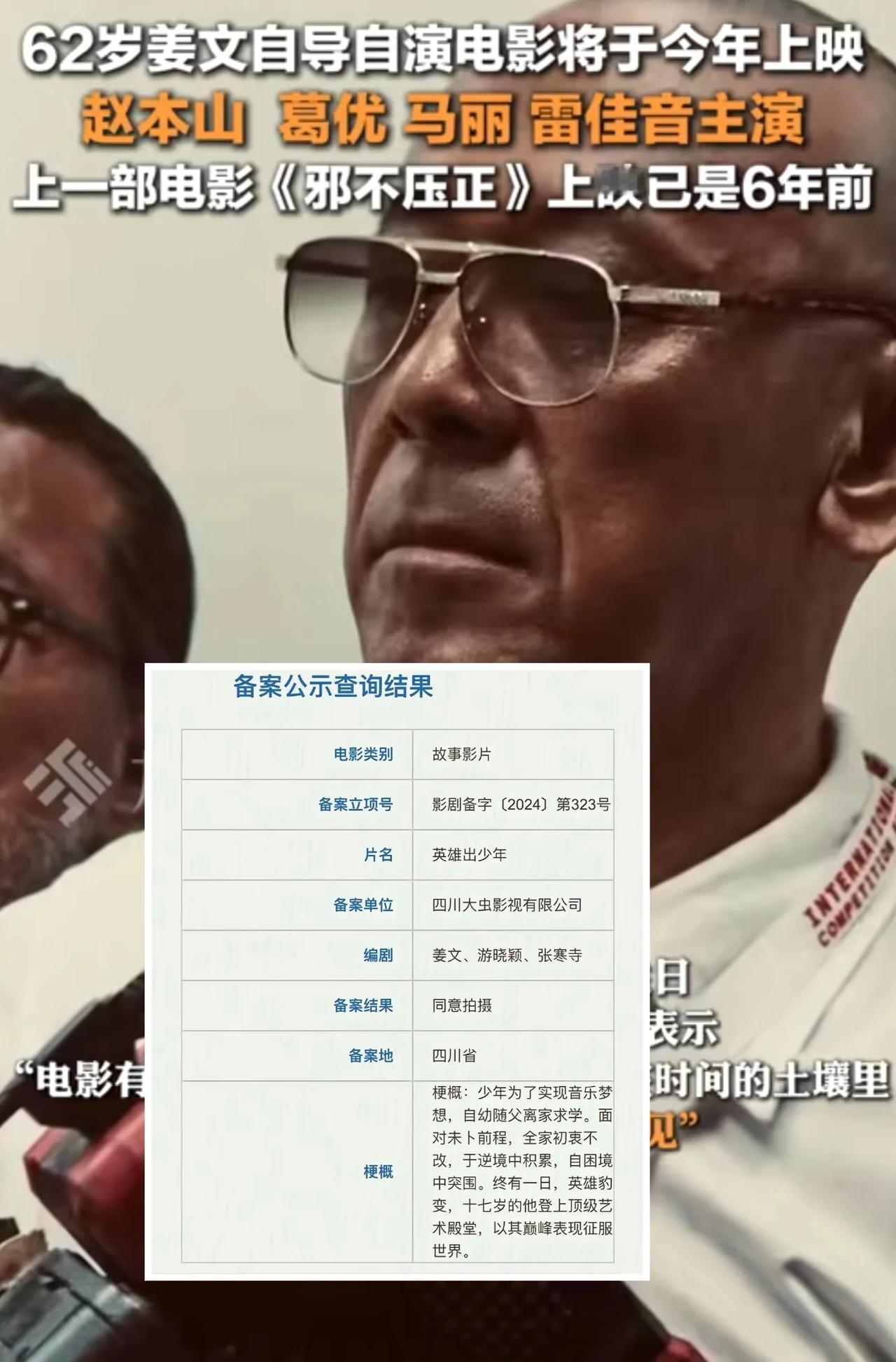两位各自拥有相同名字的男女,在三个不同时空中重遇,他们相爱、相恨,将《野兽》剧本落在其他导演手中,大概只是一部言情与浪漫并重的爱情电影。但贝特朗·波尼洛并不是安守本份的创作者,他总是要给观众出其不意。
《野兽》借用人工智能为设入点,探索人与人情感的力量,改编自19世纪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The Beast in the Jungle》。巧合的是,今年先后有两部电影改篇这本小说,并将十九世纪的故事拉到现代环境,波尼洛的版本由2044年的未来巴黎开始,未来有一个叫净化人类的情绪程序,消除情感世界,为了让人类更有效率,能够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好,而不会受到讨厌的情感阻碍。

蕾雅·赛杜饰演的Gabrielle为了克服压抑的情绪报名参加了这个项目,并因此追忆了她可能来自前世的记忆,1910年大洪水期间的巴黎与2014年地震后的加利福尼亚,在每一段前世的记忆中,她都发现自己被一名叫Louis的男子吸引。1910年的段落,讲的是一段婚外情,男女主角互相吸引,但腼腆地拒绝承诺,因为Gabrielle认识Louis 后,一直被灾难的景象所困扰。上半部分可以说是对原著忠诚地改编,展现了波尼洛扎实的戏剧功底。两人无法压制的情感,形式上最诱人,也充满了不幸的浪漫主义场面,两人的爱情无法容下时代,这是电影中最令人感动的片段。
下半段像一个Double Bill的形式,进入了另一种类型,用惊悚电影重写原著中的孤独、命运,爱与死的命题。一个多世纪后的2014 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带来灾难的就是Louis,他是一位富有但孤独、大肆宣扬男权的独身者,他因为一直无法结识女性,活在越来越疯狂的怨恨里。2014年的Gabrielle 是一位从法国只身到美国的模特儿,两人在充满敌意、陌生的城市里漂泊,Louis看上了 Gabrielle,跟踪她并想方设法去接近她,Gabrielle 好像意识到她们曾经在前世中相遇。但善意的回应并没有安抚他的仇恨和精神错乱。

从结构上来说,两段故事并没太多相关之处,波尼洛交错三条时间线以制造相连的关系:无论活在哪一个时空中,都无法排解孤独,就算能够亲近,悲剧还是会发生。影片的前半部分在过去和现代、未来的片段中切换,而近在眼前的2014年,则采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叙述,尽量完整地表达出来。很多时候波尼洛关注的不是两位主角的情感,而是媒材制作的疏离。2014年的段落有大量的监视镜头,Gabrielle向网上的占卜师求助,从电脑中看到的占卜师房间就像《双峰》里红房子的翻版,每当占卜师出现,电影中的不安气氛就在增加。加上Louis仇女的言论,环绕在Gabrielle现代大都会生活中的是随时夺命的气氛。波尼洛过度理性的色彩往往让观众无法完全投入电影的情感,但同时也在提示两人宿命般的相连,在1910年的段落,当两人热情爆发时,又立即拉回到2044年冰冷的巴黎,节奏不停受到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蕾雅·赛杜的表演,她非常投入其中,焦虑与热情并重,让电影不至于过分冰冷。她的面孔和情绪变化,是电影中引人入胜的地方,亦让观众迷醉。电影的结构也像一篇讽刺、冷漠的散文,当我们陷入时代之间的空间时,它是对人类磨损心态的评论,但《野兽》也像导演前作《昏迷》 一样,给予了现代科技世界的状态肯定。

正如前文所提及,波尼洛对未来的不安感源于人类过多对环境的影响,他可能是少数对科技环境保持正面态度的导演。这也与他精美的视觉品味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视觉元素虽然有冷酷感,但他依然保持了一份幽默感。《野兽》之所以感人,是它不自欺欺人地认为过去的情感才是美好的。当然,电影有怀旧的一面,2044年的场景出现了两个模彷七八十年代的舞场。他肯定当下的情感,在科技越来越影响人们生活的当下,情感依然可以发生。
无论是1910年、2014年还是2044年的互相追逐,电影在不同的情绪之间摇摆,无论是美学、形式还是主题,时空不停穿插的叙事方法如果只定义为取消了戏剧性那未免过于狭隘,它同时保持了爱,以及对当今时代的恐惧。电影可以说是对未来的敌托邦式的想象,但恐惧感并非来自科技的敌意,而是来源于人类慢慢失去热情、情感这一问题。在充满敌意的大都会与旧时代的压抑中,男女主角在无数梦境和幻想的场景里,探索痴迷所带来的疯狂,这是一部关于坠入爱河恐惧的轻科幻电影。

《野兽》带有警示意义地讲述着人们变得如此害怕被拒绝的情感,以至于消除了任何情感时,世界将要面对即将发生的可能。当要彻底遗忘投入情感所可能带来的美好与伤害时,也让每个人都步向真正的死亡。《野兽》跨越时空,在人类失去情感这一想象为时已晚之前,在美丽的旧创伤和未实现的焦虑中展现人类的日常情感。电影注定不会讨好大部分人,这是一部两极分化的电影,意见分歧很大,有违背观众的期望,但强烈的作者色彩,与过去被指责过分隐晦吓怕观众的前作《僵尸儿童》和《夜行盛宴》不同,《野兽》让人们重新关注波尼洛,甚至赢取不少影评人的欢心。电影原计划由蕾雅·赛杜和加斯帕德·尤利尔合演,最后,电影也写出向这位不幸早逝的演员作最后致敬,不禁要想,如果由加斯帕德·尤利尔演出,《野兽》又会变成怎样?
蕾雅·赛杜和乔治·麦凯主演的反乌托邦新作《野兽》在威尼斯首映后外媒口碑出炉,超过石头姐的《可怜的东西》获得场刊评分3.71全场最高分!目前烂番茄新鲜度85%(13评11鲜2烂),MTC是81分(7评6好1中0差)。
《Inverse》影评人Lex Briscuso(Fresh):《野兽》穿越了时间向我们展示了对爱的恐惧(伴随爱而来的高潮可以瞬间落到最低的谷底)可以像彻底不爱一般具有毁灭性。
《Daily Telegraph (UK)》影评人
Robbie Collin(Fresh):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波尼洛在影片中设计的那些充满漏洞的小笑话……但或许他希望我们把这部电影当作那个撕裂的女主角一样去看待:一个自我灵魂拒绝放弃的奇怪机器。
《Next Best Picture》影评人Josh Parham(Rotten):影片想表达的主题或许具有内在价值,但执行得却如此过时而无趣 。演员们都竭尽全力地在演,但只有赛杜对于拔高整部作品的质量起到了一些作用。
《The Guardian》影评人Peter Bradshaw(100/100):《野兽》或许不会对它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令人信服或者彻底的批判,但的确提供了一次相当珍贵的观影经历;它是伴随着锐气和批判意识所创作出来的,而配乐放大了那种恐惧的悸动。
《Screen Daily》影评人Jonathan Romney(80/100):电影中的三条主线都各有优缺点。但最有趣的是故事的叙事方式,无论是剪辑师安妮塔·罗斯的交叉剪辑还是影片在视觉相似性上的建立。
《Variety》影评人Guy Lodge(60/100):《野兽》充满了极具吸引力的想法和画面,然而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张力,结果就变成了一部长达146分钟的厚重的三联画,普通且令人烦躁。此外,电影还把工作敬业的蕾雅·赛杜和乔治·麦凯捆绑在一段跨时空、互相误解的关系之中,两人的关系一直不断地变化,但却没能使观众深深共情。

贝特朗·波尼洛(Bertrand Bonello)导演的影片《野兽》上周日(9月3日)在威尼斯电影节进行了首映。我们迎来了一对牛郎织女恋人的故事。在三条时间线上,这对恋人试图产生情愫,却以失败告终。从1910年、2014年到2044年,这部电影将时代变迁、科幻推理与阵阵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相结合,尤其体现在发生于当代洛杉矶的第二个部分。
于此,抱负远大的女演员加布里埃尔(蕾雅·赛杜饰)引起了路易斯(乔治·麦凯饰)的注意。路易斯自我定义为极度厌女的Incel[译者注:involuntary celibate,非自愿独身者,通常为男性,他们尽管拥有着强烈的渴望,但因各种客观原因无法进入浪漫关系或寻求性伴侣]群体一员。波尼洛创作这个角色的灵感来源于埃利奥特·罗杰(Elliot Rodger),2014年某个案件中的连环杀手。在夺走了七条人命之前,他在YouTube上上传了一份厌女的宣言。波尼洛在影片中一字不差地重现了当年罗杰这段臭名昭著的影像。
Variety杂志与Cineuropa杂志对贝特朗·波尼洛进行了采访。


Q:您为什么选择引用埃利奥特·罗杰的事件?
波尼洛:当我在2014年了解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和所有人一样都被这一场骇人听闻的袭击震惊了,但对我个人而言,更令我震惊的是他所说的那些话,所以我将它们记在了我的记事本上。那些言辞看起来如此正常、平庸而冷静,因此震撼人心。这是最触动我的点,也是我希望在我的写作中通过改编来表达的。也因此,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回顾了我在笔记本上记下的内容。
Q:您会因为将这样一个人物戏剧化而感到不安吗?
波尼洛:我想过,我想过。但是,不像真正的埃利奥特·罗杰,电影中的这一角色并不是一个大屠杀杀手。我更感兴趣的,是他被压抑的欲望。我从没有机会用如此强烈的语言来表达这一切,没有什么比这段自拍独白更震撼,直面人心、触及观众。显然,当你从现实中寻找灵感的时候,你必须要承担一些风险,但与此同时,你必须意识到这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Q:是什么深深地吸引了您?
波尼洛:我对美国电影界创作的这一类在凶残外表背后寻求庇护的人物非常感兴趣。Incel社群,尤其是他们所展现的暴力吸引了我。这些非自愿独身者最初接受了暴力,然后选择将暴力送还。这是一种时代与社会关系造就的大症候。

Q:您最初为加斯帕·尤利尔创作了路易斯一角。而在他不幸去世后,您不得不重新选角。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译者注:波尼洛最初于2017年就开始了这部剧本的撰写,由于疫情的影响,拍摄计划不断被推迟。原定的开拍时间为2022年4月,但不幸的是,尤利尔于2022年1月在一起滑雪事故中去世]
波尼洛:我们当时立刻就意识到,我们不能再起用一个法国演员,因为我并不想产生任何和加斯帕的比较。所以我当时给一个美国选角导演打了电话,找到了乔治·麦凯。我几乎没有改变剧本的任何内容,除了我让剧本的第一部分(1910年的片段)变成了一半法语、一半英语。我觉得产生这样语言的混杂会十分美妙,这些人物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是欧洲人,这给电影带来了有趣的音乐性。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它变化。

Q:您是如何建构电影中2044年片段的独特视角呢?
波尼洛:其实这是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它离我们只有20年。在20年内,大多数我们现在生活的建筑仍然会在那里。在科幻小说里,我们常常见到超现实的机器或后末世的景观。任何晦涩或末日般的世界都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基于我们身处的日常,我并没有做加法,而是做了减法。在未来世界里,没有汽车,没有走在街上的人,也没有互联网。我想要通过一种和科幻小说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方式,来创造一种贫瘠的、我们从未见过的景观。

Q:《野兽》混合了历史叙事、惊悚和科幻小说的元素。您有通过某些电影来获取灵感吗?
波尼洛:我非常喜欢When a Stranger Calls这部电影[译者注:同名有2006年西蒙·韦斯特导演作品《来电惊魂》与1979年弗雷德·沃顿导演作品《惊呼狂叫》,前者为后者的翻拍作品。不知波尼洛具体所指],这是一部很难找到的B级片。但对于影片的大多数部分来说,相较于去寻找参照,我试图去尊重并“劫持”某种准则。我尊重恐怖片的准则,但会用些许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同时我也针对浪漫历史剧的创作法则进行了改变。我这一代人可以同时喜欢罗伯特·布列松和达里奥·阿基多。只要真正的电影制作参与进来,那都别无二致。
Q:但您确实对恐怖片情有独钟。
波尼洛:作为一个观众,我更愿意时刻紧绷而非被感动。我最珍视的就是戏剧张力。如果一部电影没有创造任何紧张氛围的话,那这位导演一定在某个方面出了错。

Q:看起来您的前一部电影《昏迷》(Coma, 2022)似乎是一场为《野兽》做的实验?
波尼洛:确实。因为《野兽》被疫情延迟了进度,我和我的制片人觉得我们得找点事干,所以我们创作了《昏迷》。我们决定创作一部非常、非常、非常低预算的电影,因而它不可避免地是我对《野兽》这个更宏大的项目的痴迷的延伸。
Q:两者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厄运将至的预感,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波尼洛:近几年,我们见证了灾难的加速到来,尤其是生态方面的,所以如今有一种二十年前并未有的意识,虽然这种意识毋庸置疑仍然是不够的。这将我们引向了我们自身的观念问题。我们应该清楚地面对这一切,抑或选择避而不谈?你最终会发现自己兼而有之:先面对它们,然后试图转移自己的视线。在任何情况下,当我们面对大灾难的时候,我们重新获得了自身的人性,并试图寻求解决方案。如果没有问题,就没有答案。如果没有答案,就没有了生活。

Q:您的作品里,女性角色无处不在。
波尼洛:在《妓院里的回忆》(L'apollonide,2011)里,我已经拍摄过女性的群像。我也拍过一些其他的女性角色,但从未有过如此核心地出现在每一个画面中的。这也是为何我选择在一个绿色的背景前开启了这部电影。这是一种表达方式:看,我的主题就是她,是加布里埃尔,也是蕾雅·赛杜。这并不是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但观众能观看到她的每一个角度。

Q:为什么蕾雅·赛杜如此特别?
波尼洛:我们已经合作过两次,但当然,不是以如此大的比例参与。首先,于我而言,蕾雅是唯一一位可以同时出现在这三个时期的人,因为她身上有着一种现代性与永恒感。但最重要的是,她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东西:她有一种神秘感,我们无法了解她心中所想。对于镜头而言,这如此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