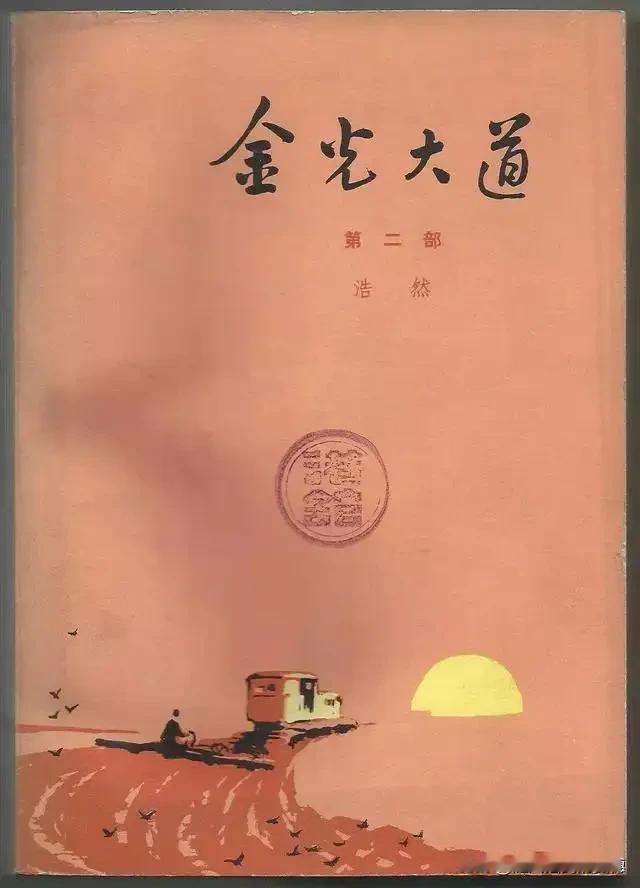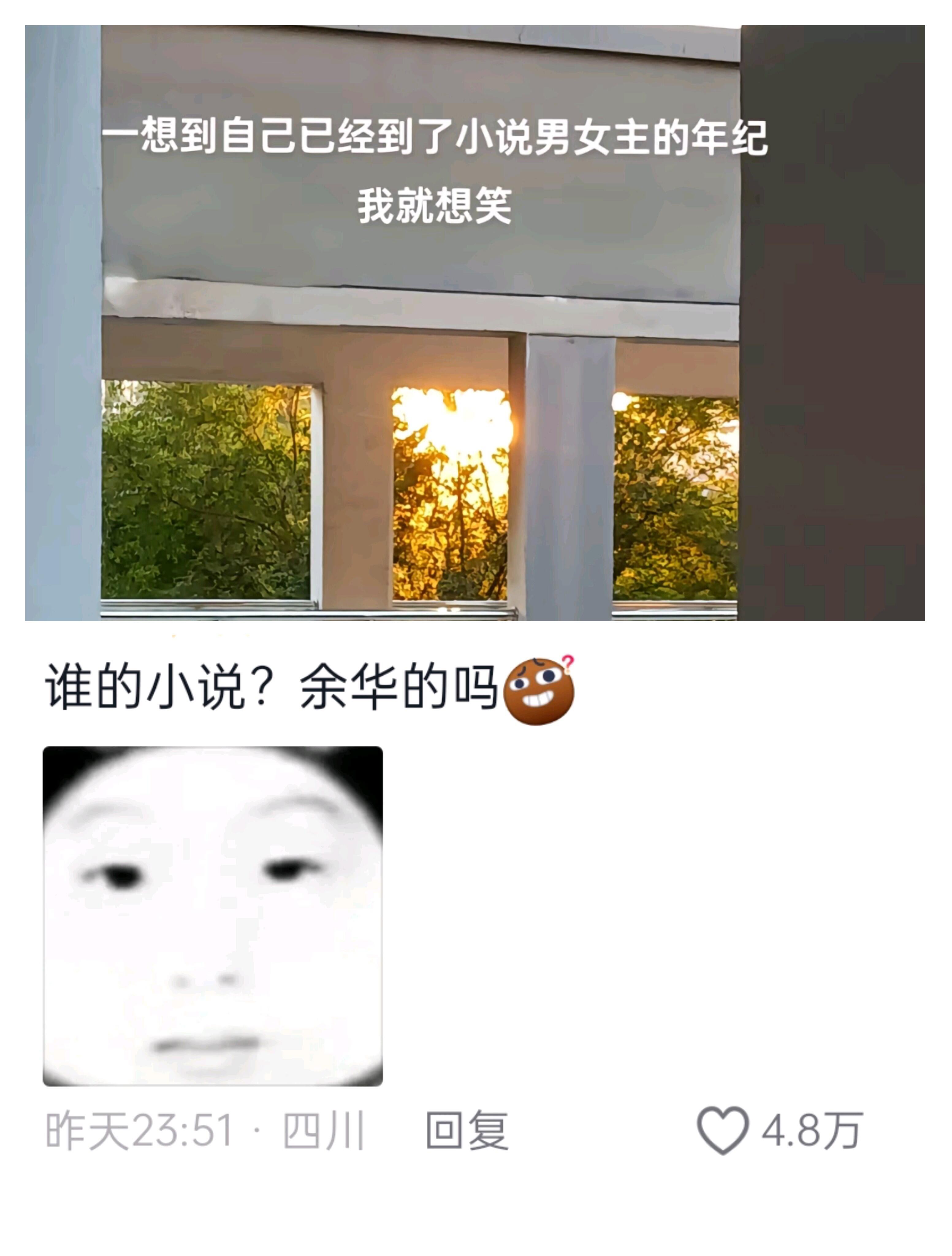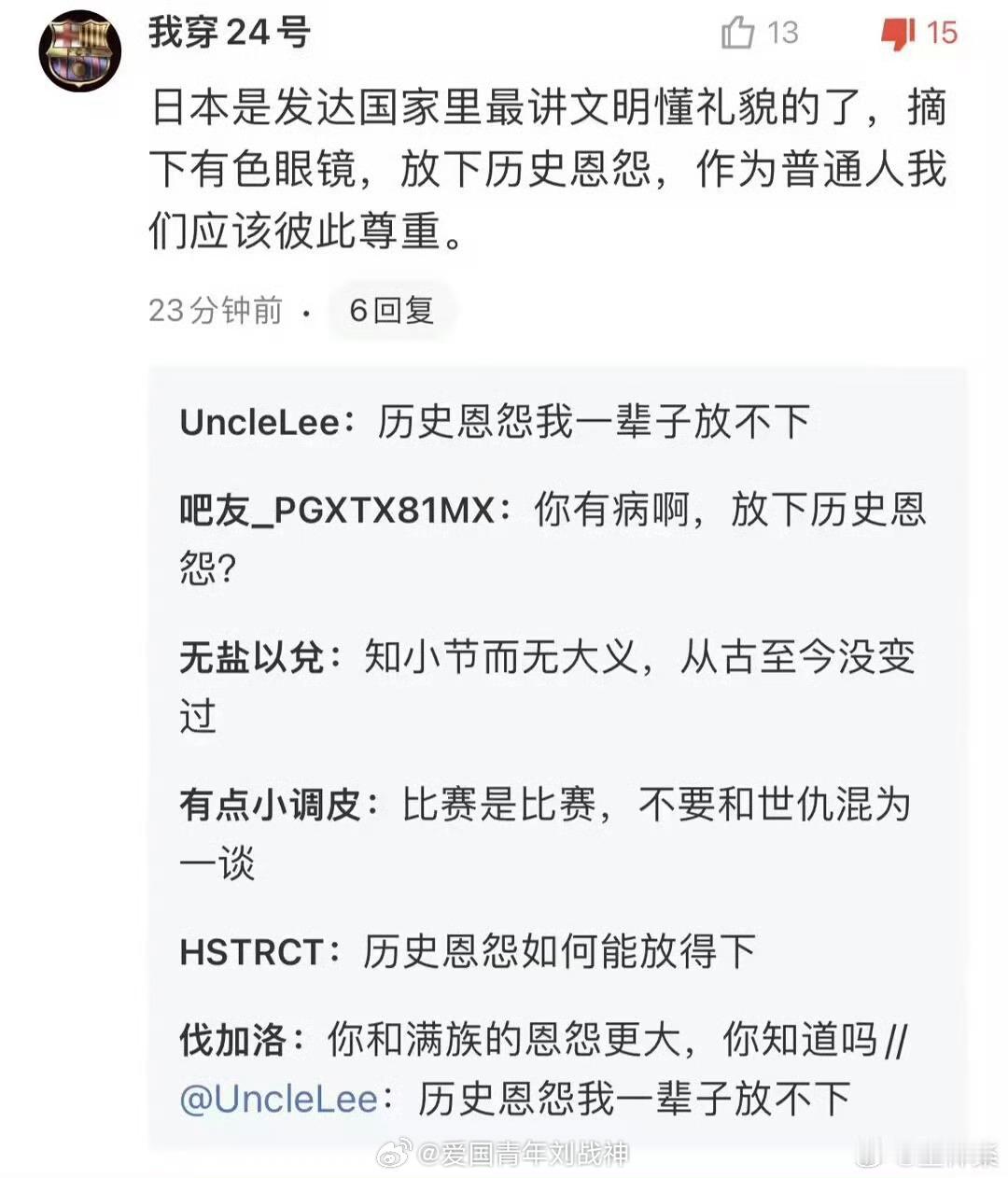当年《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胡锡进的深度访问记——《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这篇报道以浩然撰写《十年回忆录》的动机为引子,全面揭露了浩然的几个令人震惊的观点。浩然直言不讳地表示:“迄今为止,我从未为以往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感到后悔;相反,我为之骄傲,尤其钟爱《金光大道》。我认为在‘十年’那段特殊时期,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所贡献的。”他甚至自称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迹”,此言一出,立刻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采访浩然先生的过程中,他对于“文革”那段特殊岁月里所采取的独特躲避策略,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那些文艺界的老前辈们常常感慨,在那个“文革”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迷雾中,江青身处那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使得许多人难以抵御那股诱惑与盲从的洪流。在那样一个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浩然先生也不免犯过一些错误,说过一些不当之言。然而,他内心深处始终怀揣着对创作的热爱与执着,一心想要为自己开辟一片纯净的创作天地。为此,他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应对策略。 他多次向我坦言,自己实在无法适应官场的那一套,仅仅是在圈外旁观,还能勉强保持一份清醒;一旦踏入那个圈子,便觉得窒息难耐。开会时不仅要记录繁琐的议程,甚至连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都要被记录下来。他心想,只要得到江青的重视,或许就能避免被整肃的命运,从而安心地投身于创作之中。他深知,想要在官场与创作之间摇摆不定是不可能的,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 为了躲避上级派下来的繁琐任务,浩然先生甚至不惜隐姓埋名,跑到偏远的延庆去寻觅创作的灵感。在那里,他过着简朴至极的生活,每天到村里的供销社解决温饱问题,晚上则躺在卫生所的病床上构思他的作品。这种对创作的痴迷与执着,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叶嘉莹先生曾对浩然的《艳阳天》等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们不仅蕴含了强烈的政治目的,同时也展现出了浩然先生真挚的情感与深邃的思想。然而,将作品中的政治信仰直接等同于浩然先生的人格与品质,未免有些过于武断。这样的分析,显然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情感与主观臆断,而非基于严谨的学术分析。浩然先生自己也曾坦言,他深知农民的艰辛与不易,也亲身经历过那些饥饿的岁月。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那些真实的苦难与挣扎,在当时是无法被如实写入书中的。因此,我们不能仅凭作品中的政治倾向就妄加判断作者的人格与品质。 除了《金光大道》,创业史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佳作。它以开阔的视野、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与矛盾冲突。小说不仅描绘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波澜壮阔,还触及了城市私营资本的改造等社会变革的多个层面。每个人物都被卷入了这场历史洪流中,他们的迷茫与绝望、挣扎与奋斗,都被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得淋漓尽致。 此外,《创业史》在人物行为描写与心理刻画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者以精炼而准确的语言,生动描绘了人物的行为举止,使得每个角色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同时,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也颇为成功,不仅主要人物如梁生宝、梁三老汉的心理活动被刻画得细腻入微,就连次要人物如梁秀兰与杨明山的恋爱心理也被描绘得层次分明、细腻动人。 再来看贾平凹、孙惠芬等当代作家的写作困惑,他们作为“乡土作家”的代表,面临着“乡土文学”与“底层文学”相遇后产生的新挑战。这些作家出身乡土,长期以来以乡土生活为创作源泉。然而,随着乡村的变迁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他们不得不跟随笔下的人物一同进城,从熟悉的故土踏入陌生的城市世界。这种转变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惶惑与茫然。然而,在这份惶惑与茫然背后,我们却能看到他们难得的诚恳与坚持。他们不愿意停留在过去的乡土记忆中重复讲述旧故事,而是勇敢地将自己熟悉的“乡土写作”推向“底层写作”,从而揭示出“底层写作”中存在的深层问题。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及《创业史》的“题叙”。这部分内容被誉为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作者最为满意的部分。柳青先生曾坦言,如果全书都能达到“题叙”的水平,那他就心满意足了。新日本出版社在翻译出版《创业史》时也对“题叙”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引领了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新高度。时至今日,“题叙”依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读者与学者。那么,“题叙”的写法究竟源自何处?它的精彩之处又在哪里呢?这或许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