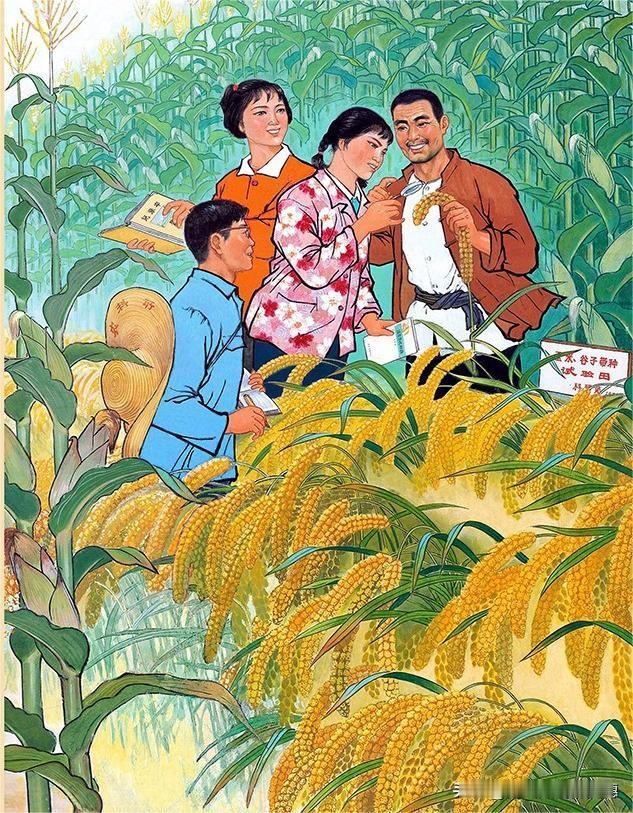陈永贵看到对大寨的的批判之后,长长地叹口气说:“唉,老虎吃人能躲闪,人吃人可躲不了啊!”事实上陈永贵对万里在安徽开展的的包产到户很不理解,曾在一次会上针对一张报纸报道的安徽包产到户经验提出不同看法,并主张昔阳不能搞。对当时社会上对毛主席的评价更不服气,说他们对毛主席不公道,三中全会精神要落实,但不能因为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就歪曲毛主席的形象。因此,面临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中心工作,陈永贵一方面左的思想还很浓厚,另一方面他确实看不惯一些人对毛泽东主席的非议。 包产到户曾经历经波折,终究被时代验证。 1961年3月,曾希圣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拂过了江淮大地。文件开篇便以设问的形式直击人心:“一、为何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而回答这一问题的首要理由,竟是“源自宿县一位老农的朴素建议”。 这位自食其力、勤劳智慧的老农,在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历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的名字、他的事迹,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如同江淮大地上的一曲赞歌,被无数人口耳相传,家喻户晓。然而,在“责任田”遭遇误解与纠正的波折中,这位老人却又被错误地贴上了“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签。1962年10月,有人受命对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撰写了《所谓“责任田”的建议者刘青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调查报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在转发这份报告时,所加的“编者按语”竟称:“刘青兰过去是个不务正业、品质不好的人,办合作社以后,就上山搞单干。”这一评价,无疑是对老人莫大的误解与不公。 时光荏苒,到了1982年11月5日,万里在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让人豁然开朗。他说:“农民最高兴的两件事,一是实惠,二是自主。过去我们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瞎指挥,大呼隆,结果生产上不去;现在农民有了自主权,可以独立组织生产,安排活计,结果‘集没有少赶,戏没有少看,粮没有少打,钱没有少得’。 有些先进队为什么也愿意搞联产承包制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利益增加了,自主权更多了。有了物质利益和自主权这两条,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成为发展生产的巨大力量。”这番话,虽然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形势发展变化的深刻剖析,但其所揭示的农民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热烈欢迎与拥护,其本质原理同样适用于解释集体化时期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深厚情感。 与农业集体经营制度相比,包产到户以其独特的制度机理,巧妙地调整了农业生产关系,赋予了农民可观的物质利益和一定程度的身心自由。这种自由,正是农民对包产到户制度情有独钟的关键因素。农民,这个看似平凡的群体,实则精于算计,善于把握机会。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言:“农民是理性的。”包产到户后,他们虽然吃饭有了保障,但并未满足于仅仅填饱肚子。为了增加收益,他们绞尽脑汁,寻找各种获利机会。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农民必须拥有人身自由。包产到户,恰恰为这种自由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原理在于:这一制度将集体生产还原为家庭生产,使得家庭生产单位能够充分利用无报酬的空闲时间劳动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关于如何让农村产业兴旺,一个行之有效的思路是延长农业产业链,将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然而,问题在于,农产品深加工是一种市场获利行为,资本总是嗅觉灵敏,一旦发现有利可图,便会蜂拥而至。农产品加工的关键,从来不是原料的来源问题,而是加工后的市场销售问题。 因此,资本为了建立更加便于加工和销售的体系,往往会选择靠近城市的地方,并按照市场效率原则运作。这样一来,从农业延伸出去的农产品加工业,就不再是农村的产业,而是城市的产业。在这个产业中,农民只是原材料的市场供给者,或者进城成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雇工。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利润,属于资本,是资本的市场行为。换句话说,延长农业价值链、增加农业附加值,这是市场行为,与农民、农村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资本和市场紧密相连。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种增加农村产出、推动农村产业兴旺的途径,那就是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其中一提及便让人眼前一亮的便是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尤其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在当前城市中产阶级普遍怀有“乡愁”情结的背景下,一些具备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的农村,确实可以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或乡村旅游来赚取城市人的“乡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