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体制认为自己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文化,因为我们监狱里关着的人数量比农民多。为了这样的数据而感到沾沾自喜,非常可鄙。”
五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阅读乔尔·萨拉丁(JoelSalatin)的《我想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时的震撼。熟悉美国食物运动,读过迈克尔·波伦《杂食者的两难》或看过纪录片《食品公司》的读者,一定对这位边杀鸡边对着镜头嘲讽农业监管体系的美国农民并不陌生。最近,他刚刚被特朗普政府任命为农业部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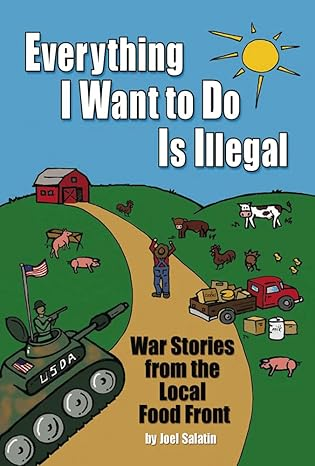
●萨拉丁和他的《我想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英文版封面。
和主流观点相反,萨拉丁旗帜鲜明地支持小农权益,他认为农业人口数量下降恰恰说明了美国农业正在衰退。
我也曾认为“远离农业”应该是大多数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直到2019年,一次健康危机和奇迹般的自愈旅程让我意识到:农业不仅是健康的根本,也是安顿心灵的去处。
1
2021年夏天,我在田纳西州的一个有机农业和食物会议上,见到了萨拉丁本人。萨拉丁从1970年代开始,就和妻子在弗吉尼亚州经营着有机农场Polyface(意为“多面”),一直活跃在美国有机农业的最前线,著书论述,指导其他有机小农的农业和政治实践。

当天,萨拉丁在演讲中痛斥了美国农业部对小农的种种打压和限制,呼吁小农积极参与立法。演讲结束后,我去找他聊天,向他介绍我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告诉他他的农业实践和农业著述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你本科是英文系的,我也是。”
我灵光一现,说:“还有温德尔·贝瑞(WendellBerry)先生,也属于我们这个Englishlitclub(英文俱乐部)。”
每个熟知美国有机小农运动的人,都不会对贝瑞先生的名字和著述感到陌生。贝瑞是获奖无数、影响深远的诗人、小说家和文化批评家。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在纽约大学教了几年写作课以后,回到了肯塔基老家,成为了一名全职农民。
如今90岁的贝瑞著作等身,其作品一直在探讨机械化大农业对人类社区、文化、心灵和身体的全面破坏。从文学走向农业的萨拉丁和贝瑞,照亮了无数立志逆流而上成为有机小农的文艺中青年的道路。
对我来说,文学的尽头是农业。文学是对人的处境的关照,而人从农业生产活动中完全脱离而造成的“异化”,是现当代人最值得关照的困境。
2
在《我想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这本书里,萨拉丁指出,在像美国农业部这种联邦政府机构的运作下,有机小农陷入了跟卡夫卡的《审判》主角一模一样的荒诞处境:一切为自己生存而努力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以合法屠宰权为例。美国农业用地分区法(zoninglaw)规定,农业用地上不能设置屠宰场,屠宰场必须是远离农场的持证设施。因此农民不能就地屠宰自己饲养的动物,而必须增加运输成本,长途运输中牲畜会经受很大的精神压力。
在屠宰场处理完的肉,如果农民想拿回来售卖,那么在法律上,农场就变成了像沃尔玛一样的零售商,必须持有零售商的执照和设施,例如必须花不菲的费用修建给客人使用的厕所和停车位。
农场主若想开放农场给学生团体买票参观,顺便为自己创收,那么在法律上,这个农场就成了一个“主题公园”,要申请主题公园的执照,又要提交一堆申请,增加一堆基础设施。
美国的技术官僚们把农业实践变成了每个环节都需要持证和监管、且和下一个环节严重脱节的工业化作业。一个想用传统方式务农、用农产品搭建本地食物和文化体系的小农,处处要接受农业官僚的审判。
萨拉丁指出,而这样的农业官僚通常“住在城郊住宅区里,吃着微波炉食品,看着好莱坞真人秀,希望农场离自己的住宅越远越好”,除了执行法律条款和规定,对农业——尤其是有机农业,一无所知。
3
这样的农业官僚更不会理解,在农场屠宰动物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能把农产品的价值都留在本地。
有一次,我的农民朋友Nancy请本地屠夫上门宰鸡,我也带上后院养殖的八只兔子,让屠夫一起帮我屠宰。
我到Nancy的农场时,屠夫Ishmael已经在做准备了。他烧了一大锅水给鸡脱毛,在草场边缘的树林里支起了一张桌子用于屠宰和切割,又在橡树树干上栓了一根绳子。
Ishmael决定先帮我宰兔子,顺便教我屠宰。只见他从装兔子的纸箱里,挑中一只兔子,捏着它的两只后腿,把它轻轻地拎了起来。
“像这样让它倒挂一会儿,血液就会都涌向兔子的头部,兔子就会发晕,停止挣扎。”Ishmael对我说。
几秒钟以后,兔子果然停止了挣扎。然后Ishmael左手拎着兔子,右手用一根现找的木棍,照着兔子两只耳朵之间的脑部快速一击,兔子就完全失去了意识。Ishmael迅速地把兔子倒挂在树上的绳子上,开始给兔子放血开膛。
“它几乎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Ishmael对我说,“重点是这一击要用力且准确。”
Ishmael宰鸡的手法同样迅速而准确,放血脱毛开膛取内脏切割一气呵成。他把宰好的鸡冲洗后放进了装着冰水的大桶里,再把内脏和血放在另外一个袋子里,这些都会被Nancy拿去堆肥,不出半年就会降解为肥沃的有机质,用作种蔬菜水果的底肥。
而在大屠宰厂,这些东西都会被当成工厂废料扔掉,进入垃圾填埋场。不能被恰当降解成有机物的动物制品,就这样脱离了生命的有机循环,成为了排放不良气体的环保负担。
那是一个初夏的午后,德克萨斯州已经逐渐炎热,几棵大树下的阴影倒是颇为凉快。四周不时传来Nancy家牛羊的哞哞叫声,我一边收拾由Ishmael给我留下的内脏和皮毛准备带回家,一边看Ishmael熟练地宰着鸡,嘴里哼唱着歌曲。
我突然觉得,比起我眼前这个自然和谐的场景,那些所谓“合法”的屠宰厂是多么荒诞:刺鼻的消毒水味,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的屠宰工人,经过长途运输而来的、处于巨大精神压力下的牲畜和动物,无情紧张的流水线作业,低廉的工资……
4
像Nancy这样的有机小农主要面向本地消费者,因此也非常乐意把钱给Ishmael等本地手艺人来赚。
我估算了一下,那天Ishmael在农场忙活6个小时,能赚400美金(约合人民币2898元)左右。而2024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大型屠宰场工人的时薪仅为18.97美元,六小时工资差不多825元人民币,还不到Ishmael所得的三分之一。
但是美国农业部规定,不在正规屠宰场屠宰的牲畜,不能向公众出售,所以Ishmael这样的使用简单工具上门屠宰的屠夫,通常只能兼职服务周围的中小农户的家用需求,很难靠自己的屠宰技术全职谋生。
一个由美国农业部认证过的屠宰场,需要少则大几十万、多则大几百万美金的资金投入。这不是Ishmael这种个体户能够承担的。
倘若一个热爱屠宰的个体户,决定贷款修建符合规定的小型屠宰场自己经营呢?萨拉丁认为,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他在书里举了明尼苏达州某小屠宰场的例子。按照规定,无论在处理肉的哪个环节,屠宰场每隔一小时就要测量和记录肉的温度。有一天,一个雇员漏了一次测量和记录,就被农业部检查员勒令扔掉这一批肉。即便此前和此后几个小时的温度记录都表明,肉并没有被污染和腐坏。这让屠宰场一下子损失了4000美金,而小型屠宰场很难在一次次执法和罚款中存活下来。
后来,一位代表大食品集团和行业利益的律师告诉萨拉丁,大型屠宰场也同样面临农业部官员的骚扰,大型屠宰场的流水线也时常发生违反农业部规定的疏漏,并不比小屠宰场“卫生”。不同的是,大型屠宰场资金雄厚,请得来律师和对方斡旋斗争。
这就是我们全人类面临的现代化困境:在这个屠宰场都只能由国际资本持有和运作的现代世界,屠夫这个古老的职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屠宰场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
在屠宰场里,屠宰变成了充斥着填补应付官僚检查文件(paperwork)的机械作业。能在劳动中获得个体尊严和意义的屠夫行业不复存在,只有流水线上拿着最低工资的屠宰场工人。
5
萨拉丁在书里说,“我希望人们感到生气,因为美国的政府把他们的集体自由和与生俱来的权利卖了,换了一碗外包给跨国企业的稀粥。”
农民、手工艺人、屠夫、厨子、磨坊主各司其职,互相服务的小社区土崩瓦解。在所有行业都工厂化、连锁店化的世界里,我们只是不同程度的流水线打工人。过去几百年来世界的工厂化,让我深刻理解了卡夫卡笔下的荒谬的现代性。
过去几年,我给每个新认识的朋友都推荐萨拉丁的《我想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它是一个从事有机农业超过半个世纪的农民对美国现有农业体制的全方位无情批判,更是给所有文明的警示。
贝瑞先生的诗歌《宣言:愤懑农民的解放前线》中有这样一句:“赞美无知,因为人类还没有遇见的东西,就还没有被破坏。”
萨拉丁的这本书也足以说明:还没有被规范化的东西,就还没有被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