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张宗昌带着母亲外出赴宴,吃饭时上来一盘荔枝。张母没吃过,不知道怎么吃,便连壳儿一起吞了下去,满桌宾客见状都哈哈大笑,张母非常尴尬。张宗昌当场没有说什么,只是将一切记在了心里。
北风呼啸的冬夜,张宗昌站在济南火车站的月台上,裹紧了身上的黑色大氅,眼神却焦急地扫视着远处。他接到消息,说母亲病重,急需他赶回老家探望。雪花落在他的肩头,化成水渍,顺着衣缝渗透进去,他却浑然不觉。
身边的副官小心翼翼地提醒:“大人,车还有半小时才到,要不您先回车厢暖和一下?”张宗昌摆摆手,声音低沉:“母亲病了,我哪有心思休息。”谁也没想到,这一夜,竟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站。
刺客的枪声划破寂静,他在慌乱中倒下,鲜血染红了月台上的积雪。母亲的病,是真是假?刺杀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阴谋? 这不是张宗昌第一次为母亲奔波。多年以前,他还是个穷小子时,母亲侯拴妮就带着他逃离了那个嗜酒好赌的父亲。
母子俩相依为命,风餐露宿,乞讨为生。那时的山东,战乱频仍,田地荒芜,穷人连一碗糙米粥都喝不上。侯拴妮膀大腰圆,性子泼辣,为了让儿子吃饱,她甚至干过拦路抢食的勾当。那一次,她藏在大树后,手里攥着一根粗木棒,眼见一个男人提着一袋馒头走来,她咬咬牙冲上去,一棒子砸在那人后脑勺上,抢了馒头就跑。
回到破屋,她气喘吁吁地把食物摊在桌上,等着丈夫回来分食。谁知丈夫一进门,揉着后脑勺骂道:“今天真晦气,弄到点吃的还被人抢了!”侯拴妮愣住,随即哈哈大笑:“这不是巧了嘛,抢你的就是我!”丈夫却沉下脸,冷冷甩下一句:“咱家再穷,也不做这下三滥的事,你走吧。”她没多争辩,收拾包袱,拉着年幼的张宗昌头也不回地离开。
从那天起,母子俩的苦日子就没停过。 张宗昌长大后,母亲咬牙送他去私塾念书,可他脑子不在书本上,十五岁就跑去闯关东,干过放牛、挖煤的苦力,后来投了军,才一步步爬到北洋军阀的高位。日子好起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副官回老家找母亲。那时的侯拴妮已经改嫁给一个姓王的鼓手,日子虽清苦,却比乞讨时强些。
副官找到她时,她正坐在院子里缝补旧衣,听说儿子当了大官,先是眼眶一红,随即摆手:“我这辈子吃够了苦,现在老王对我好,我不能扔下他。”副官没法,只得回去复命。张宗昌听后沉默半晌,提笔写下一封信,字迹歪歪扭扭却情真意切:“娘,儿子有钱了,您和王大哥一起来享福吧。”信送到那天,侯拴妮攥着纸,手抖得厉害,最终点了头,和王鼓手一起投奔了儿子。
张宗昌对母亲的孝心,从不藏着掖着。他当上山东督办后,带着母亲四处赴宴,恨不得让全天下知道,他如今有能力给她最好的生活。可有一次宴会,却让这份孝心蒙上了阴影。那是个春日,济南城里的大户人家摆下酒席,张宗昌只带了母亲,没带那群莺莺燕燕的小妾。
席间觥筹交错,桌上摆满山珍海味,侯拴妮看得眼花缭乱,高兴得合不拢嘴。饭后,仆人端上一盘红彤彤的荔枝,北方罕见的水果,透着股贵气。侯拴妮没见过这玩意儿,拿起一颗,咔嚓一声连壳咬下去,嚼得满嘴嘎吱响。她咂咂嘴,嘀咕:“甜是甜,就是壳硬了点。”
满桌宾客先是一愣,随即哄堂大笑,有人低声嘀咕:“乡下婆子,没见过世面。”有个涂脂抹粉的夫人捂嘴偷笑,手里的帕子抖个不停。张宗昌坐在一旁,脸色阴沉,低头抿了口酒,什么也没说。 宴会散了,他扶着母亲回到府邸,路上母子俩都没开口。侯拴妮察觉到儿子心情不好,试探着问:“今儿我是不是丢了你的脸?”
张宗昌停下脚步,回头看她,眼神里透着股狠劲:“娘,您别多想,这事我记下了。”回到家,他把大厨叫来,扔下一句话:“给我做一道连壳都能吃的荔枝出来。”大厨愣住,琢磨了好几天,终于用糖浆裹出假壳,把剥好的荔枝嵌进去,模样逼真,吃起来满口甜香。
张宗昌试了一颗,点头:“就它了。” 没过多久,他又请来那天的宾客,照旧摆下宴席。饭菜上齐,气氛热闹,仆人端上那盘特制的“荔枝”。夫人们照旧拿起果子,手指抠着剥壳,结果糖壳化开,黏得满手都是,裙摆上也沾了糖渍,个个狼狈不堪。侯拴妮却照旧整颗塞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拍手笑道:“这回的比上次好吃,壳都软了!”
张宗昌抬头看她,嘴角微微上扬:“娘,您喜欢就好。”宾客们面面相觑,有人尴尬地低头,有人挤出干笑,再没人敢出声嘲讽。
这场宴席,张宗昌不动声色地替母亲扳回了脸面。 可这份孝心没能护他太久。那晚火车站的刺杀来得太突然,枪声响时,他身边只有两个副官,护卫全被调开。子弹穿过他的胸口,他倒下时嘴里还喊着:“娘……”刺客逃进夜色,留下满地疑问。
有人说是仇家报复,有人说是政敌设局,可母亲到底病没病,谁也说不清。消息传到侯拴妮耳中,她坐在院子里,盯着那封歪歪扭扭的信,泪水砸在纸上,晕开墨迹。
张宗昌这一生,贪财好色,恶名远扬,可对母亲,他从没亏欠过半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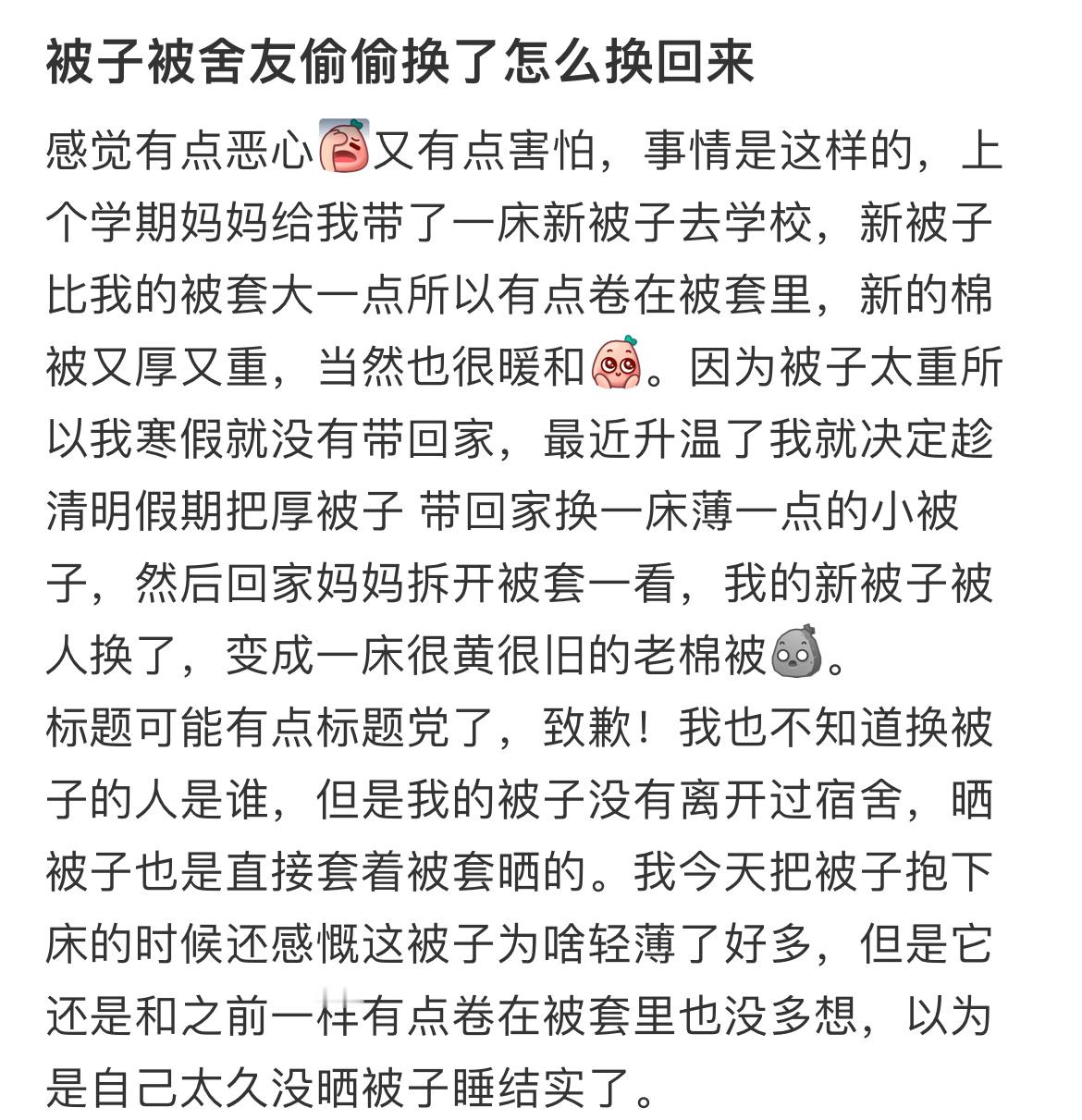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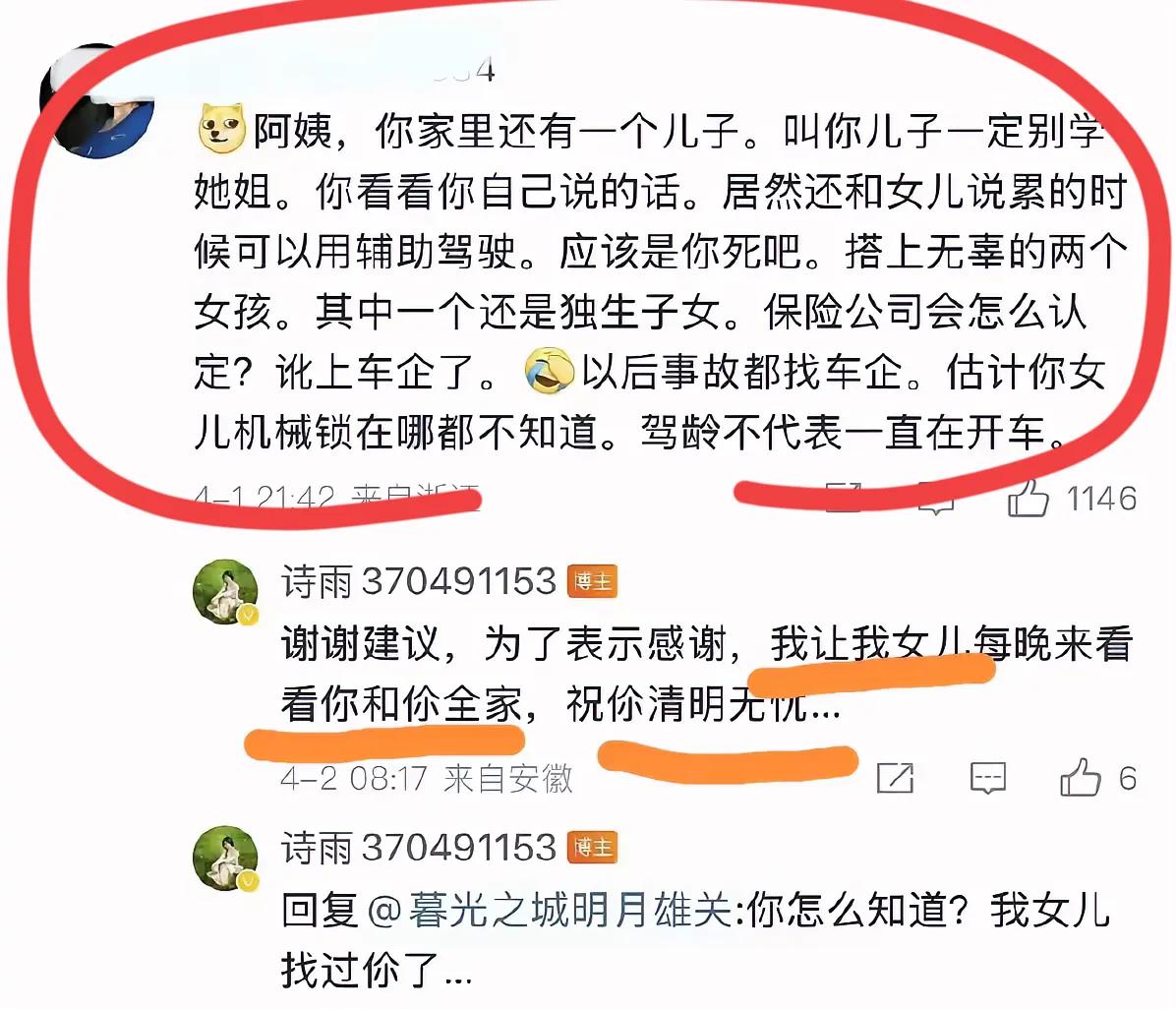





用户10xxx70
算是个人。
不求甚解 回复 03-04 11:12
离得远了,有时代滤镜。一个恶贯满盈的军阀,确实,没机会把他的恶加在你头上。
timothy_guo
娘俩都不是好人
宅家小咸鱼
抢吃的也罢了,还敲人后脑勺,那不妥妥的杀人犯!
我所看
你怎么知道倒下时喊“娘”!你是刺客?乱编
简单 回复 03-03 00:36
抓住小编!这个案件终于水落石出了![捂脸哭][捂脸哭][捂脸哭]
贫道泡师太
据说蒋介石倒下的时候也喊了声“娘。。”但知情人所说后面还有希屁两个字没来得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