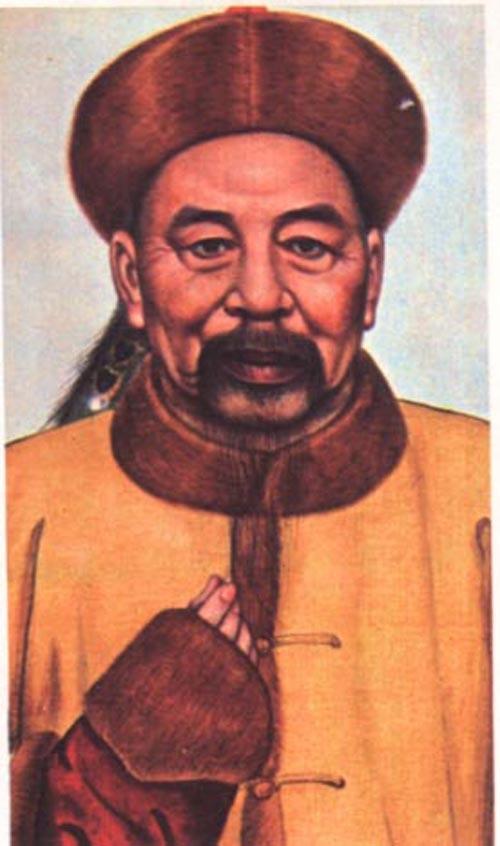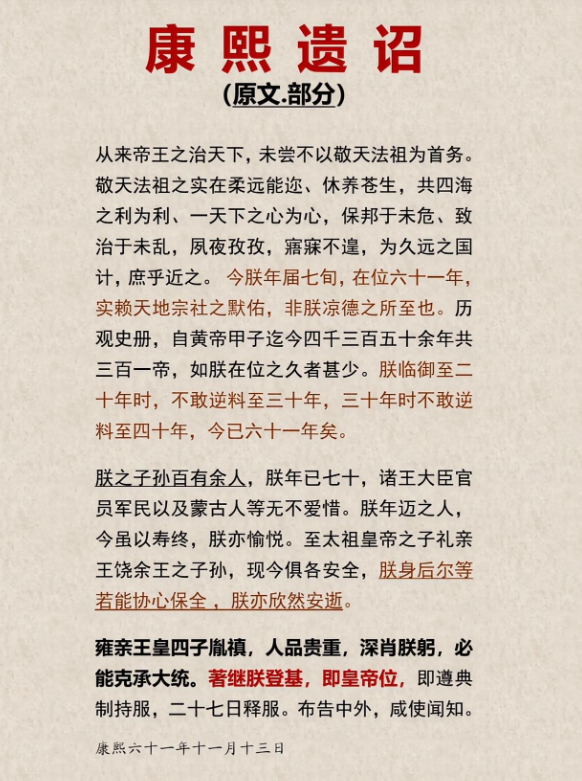有人说:其实二月河的《雍正王朝》美化雍正很多,邬思道就是四爷的影子,是四爷的阴暗面,甚至还美化了十三爷。 真实历史上,太子第一次被废后康熙圈禁了大哥和十三爷,小说上说是康熙为了不立太子不让十三爷帮四爷争抢位置,所以保护性圈禁,实际上不是,雍正后面修改了很多十三爷的史料,从零星碎片中可以得知,康熙是对十三爷狠心圈禁,根本不是保护性圈禁,而且康熙后面多次骂十三爷 问题来了,如果康熙不是保护性封禁十三爷,十三爷到底是有何大罪,要被康熙如此圈禁呢? 🦅🦅🦅🦅🦅🦅🦅🦅🦅🦅🦅🦅🦅🦅🦅🦅 鹰眼看世界:揭秘康熙帝圈禁十三阿哥胤祥的真相:胤祥一直都是棋子。 从历史记载与胤祥在雍正朝的实际行动来看,他出圈禁后并未表现出对康熙或雍正的怨恨,反而成为雍正最信任的兄弟和得力助手。但结合其经历与权力斗争逻辑,胤祥的“恨”可能隐晦地指向以下方向: 一、最直接的“恨”:八阿哥党与夺嫡政敌 政治清算的驱动 胤祥在雍正继位后,主导了对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等政敌的清洗。他亲自审讯、监禁甚至逼死胤禩集团成员(如阿尔松阿、鄂伦岱),手段之凌厉远超雍正本人。这种近乎报复的行为,暗示他对八爷党的深重敌意。 历史依据:胤祥曾痛斥胤禩党羽“阴结朋党,构陷忠良”,言辞激烈,似有旧怨未消。 对“污名化”的反击 胤祥被圈禁期间,八爷党可能散布其“悖逆”“结党”的罪名,导致康熙对其彻底冷落。胤祥复出后,通过铲除八爷党势力,既是为雍正扫清障碍,也是为自己洗刷污名。 二、隐而不发的“怨”:康熙的绝情与不公 从宠儿到弃子的心理落差 胤祥早年深受康熙宠爱,13岁起便随驾出巡,却在太子被废后突遭圈禁十年。康熙晚年对其“不忠不孝”的指责,与其早年评价截然相反,这种反差可能令胤祥对父亲产生不解与怨怼。 《资治通鉴》视角:帝王对臣子的“用弃无常”是常态,但胤祥作为皇子,情感上更难释怀。 对圈禁苦难的归因 胤祥被圈禁期间饱受身心摧残(据载其腿疾、咳血等病症均源于此),这些痛苦虽由康熙直接施加,但胤祥作为传统儒家教育下的皇子,大概率会将责任转嫁于“挑拨父子关系的奸党”(如八爷党),而非公开归咎康熙。 三、对雍正的可能矛盾:感激与隐痛 表面:绝对忠诚与感恩 胤祥复出后对雍正鞠躬尽瘁,甚至累死任上。雍正给予其超规格待遇(如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双方堪称君臣典范。胤祥公开场合从未流露对雍正的不满。 深层:被利用的隐痛 从权谋逻辑推测,胤祥可能意识到自己实为雍正权力布局的“工具”——康熙朝的圈禁客观上使其成为雍正继位后的“清白孤臣”,而雍正对其的厚待亦是巩固皇权的需要。这种“工具性”或令胤祥偶感悲凉,但史料无直接证据。 四、本质结论:政治人物的“恨”服务于权力需求 胤祥的“恨”并非个人情感宣泄,而是 政治生存的必然选择: 必须恨八爷党:雍正需要胤祥作为清洗旧势力的旗帜,胤祥也需通过打击政敌重获政治生命。 不能恨康熙:批判先帝等于否定雍正继位合法性,胤祥的“忠孝”人设也不容许他质疑父亲。 不可怨雍正:雍正是其唯一靠山,且胤祥的权势完全依附于皇权,表露不满等于自毁前途。 历史隐喻:权力场中的情感异化 胤祥的遭遇印证了《韩非子》所言:“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在九子夺嫡的极端环境中,皇子们的爱恨早已被权力逻辑异化。胤祥的“恨”终究只是皇权游戏中的一枚筹码——他或许最恨自己生在帝王家。
1729年,52岁的雍正召13岁马氏侍寝。是夜,马氏被送到了龙榻之上,雍正侧躺着
【3评论】【19点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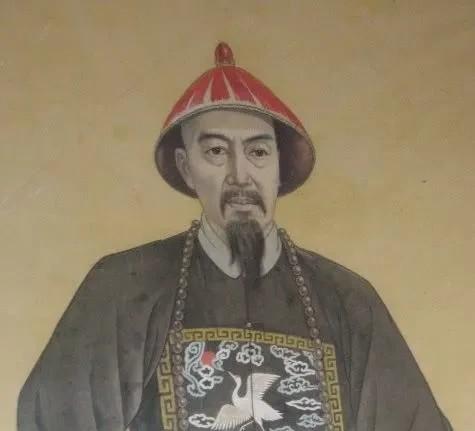
![“明朝有个皇帝叫乾隆……”[???][???]](http://image.uczzd.cn/133577848549833488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