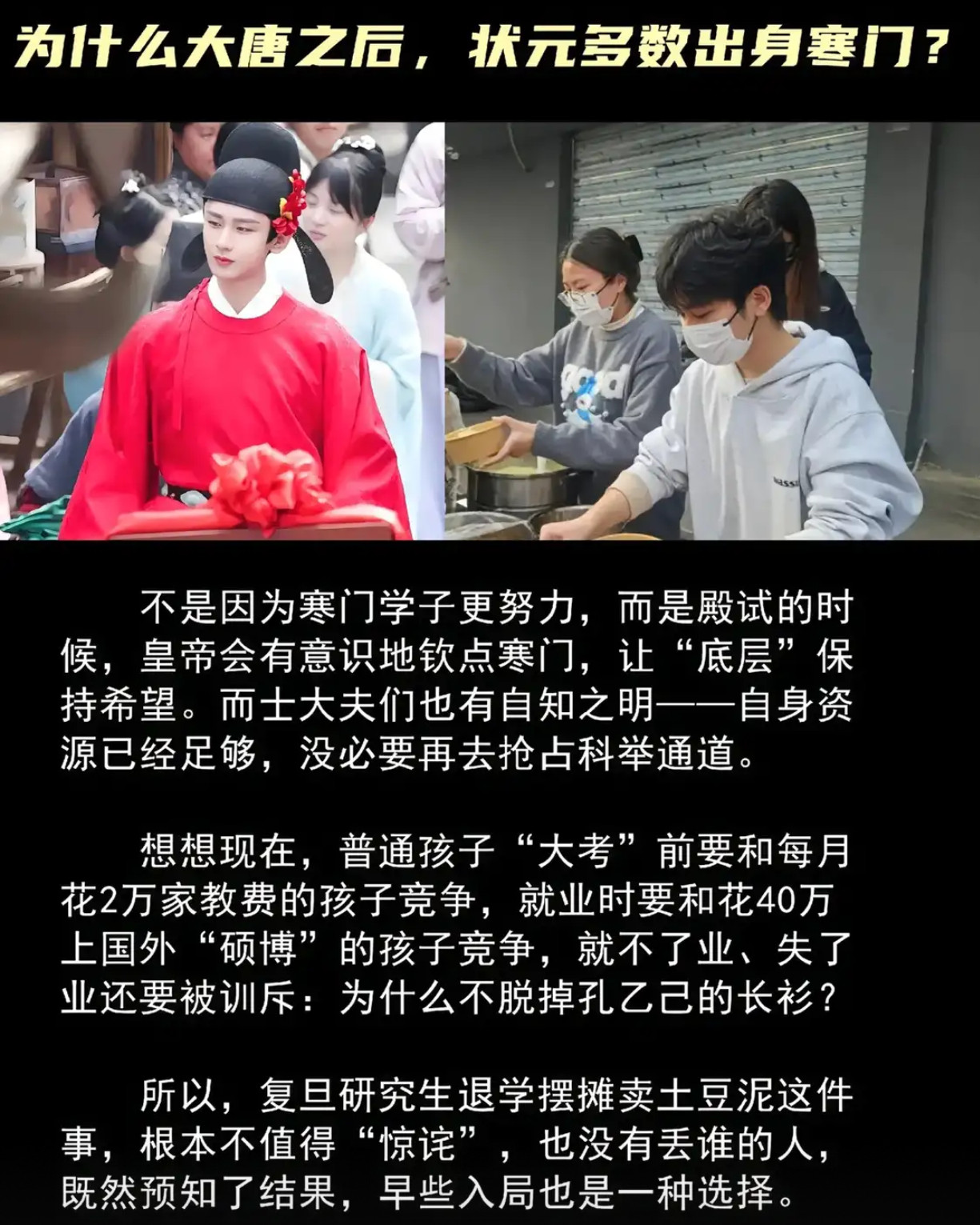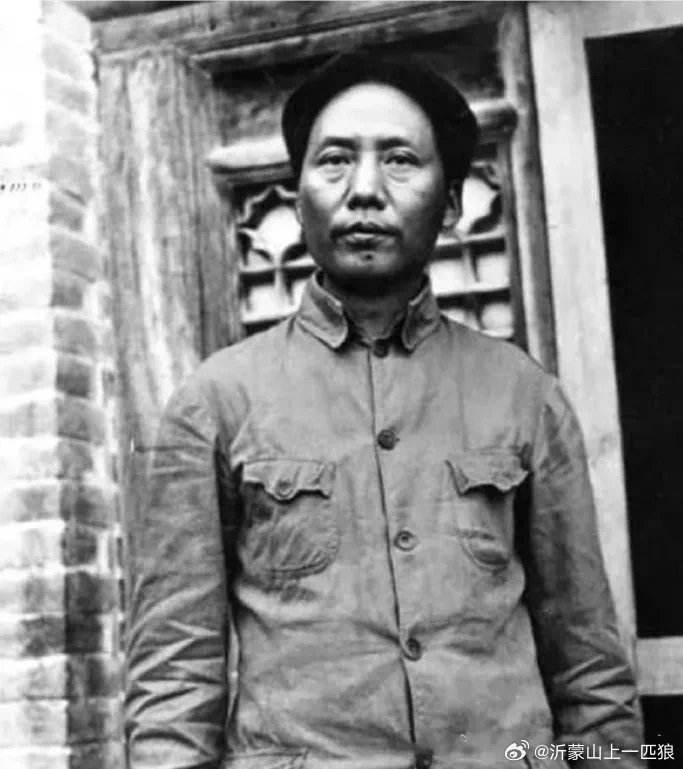1923年的一天,鲁迅的弟媳羽太信子对他指责道:“鲁迅非礼我,偷看我洗澡!”弟弟周作人听罢,抄起香炉就向哥哥砸去。 1923年7月初,鲁迅与周作人还共同出游东安市场,一起探访东交民巷的书店,显示出兄弟之间的密切与和谐。 就在同月的14日,鲁迅突然更改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开始独自在自己房间用餐,这一改变预示着家庭内部气氛的微妙变化。 仅仅几天后的7月18日,周作人写下了一封含蓄而深刻的“绝交信”,将其交给鲁迅。这封信的内容被周作人保留在了当天的日记中,表达了他对过往关系的失望和对未来独立生活的决心。信中的措辞,显示了周作人对这种裂痕的深刻感受和强烈反应。 7月19日,周作人在没有任何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拒绝与鲁迅进行任何交流,这在鲁迅的日记中得到了证实。两兄弟之间的关系,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24年6月11日,这一天的事件成为两兄弟关系破裂的标志性瞬间。鲁迅在其日记中描述了当天在八道湾家中的激烈冲突,这是一次包含了身体冲突和激烈言辞的对抗。据悉,周作人在争执中甚至动用了铜香炉作为武器,这一幕被朋友及时制止,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鲁迅同样在冲突中毫不退让,据家中人回忆,他曾试图用陶瓦枕还击。这场争执不仅是物理上的对抗,更是情感与信任的彻底破裂。两人之间的关系自此一去不复返,直至生命终结,双方均未再有任何交往。 导致这一剧烈变化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多数猜测都围绕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展开。羽太信子据称在两兄弟关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她的行为和言论被认为是触发冲突的直接因素。一种说法是羽太信子因嫉妒和不满而故意制造谣言,诬陷鲁迅偷窥她洗澡,这一指控被周作人接受,从而引发了两人之间的激烈争执。尽管具体细节无从考证,但周作人后期的行为表明,他深信不疑这些指控。 这种变化的背后,似乎与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的经济观念和家庭管理方式有关。羽太信子从一个贫苦的日本家庭出身,年轻时便开始在外工作,以维持生计。这种早年的经历可能使她对金钱有一种深刻的渴望和依赖。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羽太信子作为他们的家政帮手,与周作人日久生情,并最终结婚后随他回到中国。回国后,两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尤其是鲁迅,其文学成就和社会地位日益显赫,经济条件亦相对宽裕。 鲁迅在北京的八道湾买下宽敞的宅院后,全家搬迁至此,包括周作人一家。 羽太信子在这座大宅中担任了管理家务的重要角色。 她的经济管理方式引起了争议。 她的奢侈消费,如雇佣多名仆人、坚持高标准的生活质量等,使家庭的开销远超收入。 羽太信子的这种消费行为,部分源于她贫穷出身后对财富的极度追求,这与鲁迅慷慨且不太注重物质的性格形成了对比。 羽太信子感觉到自己在家中的经济地位受到威胁,尤其是在经济上依赖周作人和鲁迅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经济压力可能加剧了她对鲁迅的不满。 在家庭中,当经济紧张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这种不满可能转化为想要排挤鲁迅的动机。 1936年10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鲁迅在上海逝世,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的哀悼,成千上万的人群涌向街头,参与了这位文学巨人的送行仪式。 在这悲痛的时刻,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及其家人的缺席,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不仅是因为兄弟俩之间的深刻矛盾,更反映了他们关系的决裂程度。 鲁迅去世后的次年,周作人与北大教授许寿裳合作,共同编纂了《鲁迅年谱》,一部详尽记录了鲁迅一生的重要事迹的年谱。 作为周作人的朋友,许寿裳对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断裂颇为关注,他尝试从周作人那里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但周作人对此始终保持沉默。 许寿裳基于他对鲁迅个性的了解和其他可获得的信息,推断两兄弟间的不和可能源于彼此之间的误解,他指出周作人可能过于轻信他人,尤其是妇人的话。 这一观点后来被引用于1964年在香港出版的《五四文坛点滴》一书中。 书籍出版后,作者鲍耀明将一本书寄给周作人,希望听取他的看法。 周作人在回信中表达了对许寿裳看法的认同,这在他的一生中,可以算是对兄弟间矛盾最直接的回应。虽然他没有详述具体事件,但他的回应至少显示出晚年的他对这段关系的失和有所反省。 尽管周作人似乎在晚年意识到了自己的某些错误,但鲁迅已经不在人世,两兄弟无法和解。这种遗憾的情绪在周作人的言辞中隐约可见。1967年周作人去世时,鲁迅的后代也没有人出席他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