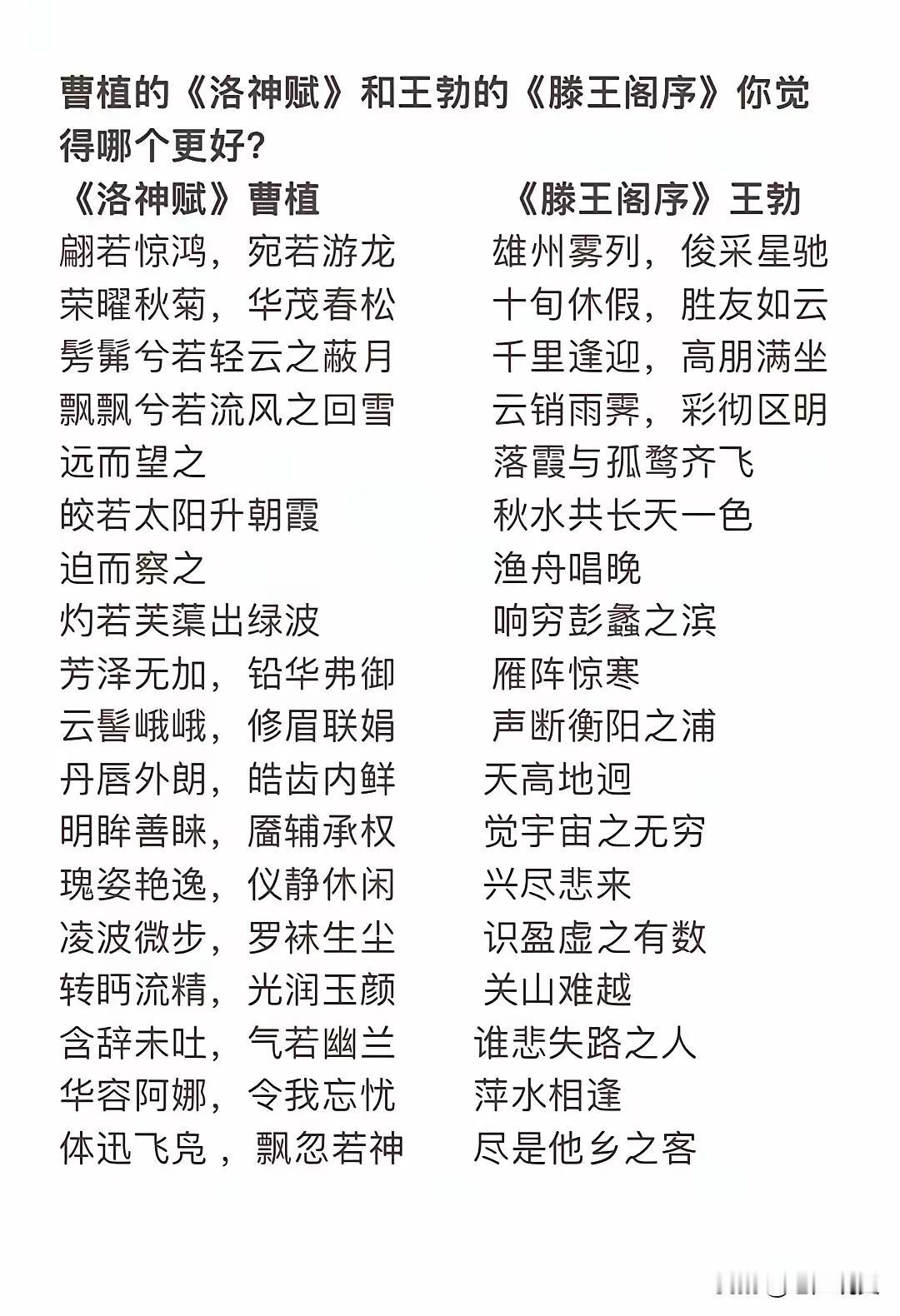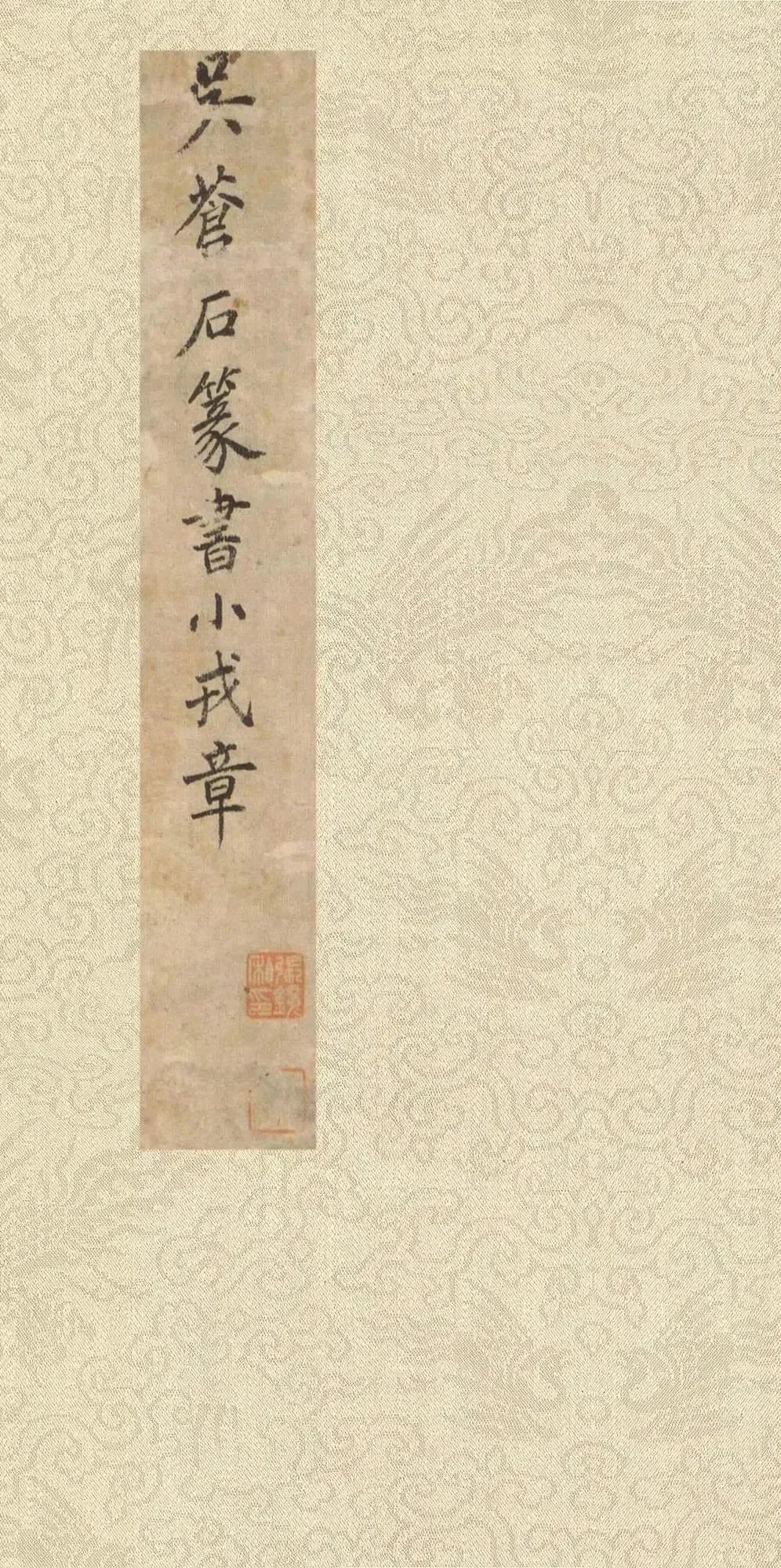《醉卧关山》
作者:香草芋圆

简介:
1.
萧挽风被从边关召回,将军卸甲,做个京城的富贵闲王。
宫宴歌舞升平时,堂下缓缓走过一个素衣美人。
赫然正是最近卷入大案的罪臣谢氏之女。
谢家嫡女明裳,容色鲜妍,性情骄纵。
纵然已是戴罪之身,依旧扬着下巴,黑白分明的眸子斜乜,递来冷冰冰一记白眼。
帝王笑指美人,“听说谢家在边关时,与五弟颇有旧怨?朕做主,将谢氏女赐你可好? ”
萧挽风手握金杯,平淡道,“谢皇兄。”
2.
河间王萧挽风,话少独断,手腕铁血。
谢明裳正式见河间王的第一面,在自家里。河间王缺个王府,据说看上了谢家宅子。
谢明裳:?
两人正式相见的第二面,在宫宴上。
谢明裳作为被赐下的美人,冷冰冰朝他翻了个白眼。
提着包袱进河间王府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活不到谢家平反昭雪、家人重逢的时候了。
后来,京城春夏换了秋冬。
冬日懒怠,她把白生生的脚趾头踩上河间王的膝盖,懒散叫他帮穿鞋。
他也只用温热手掌捂着她冬日冰凉的脚,问她:“穿哪双?”
3.
当年,关山大漠风沙起, 单骑绝尘照月来。
萧挽风的无数个梦里,始终有个十来岁的娇俏小姑娘,咬着甜杏,饮马河边,翘着小靴等他。
一别多年,当年那个小姑娘长大了……不记得他了。
精彩节选:
奉德五年的暮春,雨水比往年来得更多些。
辽东王谋反叛国的消息二月里传入京城,朝野哗然。朝廷一轮轮地清查逆党,西市处斩的血水一遍遍地被雨水冲刷。
牵扯进叛国大案的朝臣,仿佛沾染上瘟疫,朝中同僚们避之唯恐不及。
到了三月中,城西长淮巷的谢宅,成了最新的瘟疫。
三月十五凌晨。
大批甲胄鲜明的禁军出现在长淮巷口,团团围拢谢宅。一名紫袍大宦站在敞开的大门外,高声往门里喝问:
“谢家丁口三十六人,名册俱全,清点下来少了谢氏嫡女明裳主仆两人,谢家妇刘氏一人,又少了家丁八人。大清早的,人都去何处了啊。”
谢夫人站在细雨庭院中央,不冷不热道:“我家丫头喜欢乱跑,家里管不着,谁知道去哪处了。黄公公差人四处寻寻看?”
姓黄的内监“嘿” 了声,“咱家奉命清点丁口,还得替你家寻人?坐等着!谢家姑嫂两个归家,咱家回宫交差复命。人要不回来,咱家去圣上面前好好说道说道。”
*
四更正。浓云压月。
南北御道街车马匆匆,都是赶着上朝的文武官员。
靠近御街边上,有座京城出名的梨花酒楼,每逢春夏交接,满庭院梨花盛开之时,生意最好。
伸出酒楼院墙的梨花枝下,有个早市馄饨摊。
摊子不大,只有两张木桌。
一张木桌挤挤挨挨坐满八名魁梧家仆。
谢明裳独坐在另一张木桌旁,瓷匙拨几下汤碗里的热馄饨,若有所思。
“我成瘟神了?一天天地躲我,去他家总找不到人。”
并未指名道姓,但隔壁木桌的家仆们都听得明白,愤然道:“杜家欺人太甚!”
谢明裳却不再提了。舀了舀馄饨汤,只道:“这家馄饨不错。空等人无趣,你们都吃些。”
暮春的天气已经不太冷,但夜里风大,她出来时还是披了件长披风,戴了风帽,从头到脚包裹得密密实实,只从手腕处露出半截品红色织金线的锦缎袄袖。
青葱般纤长的手边,放了一枝刚刚折下、带着露水的雪白梨花。
四更末,斜对着南北御街的青衣巷口,拐出来一行人。
几名长随提着灯笼前面引路,六品青袍打扮的年轻文官匆匆拨转缰绳,上了御街。
谢明裳盯着那文官公子的身影,手里搅动馄饨的动作停了。
她冲御街那边一颔首,吩咐众家仆:
“从马上打下来。”
一阵呼啸风声,直奔马上的文官公子而去。
黑黝黝的东西打在肩背,咚地沉重声响。
文官公子被打得一个踉跄,差点栽下马,长随扑过来死死扯住马缰绳,才把人扶稳了。几个人惊怒交集,原地停下,四处找寻肇事人。
馄饨摊处传来一阵哄笑。街边阴影里走出来一个家仆,高声喝道,“杜二!”
被称作“杜二 ”的文官公子大名叫做杜幼清,出身清贵门第,父亲任职四品国子监祭酒。
敢在御街边上掷他的,除了和杜家定亲的谢家六娘,还有谁?
杜幼清捂着剧痛的肩头,回头怒道:
“谢明裳!”
谢明裳放下瓷勺,接过帕子,仔细擦干净了手,冲街上勾了勾手指。
“下马,过来说话。”
杜幼清深吸口气,翻身下马。
杜家另一个长随在地上摸索了片刻,找到了袭击的物件,捧倒杜幼清面前。
哪里是什么暗器,分明是几个吃干净的大荔枝核儿。
杜幼清捂着肩膀痛处,两根手指掂起荔枝核儿,走到街边,把‘暗器’掷回谢明裳的怀里。
他今天刻意躲人,从偏门里出来,没想到还是被人抓了个正着,心里又惊又愧。
再定睛望去,谢明裳居然带着一群健壮家仆,就坐在人来人往的酒楼围墙边上,夜里也不知被多少人撞见了,满腹的惊愧,又转成了满腹的火气。
“尚未出阁的小娘子,夤夜不归。” 杜幼清皱眉道,“成何体统。还不快趁夜回去。”
谢明裳不冷不热道,“急着回去做什么。等着官兵围门抄家么。”
杜幼清呼吸一窒,半晌才道,“事还有转机,尚不至如此。”
谢明裳轻笑了声,“骗我。若是谢家之事还有转机,你躲我做什么。”
杜幼清无话可说,最后只得道:“父亲嘱咐我最近当心。辽东王谋逆大案非同小可,若杜家也牵扯进去,如何能替你家奔走。”
谢明裳从木桌起身,几步走到街边,抬头望着杜幼清,“你有心替我家奔走?”
她在家里娇养惯了,向来喜欢鲜亮的颜色,今日虽然披了一身银灰披风,里面照样穿得鲜艳招摇。酒楼的灯笼烛火映照之下,品红色的袄裙衬得肌肤如雪,原本就明丽的眉眼,更加娇艳了几分。
杜幼清心里微微一漾,刚才当街挨打的怒气顿时消散了个干净。
“明珠儿。” 他换了旧日熟谙的昵称,放缓了声调,低声劝慰她。
“我知道你几次找我。你莫怕,我和父亲确实正在为谢家奔走。谢家这次虽然牵连进了谋反大案,罪责应该不至于灭族,至多抄家流放。父亲说了,其中大有可操作之处。”
谢明裳的指尖摩挲着掌心的荔枝核儿,“你这话我听不懂了。如何操作,详细说说看看。”
“一旦抄家,财帛身外之物,是不必再想的了。全族男丁流放,少不得一番奔波苦楚。但流放何处,是去东南州郡的厢兵营垦田,还是西北的荒漠之处戍边,其中大有门道。此其一。”
“抄家后女眷的去处,我也问清楚了。” 杜幼清的声音更低,“家里未出阁的小娘子,通常有三个去处。要么入宫为奴,要么入教坊为……为乐伎。要么通过官府,被人赎买。”
说到这里,他忽地有点心虚,不敢看面前人的眼睛,快速道:
“明珠儿,这些时日我奔走疏通了不少门路,力求不将你没入宫掖为奴,更不会教你落入教坊,而是走官府赎买路子。届时,我定会赎买你。”
谢明裳站在御街边,有阵子没说话。
良久才笑了笑,“有意思。若不是今天来找你,我还不知,你替我如此打算。”
杜幼清的情绪也有几分起伏,跟上一步,急促道:
“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我已经知会了京城的亲友同僚。杜家在京城交游甚广,家姐又嫁入了广陵王府,就算是公卿勋贵家的子弟,看在我的薄面上,定不会与我相争。明珠儿,你安心等我。”
谢明裳点点头,又想了一会儿,“你把我买下,我肯定做不成你的正妻了。以后,我就是你家奴婢?这便是你替我谋算的出路?”
“这…… ”杜幼清涨红了脸。
谢明裳一抬手,杜幼清刚才吃了大苦头,惊得连忙倒退两步,迭声道,“你听我解释。除此之外,再无他法。”
他本以为对面的骄纵脾气上来,又要当场发作,吩咐家仆动武,没想到她抬手,却只是伸手抹平了自己被风吹乱的衣袖。
谢明裳对他笑了一下,那笑容极清浅。
“其实,你这些天日日躲我,我便知道答案了。” 她平静地道。
更深露重,一滴晶莹的露珠沾在谢明裳湿漉漉的长睫毛上,她眨了下眼,露珠滑落,仿佛一滴泪落了下来。
杜幼清的心尖一颤,急遽跳动了几下。
谢明裳的性子,他是了解的。谢枢密使接近四十岁才老树开花,生下谢明裳这女儿,父母哥哥一起娇宠到大,要月亮不给星星,养成了眼高于顶的脾性。
不管对方的家世再显赫,她看不上就是看不上,偌大个京城里,公侯显贵子弟,受过她白眼的,被她当面讽过的也不知多少。
偏偏她又长了副明艳照人的容貌,碰到不喜的人,连个正眼都不会落下。斜睨瞥过,起身就走,被她瞪的世家子还愣愣地在原地发呆。
从她十五岁及笄起,说亲的人家几乎踏破了门槛。
放着满京城的公侯贵戚,谢家挑来拣去,最后却看上了杜氏的百年清贵家世,士人书香门第。
这样的一门亲事砸到头上,杜幼清被几个好友屡次打趣,说娇妻人美如花,奈何有个彪悍岳家。杜氏与其说是迎娶,不如说是入赘,杜幼清还闷闷不乐了许久。
这样的天之娇女,若是身契落入自己手里,将满身的骄纵脾气尽数收起,从此做个予取予求的房中解语花……
杜幼清心里一荡,无数绮丽的念头从心底升起,口干舌燥。
在他对面,谢明裳的手指纤如青葱,无意识地反复摩挲着掌心的荔枝核儿。
杜幼清鬼使神差般伸出手去,趁夜色握住了她的手腕,低声道,“纵使不能为正妻,也定不会委屈了你……必当筑金屋以藏之。”
谢明裳垂下眸,望着自己被握住的手腕。
她想起上个月的某个夜晚,自己赴宴大醉而回,杜幼清护送她回府,路上她借着醉意,死活要勾一勾他的手指。
当时,杜幼清忙不迭地让开了,还斥了她几句,说道礼法不可废,夫妻一日未成婚,一日便要守住规矩,莫要叫人诟病轻狂,堕了两姓声誉。
言犹在耳。
谢明裳笑了声,“现在就把我当奴婢了。我还没入你杜家呢。”
杜幼清猛地清醒过来,慌忙松了手。正尴尬时,谢明裳却已经轻描淡写转开了话题去。
“其实你说错了。家里犯了事的女眷如何发落,并不是你一个区区六品文官奔走几次就能决定的。”
杜幼清急忙道,“事在人为。在京城行事,钱财还是其次,主要是看情面。”
他口口声声的看情面,谢明裳却不肯给他一个情面,直截了当道:
“好个事在人为。你我早有婚约在身,你杜家想出手帮扶的话,早几日便该上门议婚了。如今压根不提,只谈什么赎买……怕我们谢家牵累了你们杜氏吧。”
杜幼清的脸色又蓦然涨得通红,嘴唇翕动几下,却没有吐出半个字来。
一阵死寂般的安静。
话题硬生生停在这里,两人再也无话可说。
谢明裳点点头,往后退了两步,“我知道了。”
掌心的荔枝核儿,被摩挲许久,沾染了人体体温,隐约发热。
“你我认识这么久,留个纪念罢。” 谢明裳把荔枝核儿掷去对面,“京城少见的春荔枝,种在你家庭院里,运气好的话,十年八年或许能结果。 说罢转身往对面的青衣巷里走去。”
杜幼清追在后面喊了两声,她都没有应。
正好一阵风卷过长街,从酒楼里伸出庭院的梨树枝桠上簌簌落下了一地雪白的梨花来。
谢明裳踩着梨花走过御街,穿过青衣巷,之前月下承诺的一生一世,举案齐眉,犹如这满地梨花,俱被雨打风吹去了。
青衣巷深处缓缓行驶出一辆马车。兰夏含泪掀起车帘子,远远唤道:“娘子。”
谢明裳捏了捏兰夏胖嘟嘟的脸颊,“哭什么。我们谢家人不爱哭鼻子。 ”解下系带,把披风递给兰夏。
正踩着小凳上车,身后御街方向的地面忽地传来隐隐颤动。
谢明裳起先没在意。等马车起步,缓行到青衣巷和御街的交叉口时,御街远处的马蹄奔腾声响已到了近前。
赫然上百佩刀披甲轻骑,狂风暴雨般疾驰过宽敞御道。
轻骑由南向北直行,遇车马而不缓速,前方行驶的官员车马慌忙左右躲避不迭,骂声抱怨声不绝于耳。
谢家马车在巷口勒停,目送上百轻骑排成锥形护卫阵型,簇拥着当中一匹雄健黑马,马上的应是他们主将,远远地看不清身形,只见身后烟尘滚滚,笔直往北面的皇宫方向呼啸奔腾而去。
“御街不是禁驰马?” 谢明裳放下车帘子,往后厢壁一靠。
“这是哪家入京复命的武将?胆子不小。大清早得罪满街的文臣,明天递进六部的弹劾奏本能淹了他。 ”
马车沿着御街转过半圈。晨光映亮长街时,谢明裳领着兰夏,又站在梨花酒楼面前。
“贵客来早了。 ”酒楼掌柜的开门过来招呼,“小店午时才开张。您看……”
谢明裳从荷包里掏出一枚沉甸甸的金锭,丢在柜台上。“我要一个靠窗临街雅阁子,二楼清净包场。能不能现在进店,够不够包半天的。”
能。当然能。
店家捧着大金锭掂了掂,足有二十两,“早晨半天啊,足够了足够了。”
黄澄澄的金锭砸下去,不仅叫酒楼今天提前开了张,坐在二楼最好的靠窗临街雅阁子,还附送了满满一桌的上好早点。
谢明裳把所有人全留在楼下,只带兰夏进二楼阁子。
直到窗边落座,兰夏纳闷地问:“我们不回家去,却来酒楼包场做什么呢。”
谢明裳并不急着回复,而是夹了个热腾腾的梅花汤饼,放进兰夏碗里,“跟我吹了整夜的风,难为你了。吃点热的吧。”
托腮想了一阵,才跟兰夏说:“京城门路广。杜家的路走不通了,我想找一找其他路子。”
兰夏似懂非懂地一点头,道,“不管情形如何,我们主仆总归在一起。”
谢明裳抿嘴笑了笑,拍拍她的手。
谢家从边关调入京城五年有余,她平日里随母亲走动赴宴,四品以上京官府邸的闺阁千金们认识的不少,结下交情的却不多。
倒不是她孤芳自赏,不屑于结交;而是本朝风气重文轻武,武将在朝中颇为不受待见。品级相同的文官和武将在京城街头狭路相逢,车马避让的必然是武将那边。
谢明裳的父亲以武勋出身,领兵镇守西北门户,半辈子在战场摸爬滚打,立下赫赫战功,终于在五十出头的年岁坐镇二品枢密使的高位,可以说是当朝武将第一人了。即便如此,从边关调入京城后,还是受尽文官鸟气。
朝中风气如此,自然会影响到京城的官宦夫人千金的交际圈子。
谢明裳和文官家的闺阁千金们,向来不多来往的。
这些年玩得最好的闺中密友,要算是长公主府上的端仪小郡主。
——毕竟身份高到了宗室皇亲的地步,便不怎么在乎手帕交的家族出身,是文官武将,还是世家勋贵,只看脾气性情合不合了。
前些日子,朝中就有隐约的风声传出来,谢氏卷进辽东王谋逆案,这次要不好。
到了五日前的那次朝会时,果然御史台众言官同时发难,辞锋激烈地弹劾谢家父子。
端仪郡主探得了消息,急忙派人递口信给谢明裳。
仓促间无法定下确切的见面时辰,只约好今日晨间在御街边最显眼的梨花酒楼见面,不见不散;谁先到了,便在临街窗外插一支新鲜梨花。
谢明裳推开雕花木窗,把清晨折下的满枝梨花插在窗棂边,转回身坐下,开始吃朝食。
酒楼里的朝食置办得丰盛,小银碟摆了满桌。两人吃得半饱时,遮挡坐席的六扇锦缎山水屏风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从楼下踩着木梯上二楼。
兰夏纳闷咕哝着,“不是包场了吗。”
谢明裳却并不意外,放下筷子抬头去看。
有人屈指在屏风木座上叩了叩,从屏风外转进一个紫袍青年。
那人二十出头年纪,玉犀冠,绛紫暗花袍,眉宇间满是矜傲之气,一看便是勋贵家出身的子弟。
转过了屏风来,也不走近,只站在七八步外打量着谢明裳,半晌冲她一点头。
“我听说有人早上在御街边拦住杜二,说了好阵子话,杜二早朝都迟了。又听人描绘了形貌,就猜到是你。”
他从头到脚把人打量完,道:“为了堵杜二,整宿没睡?那你气色还不错。”
谢明裳的情绪早就平复下来,不急不忙夹了一块子菜:
“你大清早横穿半个京城来城北,就为了跟我说一句气色不错?谬赞了,贺侯。”
来人正是城南武陵侯府的当家人,贺子浚。
贺子浚是谢家大公子的同窗好友,结拜义兄弟的交情。虽只有二十五六,已经袭了爵,平辈们见面要正经行礼,尊称一声“贺侯 ”了。
贺子浚跟谢家兄妹都熟识,彼此知根知底。坐下伸筷子也夹了个春卷儿,几口吃了,不再耽搁时间,直接道明来意:
“你家的情势不好。打探来的消息,男丁只怕要流放三千里。”
他以筷子沾酒,在木桌上勾勒出一幅简陋的本朝疆域地图。
他以筷子沾茶水,在木桌上勾勒出一幅简陋的本朝疆域地图。
“以京城为中心,往南三千里,在岭南。东南三千里,在闽越。西南三千里,百瘴之地。非要在三者选其一,岭南是京官贬谪之地,你父亲有故旧好友在岭南,还是去岭南好。”
贺子浚以指腹将茶水地图抹去了,伸出筷子,又点了点谢明裳。
“至于你,杜二最近四处奔走,要把你通过官府赎买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想什么。但要我说,他这事办的极不妥当。事办得顺利,也不是他自己的本事,只怕后面有人暗中推波助澜。”
兰夏在旁边奉茶,听到‘赎买’两个字,惊得茶杯掉在地上,咕噜噜滚出老远去。
谢明裳早有准备,面色倒是波澜不惊,接过兰夏手里的两杯茶,一杯推过去贺子浚面前,“怎么说。”
“官员犯了事,家族女眷的去处,若要我说,最稳妥的还是入宫。走些门路,打声招呼,去内省六司清清静静做个女官,岂不是最好的结果。如果定下赎买,你落到谁手里,可就说不准了。”
谢明裳自己喝了口茶,平静反问:“杜二赎买不下?”
贺子浚嘲讽地一笑。
“杜家号称‘百年清贵世家’,呵,京城里犯了事,清贵何时管用过?杜二自己区区五品闲职,他父亲也不过是个四品国子监祭酒,主管着国子监生员的一亩三分地,朝中要紧的政务八竿子沾染不上。大家不好当面说他杜家没落了,见面了只得口头上赞一声清贵,他竟还当真了。”
“杜二赎买不下,是钱不够还是面子不够?”
“都差得远。”
贺子浚斩钉截铁道,“明珠儿,我跟你交个底,我这处备了五千两银,准备赎你家女眷。按理说足够了。但我身上的爵位不过是个祖上恩萌的二等候爵,京城的勋贵多如牛毛,若到了赎买当日,有哪家以势强夺,那就不是银钱的事了……我也只能退避三舍。” 说罢端起茶杯,倒像是酒杯似的,一饮而尽。
谢明裳捧着茶杯想了一会儿,开口道谢,“已经做得足够多了。贺候诚心待谢家,我也实话和你说一句,这些准备都用不着。”
贺子浚一怔,抬起头来。
谢明裳轻声和贺子浚透了几句底。
她父亲,谢家的当家之主:枢密使谢崇山,虽然和朝中文臣不怎么对付,但京城禁军中的许多将领和谢枢密使有交情。
就在昨天傍晚,一位姓常的马步禁军中郎将匆匆赶来谢宅,冒险泄露天机,说道:
圣意自有决断。
驳回了谢家女眷交钱赎买的提议。朝廷这两日便会发兵围谢宅,清点丁口。谢家女眷不是流放就是入宫。要谢家提前做好打算。
“有件事不瞒贺候。” 谢明裳黑琉璃般的剔透眼睛注视过来,“我家嫂嫂上个月探出了身孕。孕相不稳,消息未传出家门。不管流放还是入宫,嫂嫂的孩儿怕保不住,嫂嫂自身的性命也有风险。”
贺子浚吃了一惊,几乎站起身,按捺着坐下。
“你阿兄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说!”
“这算什么大事。更大的还有,贺候敢不敢听?”
贺子浚:“你说!”
谢明裳抬手一指酒楼外停着的谢家马车,“嫂嫂昨夜随我出门,此刻人就在车里。我想送她出京。贺候,看在我阿兄和你多年的交情上,敢不敢帮?”
贺子浚咕噜噜又喝了几口闷茶,把茶盏砰地扔回桌上。“若要我隐匿谢家男丁,我还需斟酌斟酌。帮扶一把嫂夫人,只要谢家信得过我贺子浚,把人交给我。”
谢明裳长长地呼出口气。
从昨夜起就堵着的心头登时畅快了。
贺子浚原地闷坐了一阵,反过来劝解她。
“说起来,你父亲身上背着不少武勋。当年突厥大举南下侵袭,几乎酿下灭国之祸,好在你父亲悍勇,秋冬落雪季节领精兵翻越关陇道,千里驰援中原,追着突厥轻骑后头穷追猛打,这才有了后面的渭水大捷,把突厥驱赶回关外之事。”
“天子当年困守京城,对千里驰援的你父亲必定留下深刻印象。倘若起了宽宥之心,你们谢家或许不会到那一步。嫂夫人的事交给我安排,回去告诉你阿兄,不必太过忧虑,吉人自有天相。”
说完留下自己的名刺,嘱咐事急时可以去城南侯府找他,告辞离去。
谢明裳和兰夏主仆俩坐在窗边,注视着谢家马车从路边转进小巷停住。很快跟来一辆小车,跳下两个小厮。
贺子浚亲自在巷口盯着,嫂嫂刘氏被贴身女使搀扶下车,悄无声息换坐去贺家小车里。
贺家马车缓行出巷时,不知为何却又停在路边。嫂嫂刘氏掀开半截车帘子,眼眶隐约含泪,仰头往梨花酒楼上方转来。
两边对视片刻,谢明裳冲大嫂微微而笑,挥了挥手。
兰夏紧张得吃不下,低声催促:“昨晚常将军的消息说,朝廷发兵围门就在这两天了。娘子,车在等你!寻到了出路,娘子赶紧跟着去……”
谢明裳不紧不慢地夹起春卷儿:“我不去。”
兰夏反应激烈地大喊:“为什么!” 慌忙又降下音调,恳切道:“机会难得,娘子快走。”
谢明裳只摇头。
小车在街边苦等,谢明裳始终摇头,小车终于放弃等候,缓缓往城南行去。
“总算做成一桩事。不枉费整晚上折腾。”
谢明裳轻声感慨,夹起最后两只春卷儿,兰夏和自己的盘子里每人摆一只。
“再等一等端仪郡主。寻一寻谢家其他的路子。”
谢明裳和兰夏主仆俩继续吃朝食。
才吃了没一会儿,却又有脚步声上了二楼,屏风外有人叩了口木座,问道,“谢家千金可在这处阁子。小的替我家主人送请帖来。”
谢明裳和兰夏互看一眼,兰夏起身出去,接过了请帖,双手奉给自家主人,纳闷道,“来的是个小厮,穿戴得倒是整齐。也不说是哪家府上的,直接把请帖塞过来就走。怎么这么无礼。”
谢明裳翻开请帖封皮,看了眼内容,直接合起,把请帖啪的扔去地上。
兰夏捡起翻看片刻,啊的惊呼道:“林相府上,林三郎的请帖?他不是去年求亲遭拒,放话下来,与我们谢氏老死不相往来了么。”
谢明裳抬手续了杯茶水,嘲讽地弯唇,“与谢氏老死不相往来,意思说他那边再不登门。却不耽误他送来帖子,叫我上门去求他。”
兰夏愣了片刻,反应过来,大怒骂道,“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林三那文不成武不就的纨绔子,他也配想!”直接把请帖扔进了纸篓。
没想到林三郎的请帖只是个开头。
陆陆续续,一上午功夫,又递来四五张请帖。
都是府上的小厮长随送上楼,什么话也不说,只把请帖递进,抬腿走人。
谢明裳翻了翻名字,有的认识,有的却很陌生。
其他几个倒也罢了,有一个裕国公家的世子,正经受了朝廷册封的国公府承爵人。论起家世身份,跟贺子浚的侯爵半径八两。
谢明裳盯着裕国公世子的请帖。
谢家的武将门第,是从祖父那辈开始,从边军士卒一步步摸爬滚打、实打实靠战功积累升上来的。虽然她爹位高权重,但三辈往上布衣出身,跟京城的开国勋贵们不是一个圈子。
她半晌也没回想起来,自己何时见过这位,怎么得罪的他。
如今谢家落难了,还特意送个帖子过来冷嘲暗讽,写好时辰地点,等自己上门苦苦央求。
多大仇多大恨这是。
谢明裳正对着满桌子的帖子琢磨,屏风外又有人叩了叩,这次送进一张红底黑字的名刺来。
谢明裳第一眼还以为看错,翻来覆去翻看几遍,硬生生给气笑了。
皇室姓“萧”,本朝尚红色,名刺底色正红,四角勾边的云纹套印了赭红色,署名处大剌剌地署上名刺主人引以为傲的‘萧’姓。
居然广陵王遣人送来的。
杜二的嫡亲姐姐嫁入的,岂不正是广陵王府。
杜幼清算是广陵王的妻弟,她跟杜幼清有婚约在身,如果早两个月嫁过去杜家的话,两边算正经亲戚。
如今谢家遭了事,杜家退缩不敢再提亲事,但两家婚约未退。广陵王这厮连面皮都不要了。
堂而皇之把自己的名刺送来酒楼,在空白处随手写了几行字,‘谢氏危矣’,邀她夜里‘登门商议'。
这些天家贵胄,不要脸起来,真是破廉耻。
谢明裳伸出手,掌心紧抵住胃部,微蹙起眉。
兰夏慌忙起身问,“怎么了娘子,是不是又犯胃疾了。”
“没事,就是突然有点犯恶心……给我杯酒。”
不是外面酒楼售卖的酒,而是谢氏早几年千金求来的药方,自家家里酿的温补药酒。
谢明裳身子不大好,无论去何处,温补药酒都要随身带的。
她抿了口温酒,带着酒香的暖意滑下喉咙,直达胃里,感觉好多了。因为疼痛而略微发白的唇色恢复了几分浅淡血色。
她抬手把广陵王的名刺撕吧撕吧,往纸篓里一扔,吩咐兰夏坐去窗边,盯着御街上来往的车马,看看端仪郡主是不是快到了。
端仪郡主如今还没有出阁,住在母亲的长公主府。
长公主府的马车向来华丽气派,比普通马车大了两倍有余,车顶又有鎏金宝盖装饰,隔着老远就能认出来。
兰夏搬了个木凳坐在窗边,认认真真盯了好会儿,欣喜地一拍手,“端仪郡主来了!”
谢明裳过去窗边,居高临下望去,果然看见队伍前呼后拥,仪仗卫士开道,众多长公主府亲卫驱散了拥挤人群,仆婢以清水浇洒长街,一辆华贵马车缓缓行驶过洁净御道。
那驾鎏金宝盖顶的马车行过梨花酒楼,停在路边。车帘猛地从里掀开,露出端仪郡主惶急的面容。
谢明裳眼尖,一眼看到她这位闺中好友鼻尖通红,眼角还带着几滴泪,视线紧盯着酒楼临街窗外插着的那枝雪白梨花,眼巴巴往上四处张望。
谢明裳看见了人,端仪郡主那边也同时望见了她,两人的视线对上一瞬,端仪郡主急忙把手探出车外,冲着她晃了晃,什么还没来得及说,马车里却又伸出一只养尊处优、圆润白皙的手,毫不留情地把车帘子拉上了。
兰夏愣住,“这……郡主她明明看见我们了,为什么不下车啊。”
谢明裳眨了下浓黑的长睫。
“马车里不止她一个人。和郡主坐着的,定然是她母亲长公主。如今我家出了事……也许,长公主不希望我们再来往了。”
她伸手探出窗外,拔出了那枝依旧鲜妍怒放的梨花。
“见到人就好。”谢明裳摸着雪白的梨花瓣,“有这份心意就好。不枉我们相交一场。正好我有话想带给她。兰夏,你替我传几句话。”
谢明裳起身走到窗边,把半开的木窗左右完全打开,二楼窗外的满树雪白梨花随风簌簌地吹进来。
湘妃竹帘卷起半扇,她斜倚窗前,俯瞰御街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正在轻声叮嘱兰夏时,二楼木梯又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
扇屏木座再次被人‘笃笃’轻扣几声。
谢明裳回身望时,只见一名体面管事打扮的中年男子站在门边行礼,替主家传话道:
“小人奉长公主吩咐,有几句话带给谢家千金。”
“长公主殿下说,朝堂里的事,长公主府向来不理的。”
来人是长公主府的辰大管事,面相沉稳,谈吐有度,显然是经过大风浪的人。
他站在阁子门边,并不往里进,只管尽职尽责地转述长公主口谕:
“虽然谢小娘子和我家郡主玩得好,但私交归私交,政事归政事。谢家在朝中出了事,殿下不想管,也管不着。郡主年纪太小不懂事,为了私交,竟然想往政事里插手,已经被长公主严厉斥责了。今日长公主殿下陪同郡主出城上香,谢小娘子想在酒楼等郡主的话,不必再等,请回罢。”
谢明裳早有心理准备,听完了也无什么反应,淡淡地应下。
“劳烦大管事带一句回话。长公主的叮嘱,明裳字字不落地听到了。明裳与端仪郡主相交一场,岂为了害她?殿下放心,不会为了谢家的事拖累郡主。”
辰大管事见她不怨不闹不恨天尤人,绷紧的脸色放松几分。
他没有转身离去复命,却绕过大屏风往里走,直到谢明裳身前两三步时才停下,又深深行了个礼。
“谢小娘子和我家郡主交好多年,不管外面如何风言风语,谢小娘子的品性,长公主这几年是看在眼里的。其实我家主人今日派遣小人过来,主要有个故事,想说给谢小娘子知道。”
几句话大大出乎意料,不只是兰夏瞪大了眼,就连凭栏斜倚的谢明裳也侧过身来。
辰大管事清了清喉咙,郑重道,“谢小娘子听好了。许多年前,有个战功卓著的小将军——”
小将军得胜凯旋归来,入京当天,意气风发,鲜衣怒马,引得临街遥望的贵女一见倾心。
那贵女身份极高,并不忸怩,直接托人表达了爱慕之意,不在意门第差距,愿结秦晋之好。
不料,小将军早已心有所属,更直接地拒绝了。
贵女虽然惋惜,但并不强求缘分,本来以为此事就此了结。
没想到世事无常,仅仅大半年后,小将军卷入了朝堂争斗,被扣上‘杀良冒功’的罪名,全家被锁拿入狱,判了斩监候,只等秋季问斩。
那小将军绝望之下,想起了当初向他表达爱慕的贵女,在一个深夜私逃出狱,冒着瓢泼大雨,湿漉漉地出现在贵女的闺房外,长跪不起,声声泣血。
“几日后——案子被驳回重审。复审判定证据不足,斩监候的罪名太重,改判小将军去了官职,贬为庶人,送回原籍。”
说到这里,辰大管事顿了顿,“几个月后,小将军重新被征召入禁军为中郎将,回到京城,和贵女成了亲。”
兰夏听傻了。
判了全家斩监候,还能翻身?这位贵女了不得,只怕是皇亲国戚……
想到这里,兰夏忽然一个激灵。
长公主是先帝的亲姐妹,可不就是正宗的皇亲国戚?!
谢明裳已经猜出了故事的真相,良久没说话。
长公主府的驸马,看着斯文儒雅,当年却是边关征伐的武将出身。京城里知道的人虽然不多,也不算少。端仪郡主曾经悄悄跟她说过几句。
她点头道谢,“多谢长公主的故事。”
“谢小娘子仔细思量思量。”
辰大管事意味深长地道。
“两姓联姻乃是家族大事,不管何等的朝廷重臣,都会仔细挑拣姻亲,唯恐亲家遭遇祸事,自家受了连累。京城之中,最不挑姻亲身份,不必担心遭受连累,姻亲出事了还能伸手捞一把的……只有宗室皇亲子弟。”
他从袖中掏出一张薄薄的信笺,递了过去。
“长公主殿下亲笔手书的宜婚宗室子名单,请谢小娘子过目。”
谢明裳垂下眼,把手里的信笺打开。
言简意赅,一排齐整的名单。
十几个名字,全部皇室‘萧’姓,简单写明出身,年纪,在何处供职。
事情的转折太过荒谬,谢明裳居然有点想笑。
长公主毕竟身居高位惯了的,做事的风格简单粗暴,直接把京城里没有婚娶的宗室适龄男子姓名全写了下来,名单丢给她,叫她自己凭本事拉郎配。
她把信笺折起,放去桌上,说:“多谢长公主心意。多谢郡主关怀。我刚想传几句话给郡主,正好大管事来了,劳烦替我转达。”
辰大管事凝神细听。
谢明裳道:“昨晚传来的消息,这一两日朝廷就会发兵围了谢宅,出入困难,长公主的名单明裳只怕用不上。”
“谢家之罪,至今还未定论。但趁机威逼欺压于我,试图仗势欺人的坏胚子们可是板上钉钉,有一个算一个,全在这里了。”
谢明裳指了指桌上摊开的六七张帖子。又过去把纸篓里撕碎的广陵王的名刺拼凑拼凑,塞给辰大管事。辰大管事震惊地捧在手里。
谢明裳拍拍手上的灰:
“长公主府不沾染政务,朝臣家几个混账的帖子就不转交了。但广陵王是宗室子,并非朝臣。看在我和端仪平日的交情上,劳烦长公主给这坏胚子点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