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见字如面。
朴树,清流,再一次实锤了!
别人家的热门——
我们离了,我们没离,123上链接。

又或者是——
我们休战了,我们又撕了,为扛床垫,赶紧下单……

再看朴树的,开门见山就一句:
“我活过来了……”

一时间,评论区炸翻天。
有人喊话朴树:一定要好好活着,你的歌对我很重要!
甚至还有人在线作诗《致朴树》:

更多的人还是关心:
“我可爱的树,你怎么了?”
距离上一次发头条,已经将近一个月。
一露面就是报平安,这平安之中也让人隐隐担忧:
朴树到底怎么了?
01、
出道多年,朴树身上一直有一股拧劲。
这次也是。
不久前,佛山草莓音乐节,朴树被放在了“领衔”的位置上。

虽然陈粒、达达、马頔,每一位在当今乐坛也都是一呼百应。
但许多人还是呼喊着:为朴树而来。
活动当晚,朴树以《空帆船》震撼开场。
一登场,现场惊呼一片。
吉他扫弦的前奏,伴随着大屏幕之上,星空与阳光的交界。
不断变幻出各种天空、云朵、海浪、潮汐……
而朴树只是简单地吟唱着:“我迎着风。”

就仿佛将人们拉出了现实的桎梏,来到无边的旷野里。
再到那句,“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我们就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
又是一场热泪盈眶的万人大合唱。
从90年代到“20年代”,朴树依旧是太多人心中的首发和唯一。
有人说:“只要朴树还在唱,青春就永远不会退场。”
“只要朴树还在唱,就能在生活里,看到浪漫和阳光。”

但浪漫的背面,也写满了现实。
从合肥、常州、佛山,到成都、北京、上海,朴树两个月,演了18场。
在上海登台之前,朴树的身体就已亮起警报。
他大病了一场,吐了整整三天,只能偶尔吃流食。
甚至医生已经明确告诉他,身体状况很糟,不能演出了。

但朴树还是坚持上场、唱完。
为什么?
一向文艺的朴树,回答起来却一点也不“文艺”:
为了赚钱。
“乐队这两年没挣到钱,我觉得我有责任。”
没有说是为了期待,为了热爱。
而是为了钱和责任。
朴树的滤镜没因此而碎,反倒多了一层真诚加持,显得更难能可贵。
而为了乐队营业站台,这种事朴树也不是第一次做了。
参加综艺,别人问他为什么。
他还是坚持实话实说:我这一段真的很需要钱。

但把钱放在明面上,说着为钱而唱的朴树。
却又经常反其道而行之,自说自话地“加量不加价”。
在成都演出,本来主办方安排的是40分钟时间。
完全可以卡点下线的朴树,却一唱就是一个小时。
捂着胃,撑完全场,却丝毫不肯“划水”,直到被主办方强行“闭麦”。

朴树是有点拧劲在身上的。
他可以不出门,吃自己种的菜。
他可以不用智能手机,无欲无求到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但他又从不掩饰,坦诚自己缺钱,需要赚钱。
有人奇怪朴树:为什么总是活不起的样子?

50岁,出道27年,生命的一半时间都在拿奖。
朴树又为什么这么缺钱?
这么现实地总是提到钱?
02、
谈钱不伤感情。
朴树赚钱的理由,大多数还是为了感情。
在很多人眼中,朴树总是提及的那支乐队,仿佛是个“神秘组织”。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搞乐队,朴树是认真的。
就像他对音乐的要求与执着一样,乐队成员也只要合拍,不看人气。
在偏重流量和噱头的环境中,朴树的乐队无疑是“不吃香”的。
甚至可以说离开了朴树,就相当于走入了死局。
朴树也深知这份现实。
于是他一面扛起乐队的“流量”担当,一面又很难过,自己会做这样的事。

所以朴树给人的感觉,通常是两个字:拧巴。
他一面是文艺清新,不谙世事、不染淤泥,愤世嫉俗、远离物质的。
另一面又是直言世俗,不避讳谈钱,更坦诚需要赚钱的。
因为在他的身后,站着的是一支几十人的大队伍,和他们背后的几十个家庭。
环顾和朴树一个年代走过来的人。
曾经率领着“鲍家街”摇滚的汪峰,如今娶了影后,成了热搜冲击专业户。

大众讨论的,不是他的歌声、作品,而是以一次次热搜梗。
还有与朴树一样,横扫校园民谣年代的水木年华。
李健、卢庚戌二人早已解体。
各自走上新的路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也的确难掩遗憾,和一份现实的挫败感。
朴树,明明可以单干。

却如偏执一般,死气白咧地,非要拉着一帮兄弟搞乐队。
朴树,为何非得那样?
2012年,避世已久的朴树,重出江湖。
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建乐队,学学现场音乐怎么玩。
从此孤身一人的朴树,开始与这群人聚在一起。
虽然照片上仍然显得格格不入,但于朴树而言,乐队似乎成了一种寄托。
只是寄托的背后,也都是责任。
为了这根精神支柱,曾经的”孤勇者“朴树,开始频繁地站在聚光灯之下。

港剧有句经典台词,“做人最要紧就是开心,一家人齐齐整整,就是最大幸福”。
但2013年乐队的吉他手程鑫,被诊查出患上胰腺癌。
费力支撑的这个“家”,没法再齐齐整整,本就很难开心的朴树,雪上加霜。
其他成员都避而不谈,生怕程鑫知道会接受不了。
唯有朴树不懂得“高情商”,很直白地对程鑫说:
“你得了癌症,可能快死了,有没有什么愿望,你说。”

大好人生在一夕之间就要被“灭灯”,程鑫听了瞬间绝望。
朴树也没有太多煽情的安慰,只是承诺:“你安心治病,什么都不用担心,医疗费我出。”
自此朴树开始商演、开演唱会,维持着乐队的开销和程鑫的医疗费。

即便身边的人提醒他:
“几个月的治疗,已经花掉了你几年的收入。你要想清楚了,你卡里的钱根本不够。”
但朴树根本不听劝,只要程鑫还有一线希望,他就从没想过放弃。
甚至一向放纵不羁爱自由的朴树,打算把自己逼到墙角:“不够我们就去签公司,卖身嘛。跟救人比起来,合约算什么。”
在朴树看来,自己选择了这一群人,他们也曾给自己力量。
那就要坚持到底,做事该有这份讲究,做人也该讲这份情义。

所以得到一些,也必须舍弃一些。
那些曾经不喜欢的事,朴树也都学会了一一妥协。
而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和情分,这种“粉碎自我”,值!
只可惜朴树的奔走,与拼尽全力,没能换回程鑫的健康。
2014年2月6日,程鑫因病离世。

朴树给他的临终关怀,依旧没有煽情的长篇大论。
只是红着眼眶,给出八字承诺:
“我会照顾好你妈妈。”
而朴树乐队的介绍里,至今仍然挂着程鑫肩扛吉他微笑的照片。
就像他从未离开。

对故人的纪念,这或许也是朴树一意孤行,要把乐队坚持到底的另一个原因。
而“暴躁”谈钱的中年朴树,曾经却是一谈钱就“暴躁” 的愤青。
朴树的抑郁症,也被很多人说是“小布尔乔维亚综合症”。
换句话说就是:“装”。
朴树,到底在“装”什么?
03、
1994年,大二的朴树,选择退学。
之所以这么叛逆,因为大学本不是他所欲。
朴树的父亲是北大教授,双星探测计划发起人之一。

从小生长在北大家属院,朴树的路子几乎也是约定俗成的:
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留学,当科学家。
小时候的朴树,并没有太多想法,成绩好当班长,也曾是眼神有光的快乐儿童。

只不过“小升初”考试,成了他的“劫难”。
朴树以0.5分之差,没能进入规划好的北大附中,去了一所普通中学读书。
父母虽然从未说过什么,但朴树受不了:
“真是觉得低人一等。你没考上,你爸妈都没法做人了。”
家属院里那些考上了的孩子们,也都对朴树围追堵截,拿这事“挤兑”他。
朴树郁郁寡欢,眼里的光,也暗了下来。
父母十分担心,带他去做心理测试。
其中有一道题是:“如果你死了,你觉得身边的人会怎么样?”
朴树答:“无动于衷”。
测试结果“差3分变态”,朴树患上了:青春期忧郁症。
童年阴影,也成了朴树成年后抑郁症的根源。

在朴树还徘徊在人生分界线上的时候。
哥哥朴石先一步离开大院,做起了流浪歌手。
朴树大受震撼,开始学吉他,在音乐里寻找解脱。
父亲没有勉强他,而是尊重支持:
“我自己不懂音乐,但我尊重孩子的兴趣,音乐是他的生命,正如学术是我的生命。”
但在家长眼里,音乐也只是爱好,按部就班的路还是要走的。

高考那年,朴树硬着头皮去考试,拿到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的录取通知书。
事成之后,朴树”原形毕露“,对父母说:“我是为你们考的,不去了啊。”
父亲采取迂回路线,告诉朴树大学里有多热烈和自由。
这才算改变了他的主意。
但真正进了大学,他发现根本不是理想中那么回事。
于是两年后,他决定退学,告诉父母:“我想做一次自己。”
二老也没再强迫,只是告诉他:我们反对,但决定你自己做。

但在朴树这,自然是反对无效。
他离开学校,跑到小河边弹吉他。
一段时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关起门来潜心写歌。
母亲见此情景,问他:要不要出去端盘子?
朴树意识到,似乎是时候该赚点钱了。
恰逢其时,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清华高材生宋柯,创办了独立品牌“麦田音乐”。
主打一个校园和人文气息。
1996年春夏之交,急着赚钱的朴树,在高晓松的引荐之下。
敲开了麦田的大门,要卖自己的歌。

抱着吉他,唱了几首。
听后高晓松伤心,宋柯流泪。
两人双双疑惑:你为什么不自己唱?
朴树答:“我只想卖歌给你,因为我需要钱出唱片。”
不打算”放树归山“的高晓松,循循善诱:“你为什么不找人帮你出唱片?”
朴树依旧炸裂言论:“因为圈里的这些音乐人都是傻子 ,他们根本就不懂我的歌。”
高晓松一听,立马打包票:“你好好写歌吧,唱片我帮你出。”
本想数一数钞票转身离去的朴树,成了麦田第一个签约歌手。

但专辑这事,一鼓捣就是三年多,直到1999年底,朴树的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才问世。
有道是好饭不怕晚。
朴树独一无二的声线和气质,加上张亚东、窦唯的加持。
一推出狂卖30万张,朴树和金庸、王菲一同入选那年《北京晚报》“十大文化人物”。

有人评价“石破天惊”的朴树:
“诗化的歌词和脆弱的嗓音,像一种别样的朗诵,特别打动人。”
作为麦田三原色“红白蓝”系列之“白”,朴树成了公司的“名片”。
专辑里的《白桦林》、《那些花儿》,直到今天仍旧是许多人的保留歌单。
出场即巅峰,朴树成了“人物”,各种优秀歌曲、新人奖飞奔而来。
第二张专辑《生日夏花》,继续创造奇迹。

在唱片市场不甚景气的年代,短时间之内卖出50万张。
别人都劝朴树乘胜追击,让他赶紧做专辑抓紧赚钱。
朴树却回:为什么要赚钱?
别人挤破头要上的春晚,朴树只觉得和自己风格不符,千方百计想要躲掉。
最后迫于公司压力上台,前一天自己蒙着被子哭了一晚上。
别人合家欢乐,他一脸忧伤。

站在台上颓废又无奈,失落又失望。
在欢悦跳脱的人群中,朴树就像一个休止符。
巨大的名利涌动之下,朴树没有“我终于红了”的兴奋。
而是压抑、喘不过气。
他感到,当年小河边那个好不容易找到的自己,又要被人潮人海和没完没了的闪光灯,杀得“失魂落魄”。
朴树自闭了。
在最能赚钱的时候,他宣告隐退。

搬到北京郊区,踢球、搞创作、吃老本。
但多年之后,他也承认:
钱,名声,他也曾一度为此沾沾自喜,而且颇有些年迷失其中,沉湎于享乐,无力自拔。
“直到老天爷,收走了赋予我的所有的才华和热情。”
这也是他看似糊涂,却一朝清醒,把自己关起来,像蛇一样”蜕皮“的原因。
直到2017年,朴树人生中“唯三”的专辑《猎户星座》才千呼万唤使出来。

歌迷泪目:终于等到你,还好你和我都没放弃。
朴树也用他的歌声与文字诉说:
“此生多勉强,此身越重洋。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出泪光。”
04、
十年之间,曾经的朴树”生如夏花“,都是泰戈尔式的诗意。
后来的朴树跨过山和大海,走上“平凡之路”。
但他还是那个他。
出场依旧是冷场王,开口就能把天聊死。

宋柯的烤鸭店开业,别人好奇问他:你有去光顾吗?
朴树耿直回复:不吃鸭子,不太爱吃肉。
不恭维不带货,就是这么直来直往。
在《跨界歌王》总决赛,帮唱王子文时,被问到来的原因。
他简单夸了几句王子文后,就说了心里话:
“说实话,我这一段真的需要钱。”

到了第二季,他到现场为王珞丹帮唱《清白之年》。

主持人问:这次为什么参加?
朴树依旧实诚发言:为了工作,为了赚钱。

主持人持续“进攻”:为什么选这首歌?
似乎期待着朴树能说出什么“场面”话。
但很可惜,他是朴树。
他只会说:经纪人选的,因为想推广它。

第三季,朴树还是来了。
熟悉的问题,回答依旧还是不绕弯子:
“我喜欢唱歌,我在做一份我爱的工作,我还能赚钱。”


不仅是上节目,接受采访,即使是金马奖朴树也敢不给面子。
举着奖杯说不出一句“天下太平”的话,冷着脸输出:
“很多年来我对华语电影也有成见,我认为这只是钱的游戏!”

按说这样的朴树,是该被钉死在朋友圈黑名单上的。
但他的身边从不缺朋友,并且都是十几年以上的那种老伙计。
朴树刚出名不久,一个朋友实在周转不开。
给他发了个信息:借我15万。
朴树不问缘由,只问两个字:账号。
许多年之后,朴树也“经济危机”了。
想到这15万,给朋友发了两个字:还钱。

朋友要多还他四十万,他却坚持只要本钱。
他毫不掩饰自己和张亚东闹矛盾,原因只是在创作《NEW BOY》时,张亚东为赶时间创作了不满意的歌词。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他向来拒绝得干脆。
准备了两年的专辑忽然不想出了,因为他发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

而对于爱的事又是执着到底。
烧钱组乐队、找最顶尖的设备制作自己的音乐。
也默默捐钱建希望小学,演出的钱也总会如承诺般,拿出一部分打入程鑫母亲的账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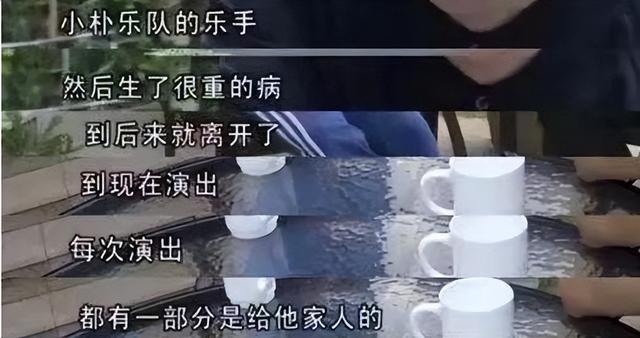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朴树在娱乐圈几出几入。
扛着现实,也带着梦想。
在朴树的《生如夏花》里,第一首歌的位置赫然放着:《傻子才悲伤》。
但朴树就是那个偶尔灿烂,总是悲伤的“傻子”。
刚入行时,他看透了这个圈子。
2015年,他在博文《十二年》中写道:
“从一开始,就厌恶这个行业,并以之为耻。电视上的明星们令人作呕,我毫不怀疑我会与他们不同。”

成名之后,他受不了无法顺从本心,被迫营业的苦恼:
“被裹挟着,半推半就着往前走,边抗拒边享受着它给予我的恩惠。”
所以他悲伤。
把自己关起来许多年,一朝回归。
他接受不了行业的现状,满眼尽是荒凉和绝望:

于是他,愤怒+悲伤。
出走半生,归来,朴树还是那个骄傲的易碎着,沸腾着也不安着的孩子。
别人感叹他:你始终是少年。
他却说自己:不是少年,也不老成,只是别人都过早地老去了。

在人人只看到流量的巨大红利,娱乐至死的氛围中。
朴树却如“叛徒”一般,像他的名字一样,活成了一棵朴素的树。
长在庭院中,枝叶遥望着远方。
也接受着叶落之时的尘归尘土归土。

身上带着阵痛,印刻了一圈圈或温情或悲情的年轮。
50岁的朴树,在试着与这个世界和解:
“你没有那么重要,请别面面俱到。你也不必做个好人,只愿你心开自然。”
也依旧在与之对抗:“像落叶一样勇敢,无牵无挂。”

懂他的人爱他十年如一日,而不理解他的人会说他“装”。
“当批评成为一种错误,那赞美将毫无意义。”
同样放在朴树身上,当浑浊成为一种常态,那么清流,就显得“装”且孤芳自赏。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两轮日月何奔忙,百年弹指,是真是装,是蹉跎虚度,还是阵阵回响。
朴树的歌里已经写满了答案。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苏打叶
©原创丨文章著作权:皮皮电影(ppdianying)
未经授权请勿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