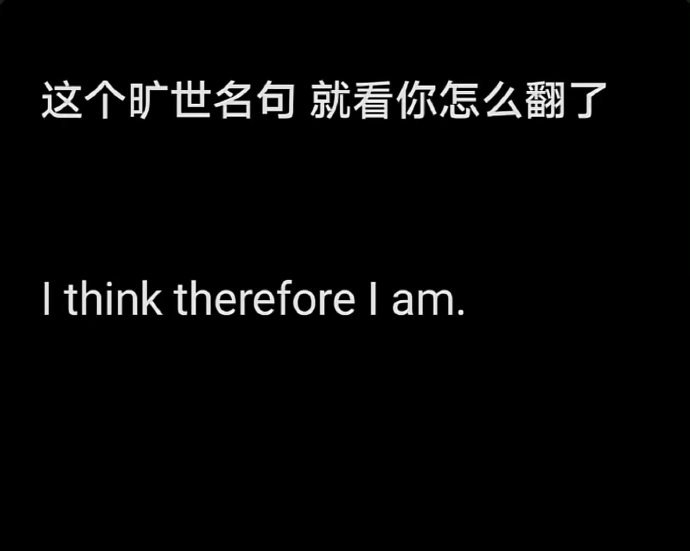简介:
一梦千年事,彩云空,香雨霁。淡扫蛾眉,盈盈照秋水。愿得因缘未尽时,君须记,捉月盟言,扇底清歌,萧萧雨。
穿越一千三百年前,她是内廷六尚之一的尚宫,几经坎坷,忍辱偷生,游走于宫闱,槛花笼鹤属于宿命?从不善权变到步步为营,且观风云变,似沧海一鳞。红颜渐老,芳华易逝,大明宫烛泪斑驳,凝锁霞帔背后的孤影。
缘之何起?情之未尽。
天子、将军、名医,如何抉择?
女皇、女王、女官,剪不断,理还乱,缕缕牵扯。
千秋的功罪,千古的洛河,终究何人评说?

精选片段:
大唐永徽四年,春。
林木才吐新绿,杏花初绽枝头,密林间是一座壮观宏大的帝王陵墓,坐北朝南、宫阙巍峨,御道两旁的虎、犀等石刻,个个浑厚质朴、气宇轩昂,这里就是唐高祖李渊长眠的山陵——献陵。
荒寂的偏宫在庞大的宫殿群里毫不起眼,杂草丛生,蛛网交错,潮湿的地面上铺了几块苫席,萧可已经昏迷了两天一夜。元如娴滴着眼泪,又给她喂了几勺清汤,怎奈还是不醒,颤巍巍摇着她,轻轻呼唤着她,这是她最后的希望。
“王妃,醒醒,求求你快点儿醒来,娴儿有好多话对你说,孩子们已经走了两天一夜,且不说千山万水,岭南乃瘴疬丛生之地,他们年纪又小,如何受得住,你快醒醒,帮帮娴儿吧!”因受谋逆案牵连,她的儿子彦英与仁儿、曦彦还有承宣一起被流岭表,她一个弱女子无依无助,除了苦苦求诉于王妃,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她连亲生之子都不顾,如何顾得了彦英,何必白白求她。”韦琳琅靠坐在一角,终日以泪洗面,恨不得手持利刃在这个假王妃的身上插上几刀。
“什么王妃,明明是个来历不明贱婢,谋杀了王妃,害死了殿下,剥皮抽筋也不解恨。”袁箴儿恨极了萧可,长身而起,狠命踢着她,“贱人,装什么装,你给我起来。”
正踢着解恨,却被一个小人儿抱住了腿,竟是贱婢的女儿。
“不要打我阿娘。”李婵娟怯生生看着她,淌着两行泪。
“小杂种竟敢拦我。”她一脚将李婵娟踢倒,再要踢人时,却被韦琳琅制止。
“够了,就算你踢死了她,也于事无补,你也别想活着了。”韦琳琅出言警告,虽然已是家破人亡,骨肉离散,但没必要为了这个假王妃,再赔上一个人的性命。
偏殿里又静了下来,李娉婷将婵娟扶起来,拉着她躲在了母亲身后,生怕袁箴儿再拿妹妹出气。
入夜,飘过一阵雨丝后,明月又挂在天际,淡淡月华洒进了偏宫里,映照在萧可脸上,静谧而柔和,她的睫毛微微颤动着,头一偏,看到女儿与娉婷靠在墙角里睡着了,蜷缩着身子互抱着取暖,连条御寒的毯子都没有,窗外月色皎皎,偶有夜风从残损的窗棱吹过。
是梦?是醒?
一片茫然。
“王妃,你终于醒了。”元如娴扑了过来,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连连哀告,“你救救彦英吧!只要让他回到我的身边,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的大恩。”
萧可吃力的坐起来,脑子里乱得跟浆糊一样,什么彦英?这又是什么地方?元如娴也在这里,差点儿认不出她,粗衫布裙,青丝零乱,与以往大相径庭,残存的记忆里,有仁儿的疾呼声,有慕容天峰高大的身影,他手上有明黄色的卷轴,长流岭表,他是这么说的,还有三郎,费尽了心思,仍是镜花水月梦一场,想到此,心口痛若刀绞。
“王妃,孩子们已经走了两天一夜,你快想个办法吧!他们那么小,走不到岭南的。”元如娴怔怔看着她,悲痛之余,就是彦英,王妃会有办法的,王妃的办法很多,何况其中也有她的仁儿和曦彦,她不会不管不顾的。
萧可一如静默着,尽量抚平心口的痛意,岭南距离长安,最近的三千里,最远的六千里,别说是孩子,就连大人也走不到那里去,多半在路上就遇害了,他们做得这么绝,怕是早就想到了斩草除根,不过是一死,听天由命吧!到黄泉做伴也未尝不可。
“王妃,你怎么不说话,救救彦英吧!还有仁儿、曦彦和承宣,你真的不管他们了?杨滟妹妹已经自尽了,她临终前把承宣交给了你,王妃……。”她的无动于衷,冷漠,让元如娴彻底心寒,这是最后一线希望,若她真的是铁石心肠,对亲生儿子也不闻不问,彦英还能独活吗?“你就说句话吧!岭南不是人住的地方,何况是孩子,那里是蛮荒之地,瘴气、毒虫肆虐,河里的水都有毒,喝上一口就死。”
“娴儿,别求她了,没用,她有自己的打算,用不了几天就会离开这里,你求她岂不是白费唇舌!你放心,彦英和承宣定会平安无事,殿下在天之灵也会看顾他们的。”韦琳琅一边哭,一边把娴儿扶起来,同时用最为怨毒的目光诅咒着萧可,“有人设了圈套让我们往里钻,平白无故担了这个罪名,别看她现在活得滋润,可善恶终有报,殿下在天之灵也不会放过她。”
袁箴儿直听得义愤填膺,想起从前种种不公之处,便要冲上去打人,却让韦琳琅死命抱住。“你还敢动手打她,不想活了,何必再为这种人丢了性命。”
李婵娟早已被争吵声惊醒,看了看阿娘,又看了看庶母们,不懂她们为何争吵,不懂为何放着好好的家不住而来到这里,更不懂耶耶和哥哥们去了哪里,她只知道母亲很伤心,一句话也不敢多问。
……
高大的围墙挡住了壮丽的宫阙,只能看到头上一方天空,偶有几只鸟雀飞过。春日里,窗外闲花野草遍地,宫门终日闭锁,这一方荒芜的偏宫,就成了她们的天地。偶尔,宫门才会被打开,总是有两个年老的献陵内侍进来,手上拎着两只篮子,然后放在台阶上,转身就走,一句不言,不厌其烦地再将宫门锁上,日复一日。
李婵娟从篮子里捧出一碗稀粥,颤巍巍迈着步子,小心翼翼端给了母亲,怎奈她又不想吃,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了,她一直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阿娘,你不要死。”想到阿娘会死,她害怕了,然后放声大哭。
听到哭声,元如娴与女儿娉婷一起走了过来,虽在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把她排斥在外,摸了摸她的脸,冷冷冰冰的,触了触鼻息,可以用气若游丝来形容,她不想活了吗?她不是已经找好了退路,她应该高兴才是啊!伸手摇了摇她。
“王妃,醒醒,你已经不吃不喝好几天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婵娟怎么办?”
被她这么一摇,萧可还是醒了,适才是睡过去了,梦里都是过去那无忧无虑的日子,骑着踏燕在杏林里穿行,穿着胡服在西市里东游西荡,甚至梦回安州,那座古朴的石桥犹在,漫天都是银杏树,叶子就似一个个小扇子。
“吃点儿东西吧!婵娟刚才都哭了,你别吓着她。”元如娴虽被她害到如斯地步,可记挂着彦英,不能让她就这么饿着,只要她活着,总会有法子的。何况她现在虚弱无比,整日靠在墙上一言不发,她后悔了吗?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给她喂了几口粥,又拿过来一条毯子,抖开遮在她的身上,“这里不比长安城,夜里寒,当心着凉了。”
萧可看着那条毯子,崭新的,很金贵,和这所破败的偏宫格格不入,元、韦两家在长安都有至亲,时不时还能得到接济,可是自己呢?飘落在一千三百年前,举目无亲。
李婵娟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寻到十来朵洁白的花儿,欢欢喜喜拿给了母亲,想让她开心起来,“阿娘,好看吗?院子里还有好多。”
萧可点了点头,硬是露出了一个笑容,元如娴说得很对,若是自己也不在了,婵娟该怎么办?她还小,今年还不到五岁,难道让她一辈子留在这里?女儿生于朱邸,长于锦绣丛中,如今衣衫褴褛、蓬发覆面,这就是‘罪人’应得的待遇?生不如死的待遇?还有婳儿,虽然被天峰抱回了府里医病,但现在是好是歹,一无所知。
刚刚阿娘笑了,婵娟又去院子里找花儿,引着比她大一岁的姐姐娉婷,她刚走上台阶,就被袁箴儿猛推,人小站不稳,直接滚落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
“贱婢生的小杂种,你还有心思采花儿,你母亲不是人,你更不是个东西。”袁箴儿恨透了,就拿她的女儿出气,朝婵娟重重踢了几脚,多年的积怨,一气儿迸发泄出来。
女儿哭得可怜,萧可却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横眉怒视着袁箴儿,费力的说道:“有本事,你冲我来。”
“你就省省吧!贱婢,还摆什么王妃架子!”袁箴儿恨在心头,又无视韦琳琅的警告,冲上去打了她十来下子,“我打了你,这仇你记着,我不怕你报复,你这荡、妇,我恨不得把你剥皮剜心,以祭殿下的在天之灵!”
让人一口一个荡、妇骂着,萧可痛在心间,大概外人就是如此看待她的,反正自己问心无愧。
眼看事情闹大,韦琳琅这才把婵娟抱了起来,斥责袁箴儿道:“你打她就是了,拿孩子出什么气。”
袁箴儿嗤之以鼻道:“孩子,还不是知道是谁的野种呢!这荡、妇早就不检点了。”又见萧可用凌厉的目光瞪着她,便伸手扯住了她的头发,“你这荡、妇,我还说错你了不成!你做下的那些事,别说是我,满长安城里的人,谁不知道!你跟……。”
“够了!”韦琳琅厉声阻止,生怕她说出不该说的话。
袁箴儿这才松开了萧可,临走还狠命捶了她几下。
就在这时,宫门又被推开,十来个内侍闯了进来,他们拖了萧可就走,甚至不给她回头的机会,在婵娟的哭声中,元如娴也跟着担心起来,难道真的要三司会审假王妃一案?王妃可是她唯一的希望。
永徽四年的春天,冷冷凄凄,而那桩震动政坛、举国哗然的谋反案也才刚刚落下帷幕不久。结案之惨烈,举世皆惊,两位亲王、两位公主赐自尽,三位驸马被处死,多有皇亲国戚、重臣高官受到罗织株连,国舅长孙无忌权势煊天,大兴冤狱,诛杀异己,就算不相干的旁人,闻之也会心惊。
而年轻的大唐皇帝也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来自首辅大臣长孙无忌的震主之威,诏令李勣为司空,仍兼任开府仪同三司一职。这一次,李勣也欣然接受,前车之鉴犹在,未免国舅的屠刀砍向他,为自保不得不挺身而出。
大理寺内,少卿辛茂将惶惶不安,正卿段宝玄现已告病在家,陛下诏令假王妃一案由他会同御史中丞贾敏行、刑部尚书唐临主审,可事到临头,唐临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遂派来一个名叫卢承庆的官员顶替,果然这烫手的山芋无人肯接。假王妃现已羁押在大理寺候审,不曾问上一句,又接到千牛卫大将军慕容天峰的秘信,明着暗着要他徇私枉法,草草审问一遍结案了事。
千牛卫大将军纵然有八个脑袋也不敢对他这么说,背后一定有人授意,他也料到了授意之人是谁,他与假王妃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太多了,长安城里传得沸沸扬扬。怎样审案才能让上下各方都满意?何况假王妃谋杀了谏议大夫萧钧的女儿,也就是宫里极为得宠的萧淑妃同父异母的姐姐,自古杀人偿命,要他如何枉法?只好先将此事搁着,现在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只好硬着头皮上,走一步,说一步。
一时间,大理寺升堂问案,三位主审官员依次坐在了主位,御史中丞贾敏行一言不发,卢承庆也在那里干巴巴坐着,合着他们到大理寺来袖手旁观了,据说卢承庆得罪了长孙无忌、褚遂良,被一贬再贬,正在不得志的时候。
一班正、丞、主薄、司直皆到齐,自有校尉将假王妃带上来,手、脚均戴有锁镣,青衣素裙,长发披散,整个人摇摇欲坠,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还当是什么凶神恶煞,原来是个弱质纤纤的女子,她不但是杀人凶手,还假冒了王妃,鸠占鹊巢长达十三年,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萧可原不想跪,却被两个校尉狠命按了下去,略略抬头,才看到那三个主审,两个不认识,只见过辛茂将。离开献陵有一个多月,也在大理寺的牢狱里待了一个多月,牢狱里天昏地暗,远不如这里明亮宽敞,谁让自己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大理寺自然不会安排别舍给她,原来坐牢也是了分贵贱的。
辛茂将首先问案,“你到底是什么人?如何谋杀了萧泽宣?她的尸骨如今在哪里?”
半晌,萧可面无表情,根本不想理他。
“本官问你话呢?”辛茂将再问。
“你找她的尸骨做什么?”萧可终于开了口,有气无力的。
辛茂将怔了一下,到底谁是问案,看看左边的贾行敏,又看看右边的卢承庆,一个耷拉着脑袋,一个提笔作画,敢情都不管这事儿,只把他一个人推出来顶缸。
“人命案,须要尸、伤、病、物、踪,没有尸体,也断不了案子。”卢承庆终于插了一嘴,对犯人和颜悦色。
“我还以为你们连一个死人也不放过,准备把她开棺戮尸,挫骨扬灰呢!”萧可颤巍巍道:“我不知道她的尸首在哪儿,她摔下山崖死了,然后······”。
说着,便淌下了眼泪,她曾听到牢狱里的女囚们说闲话,葬在安州王子山的杨慧仪坟茔被毁,墓志铭也被磨平,前吴王妃都是这样的待遇,三郎怕是比这更惨,说不定已经暴尸荒野了。
“是你把她推下去的?”辛茂将倒是挺吃惊的,原来萧泽宣是摔下山崖毙命,他原没有想到这案子审问起来如此顺利,假王妃不抵赖,不狡辩,从头至尾坦荡荡,案子快要水落石出了,正好儿把这烫手的山芋扔出去。
“我可没有这个本事。”萧可回过神来,拭去了泪水。
“那是谁把她推下去的?”辛茂将再次询问,怎么这个假王妃只说半句话。
萧可笑了起来,当年梅园村那一幕涌上了心头,当时她就在山崖边上,萧泽宣死命拽着她,非要拉她一死不可。
“你笑什么?”这样的笑声,辛茂将直听的后背发凉。
萧可嘲笑着他,“你真的想知道吗?就怕你不敢知道。”
辛茂将正义凛然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萧可甚觉得很好笑,这个一文不名的大理寺小官儿居然大言不惭的说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她看着辛茂将,轻飘飘道:“是雉奴一脚把她踢下去的。”
话音刚落,辛茂将就立了起来,再看贾行敏与卢承庆两个,早已经傻了,假王妃一语,满室皆惊,连喘气的声音都没有了。
萧可正跪着难受,干脆歪在那里坐着,抬眉一蹙,直视那些个官员,“各位不信吗?不然你们把他叫过来跟我对质。”
辛茂将再也审不下去了,三司会审终于给搅乱了,审来审去,审到了皇帝陛下身上,谁敢把他叫过来对质?照此情形看,这女子真的绝非等闲之辈,要不然谁敢冒充王妃。
御史中丞贾敏行在一旁使着眼色,那意思就是暂停审讯,容后再行议,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不过是夹夹打打,这女子大来头儿,也不敢打,也不敢夹,只能放回原位供着。
就这样,萧可又被押回了女牢,牢狱里果然是暗无天日,连一扇窗户都没有,迎面而来的,是发了霉的泔水味,刺鼻难忍。好在她住的牢房很宽敞,地上铺的草席很厚实,躺在上面休息也不觉得有多累,每日只有两顿饭,均由几个女狱卒提来。
住在萧可隔壁的,是一个叫作淳于氏的美艳妇人,见她被押回,便好奇的寻问起来,“今日是审问你吗?你犯了什么罪?”
萧可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淡淡道:“杀人。”
淳于氏似找到了知音,欣喜道:“我也是杀人,但他们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就把我一直关着,这样也好,反正他们都骂我是荡、妇,家是回不去了,他们诬陷我谋杀亲夫,又拿不出铁证,你说好笑不好笑。”她说得甚为轻松,使劲儿把脑袋探出来寻问:“哎!你也是谋杀亲夫才被抓来的吗?”
听到这话,萧可如同触了电一样,直挺挺坐了起来,隔着牢狱的木栅冲着淳于氏大喊,“没有,我没有,闭上你的嘴巴,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淳于氏不以为然道:“我只是问问,你心虚什么!”
“你才心虚,不许诬蔑我。”
蓦地,萧可忆起了袁箴儿骂她的那些话,为了不曾做过的事,让人诟病,她已经支撑不住了,千里与曦彦生死未卜,他们一个不满十一,一个刚刚六岁,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婵娟仍在献陵,孤零零无依无靠,她们恨透了自己,势必把一腔怨气出在她的身上,虽然婳儿在慕容天峰的府上,但日后福祸未知。还有三郎交给她的鱼肠剑,二月初二那日在府里晕了过去,鱼肠剑也随之不见,那是他唯一留下的东西,是太宗皇帝的心爱之物,不能轻易落入他人之手,到现在,连他唯一留下的遗物都保不住。
到了送饭的时辰,女狱卒们依次打开牢门,今日分给女囚们的是一大桶似粥非粥,似浆糊非浆糊的东西。萧可没有一点儿胃口,反正那些东西也难以下咽,总觉得有一股酸水在胃里搅动,想吐又吐不出来,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隔壁的淳于氏抱着大碗吃的正香,巴巴瞅着萧可道:“你怎么不吃?是不是病了?”
萧可摇摇头,又开始吐,还是那股酸水在作怪。
“你要是真病了,我就给你往上报,会有大夫来给你看病的。”
萧可摇头,表示没有必要。
“你这是什么病呀?是不是肚子里不舒服?”淳于氏好像发现了什么,天天看着她,真有不对劲儿的地方,“你是不是有了?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我怎么没见你来过月事?”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萧可不由自主抚上了自己的腹部,思绪又回到正月十五,大雪纷飞的夜里,她扮作了千牛卫,夹在慕容天峰的禁卫军中混进了大理寺,在别舍见了他最后一面,当时发生了什么?抱着他,吻着他,非要他以身相许不可。那天,他穿着一件天青色的圆领袍,上面缀着金色梅花样的钮子,亲手把那些钮子一一解开,然后把他扑倒在地。
“难道你真的有了?”见她呆呆的,淳于氏再问,“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可别瞒着,有我帮你呢!保证不说出去。”
萧可回头瞅着她,突然觉得身上也不是那么难受了,原本是了无生趣,不想活了的,可现在多了一个孩子,当然要抚养他长大,何况还有婳儿和婵娟。若千里、曦彦真的遇到 意外,就算拼了命也要保住这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