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与司法的分离,不仅是道德理论家本身的问题,它还是社会分工的问题,职业化的问题。
 世纪末的主题:多变的道德疑难和多样的道德理论
世纪末的主题:多变的道德疑难和多样的道德理论1897年,霍姆斯在《法律的道路》中,预言道:“时下主宰法律理性研究的人还是法条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

20世纪60年代,这一预言便开始在美国实现。
1960年,芝加哥大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家科斯发表了震撼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社会成本问题》。
在该论文,科斯深入地分析了交易成本对法律安排的影响。

而这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在卡拉布雷西关于侵权、波斯纳关于诸多法律问题以及博克关于反托拉斯的强化和推动之下,经济学迅速席卷法学研究的各个方向。
财产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甚至公平、福利、效率、正义等价值层面的问题都可得见经济学的身影。
众多学者感叹法律经济学帝国的到来,法律经济学成为当时唯一的法学流派。

但“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问题远不会那么容易解决,历史也不会像福山说的那样会有一个终结。
在科技送来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道德疑难;当法律经济学的革命涤荡陈旧的法学界时,众多人身权案件也挤进了美国最高法院。
在《美国法律史》中,伯纳德·施瓦茨写道:“法院的重点在20世纪中期前就已经从维护财产转向保卫人身权”。

在《20世纪美国法律史》,劳伦斯·弗里德曼亦谈道“公民自由权的案件在民权领域有所增加,并在20世纪八十年代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主要受理案件”。
由此,对于最高法院来说,它不得不面对两大问题:
(1)判决的超文本逻辑。

在普通的案件中,大法官们或以宪法性法律为据,或以先例为准,对案件进行裁决。
但是,对于各类道德性案件、涉及新兴权利的案件,大法官们却无从下手,先例或宪法性案件从未告诉过他们正确的答案。
因此,如何利用恰当工具解决道德疑难并获得普遍认可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2)司法审查权的“反多数难题”。
自从马伯里诉麦迪逊以后,司法审查权便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最高法院的权力。
而这个所谓的美国最高法院的“独立宣言”却带来了巨大的反多数难题:非民选的法官凭什么否决代表多数的国会所通过的法律无效?

这个问题一直在美国宪法学者之间争论不休,并在最高法院需要频繁对法律进行解释、推翻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不仅如此,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诸多判例中,与本文主题联系较为密切且较为重大的案件如“布朗诉教育委案”“罗伊诉韦德案”“临终关怀团体诉华盛顿州案”。
处理了种族歧视,堕胎,安乐死等重大的道德疑难,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该案直接导致了美国分为了两派——生命派和选择派。
他们在往后的几十年间,水火不容,互相攻讦,甚至引发了众多暴力事件。
直到2000以后,美国仍因堕胎而“分裂”。

“盖洛普2000年10月初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的生命派和选择派的支持者分别为45%和47%,基本上势均力敌。”
与此同时,美国最高法院也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自由派和保守派更为重要的战略阵地。
比如,在“罗伊诉韦德案”中,女权运动成为了该案的导火索,共和党执政期间,历届总统皆以推翻罗伊诉韦德案为其任期内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

作为反对堕胎斗士的里根总统便声称:“一个社会抹杀人类生命一部分——胎儿的价值,这个社会也就贬低了全部人类生命价值”。
可见,道德疑难的解决、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还是社会问题。
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人们一般会选择怀旧的方式来保持平衡,诉诸于超现实的逻辑来论证合理性,美国学术界也不例外。

目力所及,当时流行于美国的宪法理论包括但不限于联邦主义者学会的宪法原旨主义,德沃金的宪法的道德解读,布鲁斯·阿克曼的“宪法时刻”理论、约翰·伊利所主张的“程序导向”的宪法理论以及约翰·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等。
但,无论哪种理论,皆是复兴了深植于自由主义的道德理论或者埋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立法原意,皆是在抽象价值或者概念上进行打磨、论证。
不得不说,“道德法律理论和富有道德意味的法律理论在一部分美国法学学者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圣杯”。

不得不说,道德理论的繁荣发展远离了霍姆斯的法律之路,经验研究的预言并没有完全到来。
1973年波斯纳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欲以财富最大化为准则,彻底分离法律与道德。
但在德沃金等人的批判下,他节节败退,不得不承认法律经济学也无法解决一些道德疑难,法律与道德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分离开来。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他开始以实用主义重建法理学,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对法理的各个主题进行分析。
1997年,霍姆斯的讲座上,法律与道德的问题再次成为波斯纳需要关心的问题,霍姆斯的预言也再次需要进一步推进。
不过,与十几年前所不同的是,他更能坚定自己清除法律中的道德迷思的立场,更能坚定地与道德理论家论战到底。

因为,他拥有了更强有力的武器——实用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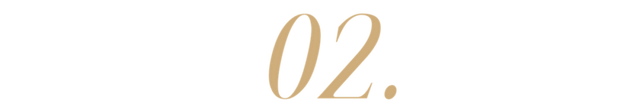 法官需要何种知识:抽象理论还是实证研究
法官需要何种知识:抽象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在批判完直接道德推理之后,波斯纳开始调转枪头对准了间接道德推理。
间接道德推理也被称之为宪法理论,其主要解决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反多数难题,其目的在于论证或批判最高法院承认新兴权利之合法性。

由于这些宪法理论常常诉诸于政治道德、哲学思辨,也便被波斯纳纳入到批判的行列了。
并且,在诸多宪法理论中,波斯纳批判最为彻底、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阿克曼的“宪法时刻”,因此,笔者将以波斯纳对阿克曼的批判来引出波斯纳真正关心的问题。
在阿克曼早期的学术研究中,其主攻的方向是法律经济学。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学术热情就被宪法理论所吸引了。
他认为,美国的宪法理论是欧洲式的,一元民主制的。
这些理论并不符合美国的宪政传统,无法解释美国的宪法和政治活动。

因此,他从历史的深处去发现美国宪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二元民主。
在他看来,二元民主“寻求区分民主制下作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决定”,“第一种决定是由美国人民作出的;第二种决定则是由他们的政府作出的”。
而只有很少的情形下,人民才出场进行决定。

大体而言,只有在具有革命自我意识的时期,才可能出现满足的情形。
例如美国建国、内战、南方重建以及罗斯福新政就是这样的时期。
这样的时期被阿克曼称之为:“宪法时刻”,它表达了一种深刻、广泛、真正地且无可挑剔地有合法性的民意,这时人们可以作为单独的公民思考和行动。

并且,在政府作决定的常规政治时期,法官利用革命意识时期所采纳的原则去废除日常政治的立法产品时。
阿克曼认为,他们并非不民主,他们忠于的是更为精致的民主概念,他们关注的是革命时期人民经过大量的公共辩论之后深思熟虑的判断。
显然,阿克曼所描述的是一种历史的政治学,是一种相当抽象的理论。

对此,波斯纳认为,阿克曼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应当承认革命激情有其合法性。
假定某个时刻出现了希特勒那样的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家当选总统,他便可以说服国会颁布一个显然违宪的制定法,把基本的公民权利统统取消。
如此,便形成了阿克曼所说的宪法时刻,如此,下一代法官就有义务来维系它,如此,则极有可能会导致极权主义。

虽说革命时期或许会导致民主立法的审议更加真诚且广泛。
但这并不能自然地得出,当民众的思潮在没有表达为实在法之前,法官就应当屈从于这股强大的潮流或者利用他们对潮流的理解来任意解释美国宪法、随意限制政府权力。
对于波斯纳来说,这种超本文逻辑的宪法观点,这种没有实证的实证主义是极其危险的。

并且,阿克曼对宪法时刻的划分也是个人化的。
以罗斯福新政为例,波斯纳便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宪法时刻。
阿克曼认为新政是整体一致的努力,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福利国家。

波斯纳却认为新政仅仅是“一系列党派的、特定的、机会主义的措施,回应那令人畏惧却理解糟糕的经济危机,回应焦躁的利益群体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在波斯纳看来,很难辨认出罗斯福新政存在一些对于社会正义坚定不移的承诺。
简言之,阿克曼的宪法时刻的划分标准具有神秘化的倾向,很难得到所有人的一致同意。

此外,波斯纳还认为,阿克曼的“宪法时刻”对法官的要求太多了。
他要求法官具有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以及政治科学家的本事,他要求法官在判案时必须在历史事件的背景下来解释诸多法律文本,这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应该说,阿克曼的宪法时刻建立在对美国宪法理论更为抽象的反思之上,他从历史深处去寻找大法官们进行判决的合理基础。

波斯纳对该理论的批判的着力点就在于其抽象性、没有实证以及个人化上。
以“波斯纳的实用主义法理学”观之,过于抽象的理论:
第一,法官是日常实用主义的。

法官的首要义务是解决纠纷,处理众多疑难主要依靠直觉。
因此,极少会有法官拥有评价宪法理论的天赋,他们处理事实的能力远强于处理理论的能力。
宪法理论对法官来说,太过抽象以致于毫无用处;

第二,宪法时刻遇到的重大难题便是如何认定革命的时刻。
缺乏实证的认证标准必然是不确定的、无法验证的以及个人化的。
恰如波斯纳对道德理论的批判一般,宪法理论的创立与宪法理论家的政治价值也是相关的。

他们或是为保守派代言或是为自由派论证抑或是为司法能动主义辩护。
“理论的思考只是一种外在的装饰个人化”。
总之,流行于美国学术界的抽象宪法理论对于法官来说,是无用的。

作为一个“上诉法院”的法官,波斯纳指责了宪法理论并没有为法官提供有用的知识。
那么何为有用的宪法理论呢?
波斯纳指出,作为学术界更应该关心“利益集团在宪法修改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传媒对最高法院有何影响?布朗案是否带来了黑人教育的改善?”等现实的问题。

而不是继续“这场持续两百年之久的、我们称之为宪法理论的政治修辞游戏”。
作为学术界,应重新安排其研究和教学,“朝着更完全参与社会科学事业(广义理解,并肯定不限于定量研究)的方向努力”,而不是依然执着于规范的分析与研究。
行文至此,我们发现波斯纳批判直接道德推理和间接道德推理,并非完全否定这些学术成果,其所要批判的是这些成果误解了法官的职业特点、并没有为法官带来多少知识。

也就是说,道德理论家提供的理论,对于法官来说是抽象的;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来讲,是无用的。
并且,诸多现实中的问题,例如宪法性权利、司法改革、法官的心理活动皆急需学术知识的生产。
但是,道德理论家对此漠不关心,继续在最高法院决定的数量不多的有关个人权利是否合法的问题上耕耘播种。

对于波斯纳来说,这是法学发展的歧路。
它不仅不利于道德疑难的解决,反而让法学与司法愈加分离。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波斯纳的双重身份:他既是一位优秀的上诉院的法官,又是学术界的风云人物。

这种双重身份也就决定了他的目光始终在法学学术与司法之间的徘徊。
由此,他看到了法官需要的知识与道德理论家提供的知识之间的隔阂,看到了司法与法学的各行其是。
法学与司法的分离,直至新世纪依然是波斯纳关注的主题。

在《法官如何思考》中,他吐槽了法学教授不理解法官,他指出“法官并非法学教授”。
在《各行其是:法学与司法》一书中,他延续了《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一书中对道德理论的批判,认为美国法学学术界仍存在下列问题:
第一,美国法学学者大多数的学术研究只盯着最高法院的判决,但对下级法院不闻不问;

第二,学术研究热衷于宏大的理论,“技术流”的律学专著越来越少,自说自话的“空中楼阁”却比比皆是。
第三,预设结论,不重实证。
宪法理论与意识形态强行嫁接,对法官裁判作出各种不明觉厉、上纲上线的分析,搞各种“花式理论飞行”等。

总之,法学与司法分离的问题一直是波斯纳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法官,他并非简单地批判道德理论的本身,他批判的是道德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脱离,“吐槽”的是道德理论没有为法官提供有用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