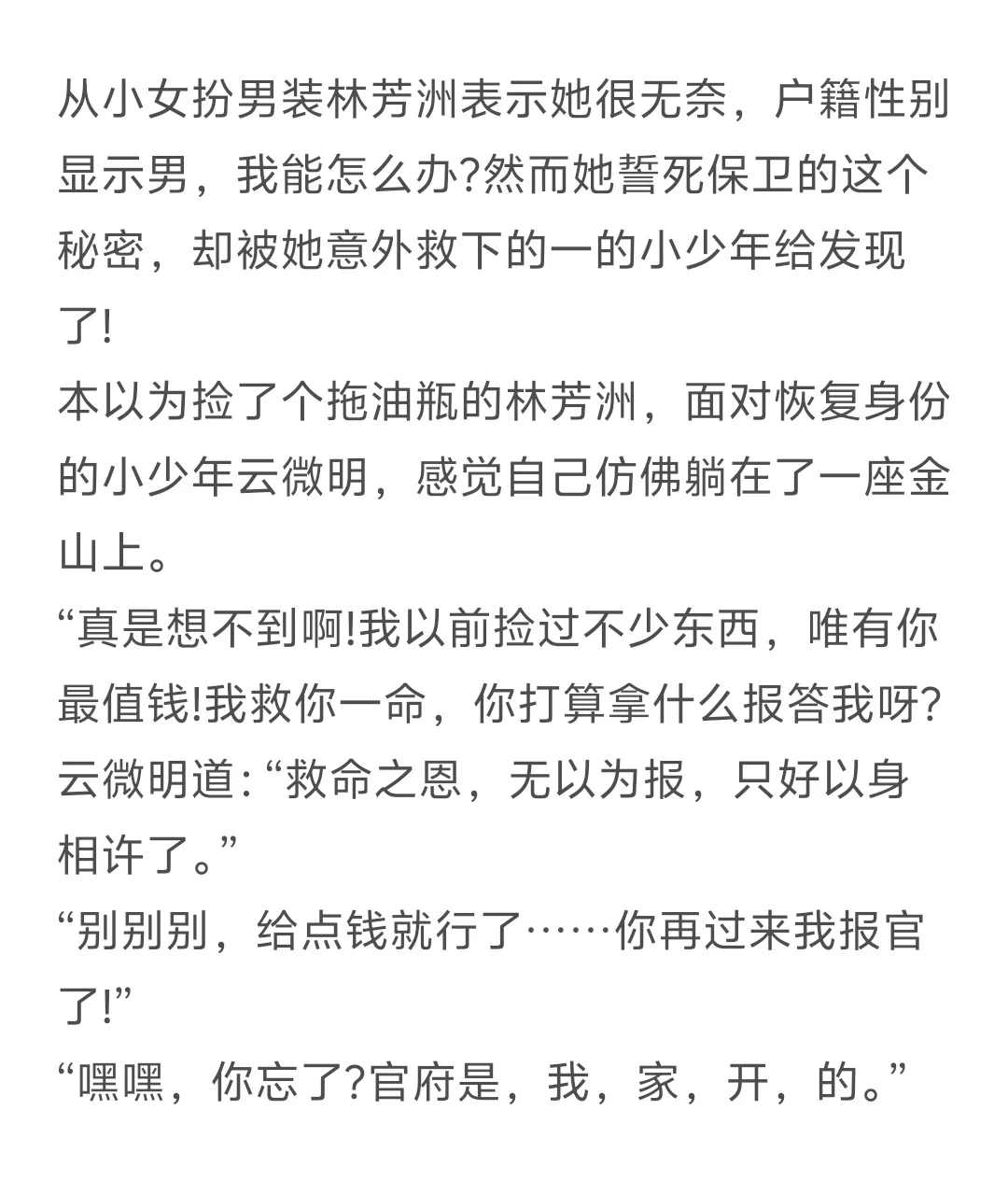甜宠完结:舍不得杀你
他是落难帝王,而我是小镇上贪官污吏之女。
我在深山老林救了他,他却下令要屠我全族。
嗯,屠吧。
我破罐子破摔,指着小腹,“连他也一块儿屠了吧。”
1
我爹是绿水县首富,亦是县令。
除了贪,人倒是挺不错。
“巧儿,今早媒婆又来了,你看看城里有没有喜欢的公子?尽快把事儿办了。”
“我找谁都可以吗?”
“这,”我爹一怔,“那也得人家愿意才行。”
我叹着气应了。
家里共有六个姊妹,我是家里最大的,却是妾生。
姑娘出嫁,总是按年岁来排的。
若我不出嫁,底下的五个妹妹,都得排队等着。
可是稍好点的人家瞧不上我,条件差点的又不愿上门,生怕触了我爹这个县老爷的霉头。
原本这事儿倒也是不急的。
但去岁二妹有了心上人,追了大半年,俩人成了。
听说那公子沾了点皇亲国戚,爹欢喜得紧,直夸二妹伶俐。
为了二妹的婚事,爹成天催我,张罗着要让我给二妹开路。
我心里想着,实在不行,便去小倌馆里赎一个看得顺眼的。
只要是男人,谁都行。
可这会儿脚还没踏进小倌馆呢,一伙官兵呼呼啦啦地冲了进去,火急火燎地贴了封条。
我与侍女青果在门口眼睁睁地瞧着,好半晌都说不出话来。
青果挠头,“小姐,这应该是天意。”
当机立断的,我去街口瞎子先生那里算了一卦。
“姑娘可是为姻缘而忧心?”
他捋着胡须,半掩着嘴巴朝我招招手,神秘兮兮地伸出手指,
“姑娘的姻缘,在北。”
我再问,他却什么也不说了。
青果出主意,“小姐,那咱们就往北走吧。”
2
我们一路爬上北边的山头。
“小姐,我觉得那老头应该是诓你的。”
我和青果站在山顶,望着远处橘红的霞光。
青果揪了两朵紫色的喇叭花,自己头上戴了朵,伸手往我脑袋上比划。
我低下头让她给我戴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罢了,兴许是我命里没有好姻缘。明儿,咱们再去隔壁镇上的小倌馆瞧瞧。”
“咱们就非得去小倌馆吗?”
“那不然呢,去街头强抢民男?”
青果摸着下巴,“我瞧着私塾的郑先生,似乎是心悦小姐的。”
我连忙摆手,“那是好人家公子,我不该祸害他。万一哪天我爹落马,是要阖府抄斩的。”
“小姐,你这样说就不对了。那难道小倌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你说得也有道理,那我不如去找个穷凶极恶之徒,到时候和我一块儿死,还能为民除害呢。”
青果没有回答,于是我摆弄着头上的喇叭花,继续眺望着远方,
“你说,我该去哪找呢?隔壁的隔壁镇上那土匪窝,咱们要不要去看看?青果?”
一块儿石子骨碌碌地滚到我脚边。
“怎了青果,我说得不对吗?”我扭头,“啊——你,你是谁?!”
树边坐了一个男人,像是方从血池里跳出来似的,映着天边的霞光,整个人杀气腾腾。
他一手握着染血的匕首,另只手掐着青果纤细的脖子,黑亮而伶俐的眸子望着我,似狼。
青果哭着扑腾,“小姐别管我了,你快走呀!”
我给了青果一个安慰的眼神,攥紧拳头,小心翼翼地朝他们挪动,
“敢问公子,你为何抓我的婢女?”
“求财的话,我可以给你。我爹是镇上最贪的官儿,这一点你是完全不用担心。”
“还是说,你求色?虽然这么说有些奇怪,但我这婢女啊,要前面没前面,要后面没后面,您不值当啊。”
青果痛哭流涕,“小姐,你这是诽谤!”
笨蛋,我这是在救你!
“呀痛痛痛……”青果一边呼痛,一边高高地扬起脖颈。
我急了,“公子,明人不说暗话,你快说你要什么。”
“她留在这里。你去,找止血的草药。”
“可我不认识草药啊!”
他蛮不讲理,掐着青果的那只手,更是用力了几分。
眼见着青果失去了求饶的气力,我顾不上那么多,赶紧冲上前去掰他的胳膊。
他正要用另只手制住我。
我瞧见他腹部衣物颜色略深,于是眼疾手快往那里来了一拳。
刹那间,我拉起青果旋身就跑。
“呜呜呜小姐,我太感动了。我这一辈子一定为你做牛做马呜呜呜……”
“你这么好,勇敢又善良,呜呜呜要是我是男人,早就爱你爱得无法自拔肯定是要对你以身相许的——”
我停住步子,“你说得有道理。”
“啊?”
我抓着她往回走。
男人仍旧倚着树边,深情恍惚、眼睛半阖,正举着匕首往自己的腿上扎。
听闻响动,他倏地抬眼。
我拉着青果站在他三步远处。
“我问你,你可是落单的土匪?可有婚配?”
他:“……”
青果猜到我要做什么,来回晃我胳膊,
“小姐?!你,你疯了!”
是,随便发发疯。
“你把身上所有武器都丢掉,我愿意救你,也可以给你安排养伤的地方,”
实则紧攥着的手心早就沁出了汗,可我越说越有劲,甚至于蹲下来,佯装轻佻地勾起了他的下巴,
“本小姐只有一个条件,你得跟我成亲。”
3
“娶亲之事,哪像你料想般简单。”
他声音愈加孱弱,捂着腹部伤处,艰难道,
“更何况,我这副模样,你不怕招来祸患嚒?”
我还未言语,青果插话道,
“你左不过是附近流寇罢了。我家小姐可是与山匪称兄道弟的,才不怕你呢!”
倒也……
没那么夸张。
但情境使然,我装模作样地扬起下巴,
“嗯。我再问你一次,愿还是不愿?”
他嘴唇轻轻闭上,下一秒就要说出一个“不”字……
手起手落。
我把他劈晕了过去。
青果劈里啪啦地在边上鼓掌,“小姐威武!”
我拍拍手,蹲下来用帕子把他脸上血迹擦干,隐约能瞧出他清俊的面部轮廓。
青果轻轻地“哇”了一声,赞道:
“小姐好眼光!”
我抚着男人的面颊,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实际上,这个大胆的决定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二妹婚事迫在眉睫,二是算命老头说“姻缘在北”。
三,则是因为……色胆使然。
方才氛围烘托到位,俨然是一副“虎落平阳被我欺”的战损模样。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可是小姐,咱们要怎么把他弄回去啊?这么大一个,难道要咱们一人抓他一只脚脖子,拖回去?”
“那不体面,”我摇头,“当然是背回去。”
青果很自觉,一边撸袖子,一边嘀咕,“唉,那岂不是要累死人了……”
“松手,”我拦她,“谁的相公谁来背。”
青果啧啧,“小姐,你真的超爱他。”
*
正是傍晚时分,百姓下工之际。
弱女子肩驮血人壮汉,尾随行迹可疑的婢女。
奇特的三人组一经出现在街头,便迅速俘获了所有人的视线。
所到之处,或是瞪如铜铃般的双眼,或是惊呼连连。
等到我气喘吁吁地行至家门口,天色已经全然暗了。
还未踏进府里,爹匆匆地从府中迎面而来。
怕吓到他,所以我往后退了退,只露出半侧身子。
“爹,我回来了。”
“欸欸,好。今儿嬷嬷做了八宝鸭,你和姊妹们先吃着,我去一趟衙门。”
他看上去急得很,手里的帽子也没拿稳,被风刮到了地上。
我看着他狼狈地随风追帽子,试探性地问:
“爹,什么事那么急啊?”
“嗐,别提了。好些个百姓报案说,有个疯女人杀了自个儿的丈夫,带着痴傻婢女在游街呢!”
……
青果惊天动地地打了个喷嚏,嘟囔着,“谁?谁在骂我?”
我无语望天。
要我说,造谣的人就该抓起来。
“怎么了巧儿,怎的不进来?”
爹终于拾到了帽子,关切地朝我走来。
“唉!”我大呵一声,“爹,你站在那儿别动,我有话同你说!”
他疾步走来,“巧儿,爹不是说了吗衙门有急事,等我处理完弑夫案,就——”
声音戛然而止。
我那见惯了烧杀抢掠之事的县令爹,站在我面前,哆哆嗦嗦指着我、青果,和我背上的战损男人——我们仨。
半晌,他把官帽丢在地上,憋出一句:
“造孽啊!”
4
青果小心翼翼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同我爹讲了。
他气得整整几日没有搭理我。
不仅如此,还指使五个妹妹孤立我。请她们吃八宝鸭,却什么也不给我留。
青果站在榻边叹气,“小姐,老爷要是一直不答应,那可怎么办呀?咱们还去小倌馆抢别人吗?”
“不去,”我绞了帕子,给躺着的男人擦脸,“就他了。”
“我懂你,小姐。没想到姑爷洗干净之后这么漂亮。”
青果一顿,“但是如果姑爷醒不来,那可怎么办呢?”
凑得近的缘故,我明显地看到男人的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
我抬手摸了摸。
咿呀,又长又翘,俊得很呢!
“应该能醒,”
我笃定地说,“如果醒不来,即便是我站着他躺着,也要成婚。”
青果给我竖起大拇指,“小姐好魄力!”
“少拍马匹!”
我捻着巾帕的一角,小心地擦完男人面颊,把青果赶出了屋子。
因为接下来,我要给他擦身子了。
连续照顾了他四日,喂药擦身讲故事,我是一样也没落下。
他不仅脸长得好,身上也细皮嫩肉的,就连……
不行,这个不当讲。
总之就是这个缘故,我并不觉得自己在照顾病患,而是在扮家家酒。
我哼着小曲,熟练地解他衣裳,擦擦擦。
然后熟练地解他裤带,擦擦擦……
嗯?
亵裤的形状有点不对劲。
我以为是因为位置没穿对,扯了扯他的亵裤边边以作调整。
没想到,形状反倒更奇怪了。
我鬼使神差地抬头瞧他,冷不丁地对上了一双黑亮而蕴满怒意的眸子,“放肆!”
5
像是要将我生吞活剥了似的。
幸亏,他只是醒了,身子却没好利索。
我忙退后两步,他便只能倚着床板冷脸发火。
“你尚在闺阁,怎么都不知羞!”
“山上的事你忘了?我救了你,你就是我的相公。”
“我并未应允。”
“可是我救了你,这是不争的事实。想走可以啊,你再恢复那天的惨状,我原模原样地给你送回山头。”
他嘴唇翕动,抓着床杆的指节微微泛白,“你真是——胆大包天。”
怒意隐而不发,语气凶恶而不粗鄙,看着倒像是个成大事的!
我没忍住摸了一把他的脸蛋,手感颇好,白嫩嫩滑溜溜,像是才剥出来的嫩鸡蛋。
他一双剑眉蹙得愈发紧了,抬手要来捉我。
可他才刚醒来,人正是虚弱着。
我拍掉他的手,闪身道,“欸,抓不着~”
不仅如此,我还推他挺阔的胸膛,把他按回到床榻上,
“相公呐,我知道你着急,但是你先别急。那种事情,还是得留到咱们的洞房花烛夜。”
他眼尾泛红,咬牙切齿道:“放肆!”
我没舍得继续闹他,倒了盏茶水放到榻边台面上,“喝点水,我差人去给你叫大夫。”
青果一直就在门口候着。
听我说醒了,她兴致冲冲地踮脚往屋里看,却忽地缩回脑袋,“姑爷看起来怪凶的嘞。”
她一溜烟就跑个没影。
再回来的时候,身后呼呼啦啦跟来了一大堆人。
三个战战兢兢的大夫,五个好奇张望的妹妹,和一个背着手的爹。
真是好大的阵仗。
大夫轮番把脉,彼此之间小声地交头接耳。
我急坏了,“怎的,可是留了什么后遗症?”
“非也,”
为首的大夫摸着胡须摇头,
“姑娘大可放心。这位公子的身子骨结实得很,平日里定是好生保养着的。”
“那他什么时候可以痊愈?”
“现今公子伤处已无大碍,合理进补即可。”
我满意地点头,“圆房也没问题吗?”
五个妹妹臊红了脸,害羞地往我肩膀上靠。
我把她们移到青果的肩膀上,继续凝视大夫。
大夫支支吾吾地看向我爹。
我爹冷哼一声,甩袖出了屋子。
“这……按道理来讲,是没问题的。但是——”
但是什么但是!
我打断,“青果,送客。”
“得令!”
屋里剩下五个妹妹,她们躲在我身后,用帕子捂着嘴,探头朝榻上望去。
“姐夫不是醒了吗,怎么眼睛还是闭得那嚒紧嘞?”
“这你就不晓得了吧,这天儿啊,马上就要黑了。姐夫这是养精蓄锐呢。”
“哎呀二姐你胡说什么呢,羞煞人了!”
我张开臂膀搂住了她们,一道儿把她们搂出了屋子。
“姐姐我啊,要办正事了,你们自个儿玩去吧。”
其余四个瘪着嘴不情不愿地走了,二妹留了下来。
“阿姐,爹还不同意你与姐夫成亲吗?”
我点头,“爹不同意,兴许是因为那日傍晚情形过于炸裂。不过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不会误了你的婚事。”
却没料到二妹拍拍胸脯,说:“阿姐,我会帮你的!”
6
还真叫她给办成了。
早膳时分,二妹对爹好一通忽悠。
什么夫家算了生辰八字,成亲吉日恰逢年底,若错过便要再等一年。
眼看着爹应下婚期,二妹则柔柔弱弱地说,
“爹,可是阿姐还没嫁出去哩……我这样不合规矩,到了夫家是要看不起我的……”
那小模样,谁看了不心疼?
爹搁下筷子,终于松了口,叫我用晚膳的时候把人领过来。
“他行动不便,晚饭就不来了。”我搓搓手,“直接定婚期吧!”
“你想什么时候?”
“越早越好。”
“这阵子不可。城里洋商横行,我无甚精力料理你的婚事……”
“爹你不用担心,婚事我自个儿料理。就定在月底吧!”
我一股脑说完,不等他开口,就抹嘴儿跑了。
跑跑跑,一头扎进了某个结实的怀抱。
想也不用想,一定是香香软软的家夫。
唔……是香香硬硬。
他捏着我的肩膀将我挪到一边,转头朝外走。
“你干啥去?”
“归家。”
“你家在哪?”
他脚步微顿,“在远方。”
整得还挺神秘。
“我和你一块儿归家。”
“不必,事实上那并非我真正的家。”
他继续朝外走,“你且回吧,冒犯之事便不再向你追究,救命之恩也会择日相报。”
倒是个讲究人。
我张开手臂拦他,“但是我可不搞什么君子协议,我脑筋直,偏要你做夫君。”
“我已有妻妾。”
“骗人!那日山上,你分明就说没有家室!”
“那日才是欺瞒。”
“我不信!”
他不再多言,丝毫也不怜香惜玉地掰我胳膊。
青果在边上忧伤地叹息,“强扭的瓜不甜,祖宗诚不欺我也。”
我突突地跑到门边,拴上木阀,手脚作“大”字状,
“你想出去,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他变戏法似地从腰间某处一柄匕首,迈着平稳的步伐朝我走来。
青果担心地大喊,“小姐快闪开,他来真的!”
这厢纠缠之间,只听闻“轰”的一声巨响。
我与青果早已见怪不怪,而我这没见过什么市面的准夫君,却是动作一愣。
他侧耳听隔壁院子的异动,“什么声?”
“夫君别怕,只是小事情!”
我眼疾手快地抱住他那匕首的那只胳膊,解释道:
“有人来给我爹送礼了。”
“没猜错的话,令尊是县令?”
“嗯嗯!”
他扬着胳膊,而我又抱得紧,只得微微踮着脚姿势怪异地扭身看他。
他问,“那礼,应当会退吧?”
我笑了,“你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他面色稍微和煦了点,“嗯,你莫生气,我只不过——”
我将后半句话补充完整:“送上门的银子,我爹一概来者不拒!”
“……”
“哦,是嚒?”
“是呀是呀!我是拿你当夫婿,所以才告诉你的嗷。你要是敢说出去……”
他垂眸睨我,“如何?”
匕首尚在他手中闪着寒光,我想不出威胁的话来,
思来想去,撅起嘴巴在他脸颊上来了一下,恶狠狠道:
“你要是敢说出去,我就像这样,狠狠地糟蹋你!”
伴着一声不明情绪的哼笑,我腰上一紧,顷刻间双脚离地,被结结实实地按在身后的门板上。
匕首被他随手丢到地上,刀刃与石阶碰撞,迸发出极具侵略性的响声和余韵。
他的指尖微凉,覆着一层薄茧,在我喉间轻轻摩挲。
两分痒,七分热,还有一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悸,我怔怔地对上他的眸,开口欲言。
他却倏地低下头,逼得我一动也不敢动,但凡再说一个字,就要碰上那近在咫尺的唇角。
温热的气息细细密密地喷洒在颈间,我没出息得浑身颤栗,却听得他在耳畔沉声说,
“朕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7
“你……自称什么?!”
朕?
如果我记得没错,普天之下,应当只有一个人可以以此自称……
更后悔的是,被他丢到榻上的时候,我小声问了一句,
“你大病初愈,身子骨是吃得消的吗?”
嗯。
吃得消。
他完全吃得消。
我和床板吃不消。
神智涣散,我还谨记着讨价还价,
“你先前说冒犯既往不咎,还做不做数的?”
“我何时说过?”
我哭,“书上写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书上是否也写了,春宵一刻值千金?”
“哪本书!”
他倾身从枕下摸出一本黄颜色的小册子,“昏迷的那几日,你不是每天都给我念嚒?”
昏迷了也能听见?
想起他昏迷期间我趴在他胸膛上碎碎念的那些话,不自觉地哆嗦,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们?”
8
我晓得我们家迟早是要出事的。
但是我曾想过的死法,不过就是上面下令抄家,该斩首就斩首,一了百了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最怕温水煮青蛙,活不成又死不了。
屋里藏了个大佛,家里谁都不晓得。
我只能眼睁睁地瞧着镇上权贵一个两个的来找我爹“议事”,金银珠宝也一日一日地往家里抬。
而“大佛”本人,伤完完全全好了,却不急着返京。
偶尔在府门口瞧着,甚至还要与来送礼的主管攀谈一二。
他去哪,都要我陪着,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分毫。
某天夜里我借口上茅厕,猫进我爹书房里。
“爹啊,你说得对,我这个未婚的夫君,他——”
爹兴奋地打断我的话,“你这个未婚夫,爹认可了,三两句就能将友商哄得心服口服,来日可期!”
我摇头摇得好似拨浪鼓,“不是的爹,我想说……”
“吱呀”一声,有人推门而入。
“岳父。”
“诶诶,小婿来啦?”
我噤声,恨不得缩进墙缝里。
当今圣上与小地方贪官互称翁婿这种大场面,我这么点狗胆属实是经受不住。
眼瞧着爹喜上眉梢还要与之攀谈,我赶紧拽着陛下大人回了屋。
烛火幽幽,他按着我最脆弱敏感的地方,不咸不淡地说,
“若府上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的身份——”
他指尖微动,我不自觉地蜷起身,“嗯……会,会抄家吗?”
“有这个可能。”
我好不容易喘平气息,不放心地追问,
“抄家是直接斩首的吧?”
“朕会网开一面。”
我双眼放光。
“严刑一百零八招,可供你自行挑选。”
我呜咽,“啊……你,陛下——要杀要剐能不能赶紧的……”
“不可,朕还有些事未曾调查清楚。”
“什么事?”
我好奇地扭头看他。
他挑眉,“你倒是很有闲心。”
我脑中警铃大作。
“不是的,我没有闲心。我很投入,我,唔……”
9
一大清早,他神清气爽地看起了卷宗。
“听说令尊除了县令一职,同时还是生意场上的翘楚?”
我坐在被窝里低头绣花,含糊其辞,
“嗯,他不过认识那么几个商人罢了,我爹那人能有什么本事,他……”
“想好了再说。”
我苦大仇深地搁下针线篮子。
半个时辰后,我领着他来到了镇上最大的米庄。
“还有呢?”
我又领着他来到了布庄、饭庄、医馆、客栈、义庄……
每去一处,他的神色更平静一分。
我却隐约觉得他已经在冲冠之怒的边缘。
他问,“还有呢?”
义庄门口冷风阵阵,我双手交叉搓着胳膊,缩成一团。
“没有了,没有了……”
他说,“人在做,天在看。”
狂风刮过,白纸糊的灯笼在半空呼啦作响。
我顾不得劳什子尊卑有别,蹿了两步抱紧他的胳膊,“我招,我招!”
约莫半刻钟后,我领着他来了小倌馆。
门口小倌与我相熟,热情地朝我俩招招手绢儿,“巧儿姐,你来啦?”
陛下大人扫他一眼,看了看牌匾,旋身凝视我。
我赶忙抓住他的手求他冷静,叭叭地和他解释,
“这个原本不是我爹的产业,是我盘的店。遇见你那天我是要来小倌馆挑一个人回去做相公的,没想到当天贴了封条。”
“后来走街上发现里面的大家伙儿都无处可去,恰好我与他们都有些私情——我是说私下有点交情——所以出钱资助店铺又开起来……”
街口算命的半瞎捋着胡须,笑眯眯插话道,“姑娘这是,找着了姻缘,来回访了?”
回访什么回访,躲都来不及!
路边窜出三两流民抱住我的腿,另一只手攥着缺了口的破瓷碗,讨要银钱。
我说,“我没有钱。”
陛下凝视着我,相顾无言。
回到府中,青果从二妹屋跑里出来迎我。
而我身不由己,被攥着手腕朝自个儿小院的方向走,
青果大吼,“喂,你一个小小流寇怎么敢这么对我们家小姐的?!”
笨蛋果子,捋虎须还是你在行!
我来不及思索,狠狠地凶她:“闭嘴!”
“小姐,我在帮你……”
“不要你管!”
青果神色落寞,嘬了嘬手指的油色,旋身回了二妹院里。
不用猜,她们指定又在聚众吃鸭了。
而倒霉的我不仅吃不上八宝鸭,还要被迫承受一波疾风劲雨。
我心里苦。
门“砰”一关上,我颇有自知之明,膝盖一弯跪在他跟前,
“求求你陛下,我爹虽然是个贪官,但他……其实贪得并不多。”
“衣食住行都涵盖了,生老病死一条龙服务——贪得不多?”
我被噎得说不出话,左右想不出别的什么讨饶法,咣咣地给他磕头。
他没扶我也没喊停。
我原本只是想表诚意装可怜,磕着磕着和自己怄了气,越磕越重。
爹为什么贪。
我想,我大约是知道的。
我曾屡屡劝过他,也不顾孝悌地骂过他。
直到一天深夜,他那张总以笑意迎人的油滑面具,终于在我面前碎裂瓦解。
他说我娘死于饥荒。
他还说,做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额头愈发钝痛。
我心想,倒不如磕死在这里算了。
忽地额间一软,一只靴子横在我面前。
“你以为装可怜有用嚒?”
“起来。”
再往他靴子上磕,便多少有些不识好歹了。毕竟天子的喜怒,哪是寻常人能看破的。
但我也没起身,仍跪着,垂下头不说话。
好半晌,他屈指整理我额间发,叹气道,“地板冷硬,要跪去榻上跪。”
我点头起身,自觉地头朝里,跪趴到榻上。
脚步声逼近,忽从身侧探出一只手来把我拽起来,随即那手又探向我胸前的斜襟……
我挺起身子迎合。
他抵住我的肩膀,低叱道:“你真当我是昏君嚒?”
手从我胸前略过,抽出了我掖在我斜襟的帕子,在我面颊上擦拭,“你哭什么?我又没凶你。”
这还没凶吗?
从街头到里屋,手腕子都被他攥得发紫了。
“莫哭了。”
抽泣难以止住,我频频抬手擦眼泪。
他攥住我的腕子把帕子塞给我,沉声道:“再哭,朕即刻下旨——”
“行啊,抄家吧。我们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还有他,”
我指着肚子,“全都死了算了!”
那道灼热的目光投射到我的肚子上。
至此,我才颇觉得自己有些冲动,小声嗫嚅道:
“还没看过大夫,就是胃口不好,总是要呕……”
他扶我躺平,抬手搭我的脉,随后沉吟道:
“嗯,是有了。”
10
没想到几日后,他不告而别。
我映着烛光绣花,青果在边上给我理线。
穿来绕去,硬是叫她理成了死结。
“小姐别等了,兴许他永远不会再来了。”
哼,不来才好呢。
好似离了谁不能活似的。
只不过阖府上下心里都明白我被弃了,总要逗我开心,见缝插针地劝我。
二妹送来八宝鸭,见我正在绣的物件,骇了一大跳。
寻常百姓绣龙纹,当斩。
她冲过来抱紧我,“阿姐,你莫不是生了癔症?呜呜呜……是我不对,我骗了你。”
“我未婚夫那里,压根没有长姐必须出嫁的规矩,全是我和爹胡乱杜撰的,想叫你自个儿去寻个好相公……”
“爹原想着催你一段时日,若你寻不来人或是寻来的人十分离谱,爹就会同你讲实话……”
“姐夫刚被你驮进府的那会儿,爹是坚决否定想拆散你们的。但相处了两月有余,大家伙都晓得你对他动了真情。谁晓得他——”
我恍然大悟。
怪不得爹那样一个随心所欲的小老头儿,会一天到头地催着我寻夫婿。
可心底却没有什么怒意。
我摸摸二妹的脑袋,说:“不怪你。这两个月,阿姐很开心。”
这是大实话。
二妹的婚礼如期而至。
她出嫁那日,原本连续多日的阴雨辄止,天空放晴。
我爹高调极了,办了半条街的流水席,走过路过的街坊邻居都能扒两口好饭好菜。
二妹的花轿叮铃叮铃地消失在街口,爹老泪纵横地攥紧我的手,举目眺望。
许是情绪使然,他醉倒在无人的席间,见了我,念念叨叨地说了好多话。
“你娘出嫁的时候,也是这般年纪……
“那天,是我亲手抬的花轿。”
“什么?”
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可爹用袖口胡乱抹着眼泪,“我与你娘从小一起长大,彼此钟情——说好了长大了要结为夫妇,可长大后她却反悔了。”
“家里长辈望我出人头地,变卖家产供我科考。
“我用娘家哥哥的身份送她出嫁后,背上行囊背井离乡,待考中举人再回来,一切都天翻地覆……”
“巧儿,你晓得人只剩皮包骨是什么模样吗?身子压根就撑不起衣裳,脊背佝偻着,一边走路,衣裳一边往下滑。”
“走时俏生生的文静小姐,竟趴在污秽的舍后,舔食巨石上结的盐粒……至于边上襁褓里的孩儿,就那么不管不顾地任其吃着臭泥巴……”
忽地,他话锋一转,仰天长叹:“爹——也不想贪哪!!”
我赶忙寻了个窝头往他嘴里塞。
他叼着窝头,头仰着未动,晶莹的泪水从眼角滑落,浸润了泛白的衣领。
我随他的目光,一同落寞地仰望夜空。
我爹这人啊,
唉……
11
二妹才出嫁没几日,爹出事了。
城门无故堆积无数灾民,经问询得知,人是打东边儿来的。
可是东边是富庶的州郡,且局势安稳,如何会有那么多灾民?
年纪稍长的老人咳出了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
边上妇人从破烂的裙摆上又撕下一块,匆忙地为老人拭手。
她愤愤道,“州郡缘何富庶?还不都取自于我们庄稼人!!”
爹为他们提供了吃食与住所。
可没过几日,大批难民纷纷口吐白沫当场气绝。
爹怒极,下令彻查。
可此案尚未查清,巡抚造访,言及有民众举报绿水县县令伙同山上土匪贩卖私盐。
早膳途中,忽然一伙官兵闯入,阖府上下皆被羁押在堂前。
四个妹妹吓得如鹌鹑般蜷缩在我身侧,倒是青果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入狱后,深夜里。
我小声问爹,“你真的贩私盐了?”
爹叹息,“嗯,贩了。”
我也随他叹气,“为什么啊……”
“莫问了,”他阖上双目,“爹只想做个无名英雄。说太多,显得怪矫情的。”
我似懂非懂,想起那批涌入的难民,又试探地问,
“那,这些事情能不能上书朝廷?”
爹哼笑,“你怎知我未上书朝廷?那封举报信,便是你爹我,亲手写的。”
“什么?!”我没忍住提高音量。
熟睡的青果呼噜声骤止。
霎时间寂静无声,只见爹瞟我一眼,颇为自得地说:
“举报信,是女婿让写的。”
啊?!
我不自觉地抠着手指,“哪个女婿?”
爹仰躺在枯草堆上,颇有闲情逸致地反问我,
“你希望是哪个?”
还不待我答话,他又自言自语地说,
“噫——我真是老糊涂了,只有二闺女嫁出去了,我只有一个女婿呀!”
我便晓得了他在戏弄我。
“爹,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好让我晓得此番还有没有命可以活,”
我捶了捶酸痛的腰背,对他说,
“若是……若是我那个跑了的夫君指使你这样做的,那咱们兴许还能见到明日的太阳。”
总不是故意让我爹送死的吧?
他应该晓得,若我爹倒了,我与腹中子也是没命好活的。
爹戏谑地看着我,“呦,这么相信你夫君的实力?”
怀疑人品也便罢了……怀疑实力?
我蹙眉,“爹,你是不是,不晓得他是谁?”
“知道啊,闺女,”
爹抱起手臂,手铐叮铃作响,“爹想不到你这么厉害,连郡王都能拐回——”
外头廊里响起一道急促的嗓音,是白日里的那个巡抚。
“欸,欸——陛下走慢些,当心地上湿滑!”
“朕难道没有同你说优待女眷嚒!”
“陛下,那样不合规矩……”
“呵,规矩是谁定的?”
“微臣该死!”
锁钥入孔,我翻身朝里侧卧。
噗通一声响,我爹从榻上掉了下去。
“额,小婿——王爷——额,陛下!!”
我仍然面朝里侧卧着,闭上眼睛。
有人拍我的肩膀,沉声道:“朕来了。”
哦,欢迎你啊。
青果和我连着心似的,呼噜犹如雷声轰鸣。
他又扳我胳膊,我不声不响地与使了劲,硬是不动如山。
他终于觉出几分不对来。
“埋怨朕?”
哪敢呀。
我心里正腹诽着,忽觉整个身体腾空,忍不住惊呼一声,抬眼撞进一双黑亮的眸子。
一如当日山上初见时那般的侵略性,除此之外,似乎多了些旁的情愫。
他抱着我,朝着县令府走去。
从我的视角来看,月色正巧在他发冠边上打转儿。
我环着他的脖颈,心里颇有些拧巴,闷声说,“肚里的孩子很想你。”
他垂眸看着我,“你呢?”
我扬起头在他脸颊啄了一口,扭捏道:“也就那样吧。”
他开口欲言,被我不由分说地堵住了唇舌。
他低声笑骂,”放肆!“
我胆大包天,轻轻拍他的面颊,”装什么装?你不喜欢吗?“
他不言。
身子却愈发的热了。
我额头抵在他温热的胸膛上,听着他的心跳,也听着自己的。
除此以外,万籁俱寂。
——
后记
1
他接我回宫了。
宫中,真如他所说的“已有妻妾”。
不多,仅一妻一妾——一个皇后,一个贵妃。
但她们整天手挽着手黏在一起,对我好得过分。
我不安心,夜里偷摸地告状,“她俩不会是结了盟,想要偷偷地弄死我吧?”
他脱衣上榻,“放宽心,她们无意争宠。”
直到我抱着肚子在后花园溜达,不慎在假山后头看到她们互诉衷肠,
脚一滑,跌倒了。
孩子生了,是龙凤胎。
据太医说,是因为孕期忧思过度,才导致的一胎双生。
虽然太医以性命担保,孩子生下来是健康的。
但我心里总免不了想东想西。
“都怪你!”
某天,我终于忍不住把下朝回来的某人挡在殿门口。
“孕期忧思过度——还不是因为你威胁我说要抄家,我咣咣给你磕头你都不肯松口!”
“后来你不告而别,我真拿不住主意以为你要把我们娘俩丢了,不,是娘仨!”
他原本还在诚恳地道歉,直至听见最后一句话,
“不告而别?朕分明——”
他蹙眉,看向我身后,我也随他扭头看。
只见,青果呈半蹲状,正缘着墙根小心翼翼地往远处踱着……
2
也不晓得他与我爹谋划了什么,总归最后处死的并不是我爹,而是当地都郡的藩王。
“那藩王……不是你的外姓表兄弟吗?”
“是,他比你爹贪得可多多了。还有我那日山上重伤,便出自其手。”
“那我爹配合你除去异己,你能不能……”
虽说有苦衷与难言之隐,但贩私盐、收礼金,这些事都是切实存在的。
每一桩每一条,都是杀头的大罪。
他还是手下留情了。
杂草丛生的旷野中多了一座小房子。
我爹领着四个妹妹,过起了采菊东篱的好日子。
——全文完——
热门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