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个小故事,“我”指代很多人,大家当杜撰的听。
几年前,我外公患病去世,遗产大半留给了我舅。
他走之前,把屎把尿的是我妈,出钱跑医院的是我姨。
我舅也不是什么都没做,他会偶尔接送一下,也是葬礼上哭得最大声那个。
我妈说,遗产的事儿,外公走前和她谈过,那是他们姐妹俩同爸爸共同的决定。
理由也很简单,我舅是几姊妹最缺钱的那一个,而我妈和我姨都说她们不介意。
丧礼过后,在回家的高铁上,我妈望着窗外一路沉思,直到进入一条隧道,她突然小声说了句:
“如果是妈后走呢?”
然后就没然后了。
外婆自然给不了答案,于是这段故事就在隧道里无风无浪地结束了。
又聊起,是因为前些天,我在银幕上看到了它完完整整的复刻版:
《姥姥的外孙》。

说完整复刻也不太准确,因为片中走在后面,掌握了遗产分配权的,确实是“妈”,也就是影片名字里的姥姥。
但除却这些小细节外,说它是一部中式家庭的纪录片也不为过。
一个背景小科普:这一家是泰国极其常见的潮汕移民,而潮汕又是南方这边儒家文化、传统道德比较根深蒂固的地区,这个故事因此有了一种超越地域、国界的普适性,大概整个东亚都不难get到这种家庭伦理。

剧情极好概括:老人患病,儿孙尽孝,爱与钱一起计较,先是各怀鬼胎,最后又真切哭坟。
影院里,所有人都在照镜子,在细细密密的共鸣处哭得肝疼。
然后猝不及防地,它回答了我妈的问题。

想说的很多,不如从全片第一个哭点聊起吧:
姥姥的鞋。
姥姥的鞋不合脚,孙子阿安很早就发现了。
但老人家固执,硬说合适,阿安也只能作罢。

转折发生在捐棺材(一种为没有棺椁的逝者捐钱,借此为自己积德的仪式)的那场戏。
彼时,怀着分遗产的心思前来照顾姥姥的外孙阿安,已在与老人家的朝夕相处产生了真正感情,但事业有成的大儿子阿强仍在打着阿安开头的算盘。
表面功夫很多,买设备,接老人,只是全然不去看姥姥为难的表情,一味用表孝心去堵老人欲说还休的嘴。
带着老人去捐棺材祈福,刻意派女儿去问询姥姥“开不开心”,但神佛面前露真心,自己许的愿有妻有女有事业,独和老人无关。

在寺庙门口的换鞋处,姥姥开始陷入回忆,对孙子阿安说,很多年前,也是这样好的阳光,她带着大儿子来这里祈福,……(具体说了啥我忘了家人们)
总而言之,是老人常有的那种对自己还年轻、孩子还单纯的旧日时光的咂摸回味。
阿安看着姥姥被鞋勒红的脚,说:
“这双鞋是阿强舅舅送的吧。”
老人家点头。
阿安不忿,于是在姥姥那一大串“希望家人如何如何好”的许愿纸后面,狠狠贴上一张“希望姥姥中彩票”。

回家的路上,姥姥对阿安说,我脚疼,给我换双鞋吧。
这,就是她对儿子化身秃鹫一事,所有所有失望的唯一表达。
很东亚,很中国。
当虚伪被赤裸摆出,你分明在她的沉默里看见了巨大的坍塌,却永远寂寥无声。
哭,因为永远会被老一辈中式女性的忍痛能力震撼,又悲戚于这个能力,往往只使用在“儿子不孝”一事上。
或更准确地说,是对男性晚辈的“无心”上。
剧情走下去,类似情节,小儿子一次,孙子一次。

本以为孙子会成为她最后的稻草,但事实是,当她发现全职乖孙的企图,做的,也不过是翻出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嘱咐他去找个好工作,不必每日围着自己打转。
大儿子的冷漠,小儿子的混帐,孙子的幼稚,姥姥看在眼里,然后照单全收,仿佛这是什么无力辩驳的自然规律。
大约因为她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父母辈的重男轻女,让姥姥和她哥哥的生活天差地别。
病情恶化后,姥姥前去向哥哥借一笔买墓钱,却被逐出那栋庄园一样的大别墅。

哥哥让妹妹别再来找他了,因为父母当年已经选择把钱给了他。
姥姥争取:“但当初照顾他们的都是我,你什么也没做。”
哥哥却理直气壮,说钱给了妹妹,也不过是被混账妹夫挥霍一空。
姥姥悲愤又无力:“我那混账老公,还不是爸妈找的吗?”
接受了的,无法改变。
当年她无力争,如今她不配争。
这一生,姥姥从未见过有心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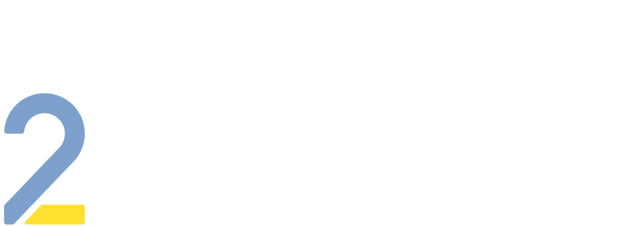
女儿阿秀,是唯一真心的。
她戏份不多,像所有中式家庭一样,大儿子负责出息,小儿子负责表面孝顺,而女儿负责“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切实在活儿。
片子开头,姥姥摔倒,众人急忙将老人家送医,但很快又作鸟兽散,阿秀被兄弟们拙劣的逃跑借口逼得火气上窜,站出来说自己愿意留下照顾。
这时候,同行的儿子阿安也背叛她了:“舅舅能顺道把我送到地铁站吗?”
这就是女人的命运。

在儿孙们试图以表孝心换些什么的时候,唯阿秀默默将工作调了晚班,空出时间陪老人运动。
阿安小人之心,问妈妈是不是也想得到什么,阿秀说:
“我只是想她了。”

逻辑告诉观众最后分得遗产的应该是她,可东亚人的基因悄声说着未必。
果然,代际循环。
像不给自己留一分钱的父母一样,姥姥为赌鬼儿子留下房子,为孙子也存下百万,轮到阿秀,却只有一句:“我最想你陪在我身边。”
对此,阿秀的回复是:“有什么所谓,付出比得到更安心。”

愤怒也罢,不平也罢,总之开头那个小故事,已经有了答案。
后走的是妈,结果也未必不同。
只是,为什么?
我知道那个问题的执念,是觉得父亲偏心能为自己传宗接代的儿子尚且天经地义,于是希冀母亲能有所不同。
毕竟同是受害者,都是被蚕食的,何苦护着他们,辜负真心也辜负自己。
但为什么,事实好像总不遂人愿,活到最后也并不会笑到最后?
影片用姥姥出院那场戏,回答了这个问题。
前置情节,是姥姥因病情加重而入院治疗,已是到了安排身后事的时刻。
而彼时的阿安已彻底对姥姥投入真情,守在病房门口没有离去。
于是他亲眼看到了妈妈将姥姥的房本给了赌鬼小舅,曾见过姥姥是如何不堪其扰的阿安正想急着替姥姥护住房子,下一秒就被告知这是姥姥自己的选择。

陪姥姥办理出院手续时,阿安按捺不住委屈与不解,质问姥姥:
“我在你心里,到底排第几?”
轮椅里的姥姥沉默很久,身子开始颤抖,第一次有了真正外显的悲伤,她落泪,然后回答:
“对不起,我没有更多东西可以给你了。”
很卑微,很凄怆,很错位。
此刻的阿安在意的早不是姥姥的房子与遗物,曾经想排第一是为了财产,现在是想以财产证明自己排第一。
他要问的,不是姥姥的钱在何处,而是姥姥的爱在何处。

可姥姥显然已不具备理解这种关于“真心”的提问的能力了。
她听在耳里的,只剩“为何我没得到房产”,所以给出的答案,是“抱歉,我没剩了。”
她已然接受了自己在这个家庭中作为“燃料”的定位,不敢去想有人还在意她的爱,因此在生命尽头,也只是惯性地紧着最缺柴火的地方烧。
曾经大儿子体弱,她便向神佛起誓一生不吃牛肉去点燃大儿子的健康,如今小儿子躲债,她又以所有身家去补上小儿子的窟窿。

而女儿呢?
人人都说这会寒了女儿的心,可“心”是什么?心也需要柴火吗?
且,女儿如何还要我去烧,我们女人生下来,不都是柴火吗?
姥姥再不能理解。
儿子是抚养的对象,疼爱的对象,是要助他上青云的对象,而女儿,是留下来一起共担命运的人,这都不是偏心于谁的问题,而是在父权逻辑里,她们甚至没资格参与爱的分配。

所以他们继承遗产,她们继承癌症。
拎不清的从来不是姥姥,因为她没有理解错,因为阿安最开始在意“我排第几”,正是想问“能分多少”。
怎么?被算计了一辈子,临死了突然开始谈真心了?


到此,这漫长的答案还没结束。
最讽刺的部分,其实在影片的最开头:
姥姥的故事,开始于阿安的爷爷。
因为看到悉心照顾爷爷的堂姐最终分得万贯家财,由此才引发了阿安想效仿的邪念。

相较临了都在顾着自己粥摊,为外孙存钱到死前一刻的姥姥,爷爷的人生尽头,是看着电视中的靓模度过的。
但他的确成为了那个完成“公平分配爱与钱”的人。
随心所欲,不问身份,只图开心,谁将他伺候得好,谁在床前付出的多,便把财产留给了谁。
爷爷是活明白了,不为那些迂腐观念拘泥,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他没做错什么,只是两厢对比,这份轻而易举的通透有些过分刺眼。
离经叛道,是上位者的特权,因为他们左转右转,都能得益。
而撕伞,是淋雨者的宿命,因为顾前顾后,都是万丈深渊。
姥姥成为了自己的妈妈,而女儿也不待见哥哥的媳妇。
轮回一直在继续,直到阿安成为了那一个变数。

与姥姥朝夕相处的日子,让他足以洞见了埋在姥姥一脸平静之下的欲望。
思维上的爱无能,抑制不了心里本能的爱渴望。
所以姥姥会在周末聚餐前认真打扮,会将不合脚的鞋一穿数年,会为孙子留下出生那年种下的石榴,会对换班的女儿说:“你不睡觉就不要再来了。”

她被病痛折磨时也哭喊“妈妈”。
她拥抱哥哥时也满眼深情。
她不谈亲情,只埋怨自己最憎春节全家团年饭的次日,冰箱里全是菜,“我一个人怎么吃得完”。

于是阿安假戏变真做,实在心疼起了姥姥。
当得知小舅将姥姥房子卖去还债,又送姥姥进养老院后,他去养老院接回姥姥,不再计较“自己在姥姥心里排第几”,只知道“姥姥在我心里排第一”。
他也终于明白,母亲所说的“付出比得到更安心”不是潇洒地扮圣母,而是心中有情,你便无法不付出。

情本无错,利用情者才有错。
情可以无需回报,但不应当替他人做老婆本。
这才是安妈,我妈,我表妹妈,以及天底下所有做女儿的,真正的“介怀”。
女儿们的痛苦,是明明自母亲处感受到了一种道不明的联结,应该是爱,却找不到证据。
或悲哀,又或幸运的是,阿安找到了。
孙子的身份加上与姥姥的相处,让他成为了唯一一个,既对姥姥有心,又分得了财产的人。
也就是家中唯一一个,付出了爱,并得到准确的爱回音的人。

所以影片最后,阿安用姥姥为自己存下的100万,为姥姥买了她心心念念的独栋豪华大墓。
悲哀,因为这种循环似乎只能由一个“孙子”去打破。
幸运,又因当阿安放下了蚕食者的角色,选择将姥姥的归还姥姥,成为一个有心人之时,性别的界限便已模糊,变得不再重要。
只是,这种爱战胜利益的时刻,在生理天然优势下能坚持多久,无人知晓。
诚如上述,阿安左走,是百万家产,右走,是世纪孝子。
这个选择于他,没有那么难,却也是电影能给出的最大温暖。
至于真正属于阿秀们的温暖。
只能由阿秀们去完成。

有淡淡的忧伤,又有心不甘情不愿的~被裹挟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