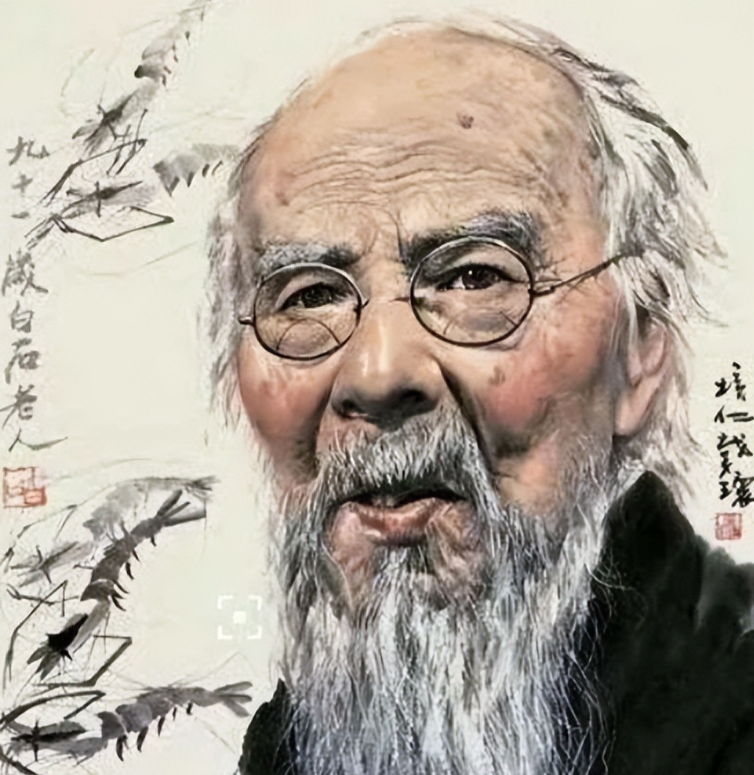河南作家|何少波:闲文三章
别人的妻子好温柔
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男人,却总是希望此生能碰上一位好妻子;明知道自己的脾气暴躁不堪,喜怒哀乐无常,却总是希望自己的妻子要温柔。这也许是天下男人不算通病的通病吧?每当我推门进家,迎头一句:“干啥去啦,怎么回来这么晚?这个家你到底还要不要?……”之类的语气极不友好,声调极不引人的斥责时,心里头总有一种淡流的哀愁和无言的慨叹:怎么别人的妻子,悠地温柔呢?……
有时候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望着妻子,望着望着就发起愣来。眼前的妻子像换了一副新面孔,陌生起来了。她的一容一貌,一举一动,仿佛很遥远,仿佛与自己毫无瓜葛,又仿佛是一个冷漠的跳动的幽灵。结婚多年了,仍然不习惯她把灯泡突然拉灭,突然把擀面杖敲得叮当响,突然把茶杯向桌上一磕,突然把正在看的书摔在地板上……我难以想象出我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也难以想象出是什么缘故使妻子竟然变成了这么一副模样。时间长了,进而又怀疑自己是否真正爱过她;在热恋的时候,何以在一瞬之间千百万个妙龄女子会化做她一个面孔,自己的一腔热血又何以为她那么深深地凝滞过?……难道婚姻确如人们所说的,是爱情的坟墓?每当我看见蒙着灰尘的家具,堆放杂乱的厨房,扔满脏衣服的床,叠得无棱无角的被,时常清扫却时常脏乱的屋子……心里头就会升起一阵莫名的烦恼和失望:这就是我的家?我的视线掠过妻子蓬松的头发,惺忪的眼睛,没有表情的面孔,浸着汗渍和奶迹的上衣,趿拉着踢踢沓沓的拖鞋……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昔日热恋的女友,今日亲爱的妻子啊。
别人的妻子会是这样么?就说穿着,她们平日里也很随便,但又是那么整洁那么得体,让你看了,不由得让你觉得她们的骨子里有着一种淡淡的风韵和自然的潇洒,更不用说在夜总会上那刻意的妆扮了。你愿意和她们在一起,因为她们自然而然地让你想到,她们是美的化身。她们挣钱也许不会太多,家中也不一定太富有,但她们仿佛又都很知足,脸上时不时绽出的是可人的微笑。她们与你打招呼,与你聊天,与你戏谑,声音总是那么悦耳,语调总是那么柔婉,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心里总是有一种亲切与和谐的感觉。你愿意和她们倾诉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苦恼,你的烦忧,而她们也总是耐心地听着,由衷地叹息着,仿佛她就是你的知己。你在沙发上喝着茶,她在床边打着毛衣。你的茶水完了,她就像心有灵犀似的悄然而至,为你倒上热乎乎的一杯。她似乎不在又好像无处不在。这时你心里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啊。到吃饭的时候了,她走进厨房,只是一会儿的功夫,摆在你面前的却是好几样可口的饭菜和美味的汤羹。你能说什么呢?虽是家常,但咽到肚里,谁不感到是无上的享受呢?
当她们与她们的丈夫坐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她们偶尔相遇的眸光里有着一种不能言传的情投;当她们与她们的丈夫在街头漫步的时候,那亲热甜蜜的样于,简直让你觉得他们之间一点也不存在什么误会和隔阂;当她们向你谈起她们的丈夫的时候,你会强烈地感到她们的自豪以及她们与他们之间的那根看不见的红线线……她有发脾气的时候,但她的样子让你觉得心痛;她有撒娇的时候,但她的样子让你倍觉可爱。她时时让你觉得她是你的,然而她又时时保持着她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她可能为你流过泪,也可能为你伤过心,发过愁。但她从来没有恨过你,没有怪过你,仍是一如既往地爱着你。她把你看做是她白天的太阳,夜晚里的月光,沙漠里的骆驼,大海里的舵手。她疼爱你,如同疼爱她自己的生命;她珍惜你,如同珍惜她自己青春的容颜。你怎能不爱她呢?
每一个男人,都愿意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每一个男人的心里,家,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当他疲乏的时候,在这里他得以休憩;当他狂燥的时候,在这里他得以冷静;当他寂寞的时候,在这里他得以欢乐;当他受挫的时候,在这里他得以恢复勇气。这一点,是不是每个女人都能理解呢?
啊,别人的妻子,恁地温柔……
月光曲
妻子醒过来了。在黑暗中她凝视了我好一会儿,转过身就要开灯。那一霎我失声喊:“别开灯!”
像怕被别人窥破什么秘密似的。
也似乎忘记了妻子还在病中似的。
妻子伸出去的手又缩回来了。即就是在病中,她还是那样地依顺着我。
“为什么不开灯呢,屋里这么暗……”她轻轻地说。
我道歉地笑了一下:“没有吓着你吧。”
妻摇了摇头。
“感觉怎么样?”
“有力气多了。”她温柔地笑了。
在床前和妻子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好久。
估计差不多了,我便起身,以最快的速度拉开了小屋子所有的窗帘。
望着霎时便弥满了洁白的月光的小屋子。她明白过来了,惊喜地喊:“今天是十五么?好迷人的月光啊……”
我欣慰地看着妻子。熬了好几个钟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应该到院子里去……”妻说。
于是我扶着妻子走出屋子。在庭院的葡萄架下坐定。
妻子的兴致很高,就背诵了几首关于月光的诗。妻在大学学中文,古文的底子蛮好的。
我也和着妻子的声调,胡乱地吹奏了几曲箫。在这静静的秋夜里,似乎唯有萧的声音才显得古远,神秘,令人神往。
“柜子里还有酒么?”妻子忽然问。
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便从柜子里取出了一瓶葡萄酒。幸亏还有两碟小菜,也就一并端了过来。
取来三只杯子,慢慢地斟了。一杯给妻,一杯给我,另一个杯子在妻子诧异的目光里斟满了,对着月光虔诚地一倾。
“你不会说我坏吧,”我逗着妻,“你和月光,都是我难以割舍的爱……”
妻无声地笑了:“我何尝不是呢?”好像是要显示自己并不比我差,她接着说,“把那个空杯子给我。我要用月光用过的杯子……”
……
……
夜已经很深了,而月光还在小屋庭院里温存地荡漾着。妻在我怀里已经睡着了,微微地打着鼾息。我一会儿望望月光,一会儿又低下头看看妻子,一种从来没有的甜蜜的感觉油然涌向心头——如果能像这样,相依相偎直到永恒,那该是前世修来的多大的福分啊……我这样想着,也这样祈祷着,直到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昏睡了过去。
对面山头上的那盏灯
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父亲坐在窗前聊天。父亲望着对面山头上的那盏灯若有所思。
他问我:“你看见那盏灯了吗?”
我答:“看见了。它忽明忽暗,忽近忽远。”
父亲说:“那是风的缘故。”
我点点头。
“其实,”父亲抬起头,在黑暗中望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风中的一盏灯。”
又一个晚上。父亲和我又坐在窗前看对面山头上的那盏灯。那时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不断地喘着气,咳嗽着。
父亲问:“你能猜得透那盏灯的心情吗?”
我想了想,说:“总的来说,那盏灯的心情可能极不好受。它可能焦虑,而且在焦虑中恐怕还蕴藏着无奈。那全是风的缘故:随时一阵风都可能将它一下子吹灭,可它阻挡不了风的存在。”
父亲咳嗽着,艰难地听完了我的话。好久,父亲才停止了咳嗽,说:“可你——可你听见了它在歌唱了吗?”
我迷惑了:灯会唱歌么?它会唱什么歌?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听不见。”
父亲恼怒了,用手狠狠地拍着桌子,“你怎么听不见?你怎么这样没有灵性?他现在不是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唱着一首光明的歌儿,一首奉献的歌儿么?”
我呆了。
今夜,是我一个人独自地依偎在窗前,默默地望着对面山头的那盏灯。其实那盏灯早已经没有了;而父亲,也在半年前就去世了。
过了一会儿,母亲忙完了手中的活儿,走了过来,坐在了父亲曾经坐过的椅子上。
我流着泪说:“母亲,对面山头上的那盏灯已经没有了。”
母亲也流出泪来了,但她用手抹了抹,露出了笑容:“儿呀,可你和妈这两盏灯,不是还闪亮着吗?”
我哽咽着,一下子扑到了母亲的怀里。
我忘不了对面山头上那盏曾经闪亮的灯;也时时记着提醒自己,在风将我这盏灯吹灭之前,我要尽力唱好我自己的这首人生的歌。
作者简介:
何少波,男,1968年生,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某通信企业员工。作品主要见于《人民邮电》《河南通信报》等专业报刊。著有《夜歌》《足迹》《凡心偶动》《蓬累而行》《渐行渐远》《曳尾涂中》等散文、诗歌、新闻。
微刊投稿邮箱:1505105907@qq.com
◆总编:刘云宏
热门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