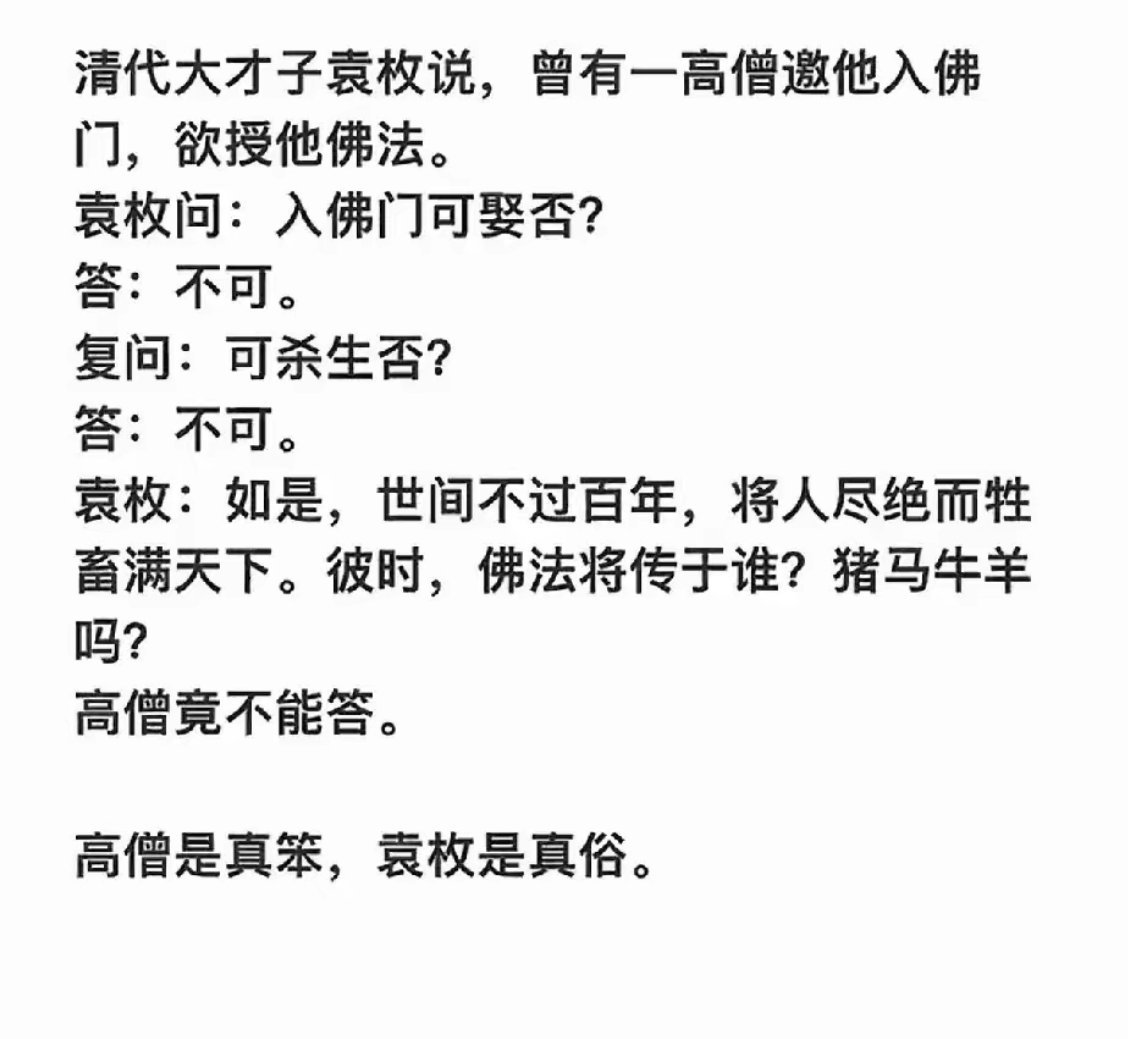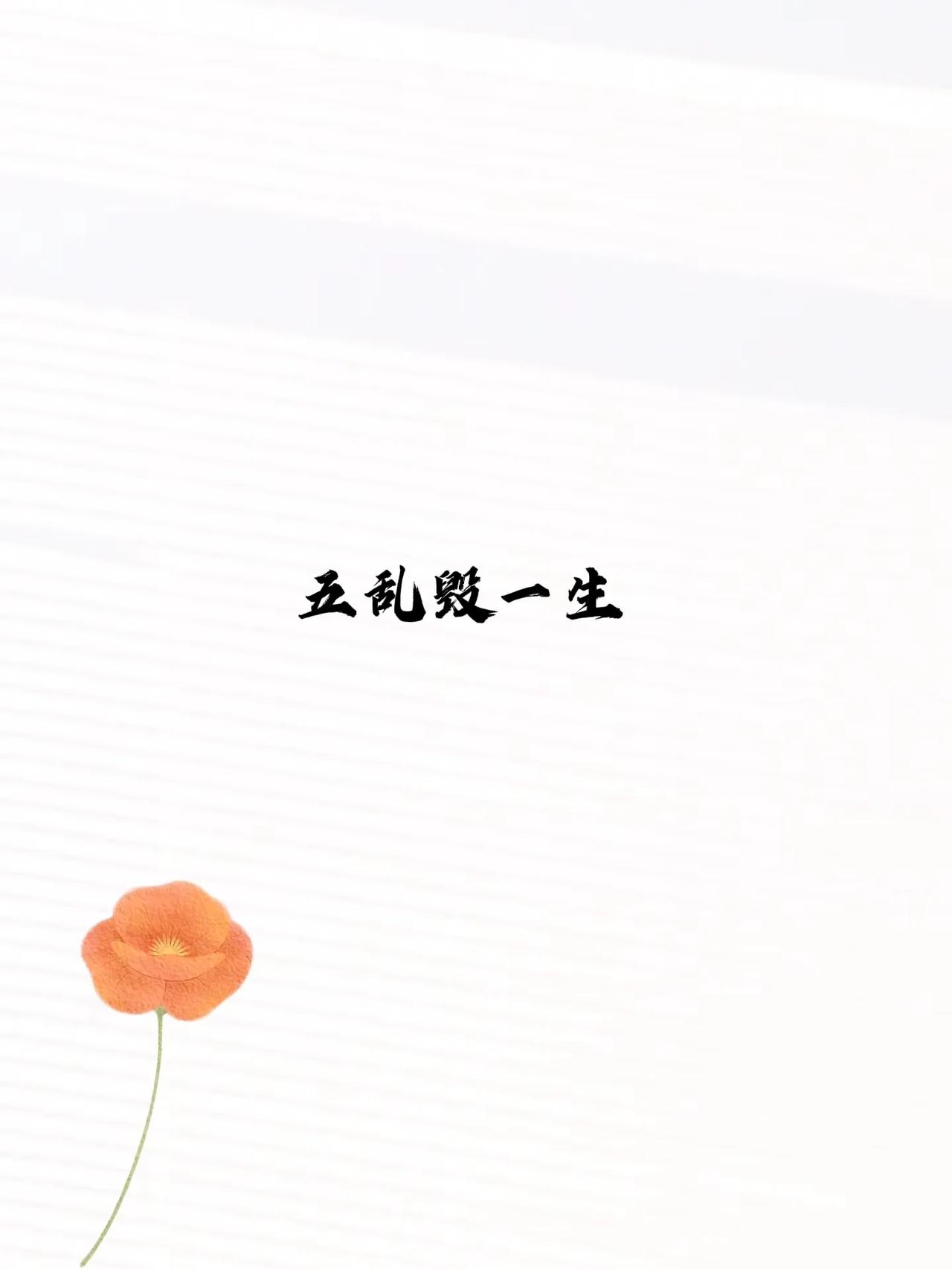《重生之美人事君》
作者:青灯

简介:
上一世,她和他争锋相对,斗了一辈子,结果是两败俱伤,害人害己。重来一次她发誓要远离纷争,远离那个印象中狠辣乖戾、阴暗心黑男人。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可那个混账却黏上来了……
精彩节选:
俞婉忽然惊醒了,喉咙仿佛吞刀子似的疼,身边有人在说话,模模糊糊听不真切,只是很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
眼睛还有点睁不开,身上重的很,嘴巴里一股甜腥的味道。难过的感觉太强烈了,她不是死了吗?都说人死后会进阴曹地府,按照德行善恶入六道轮回。她这一辈子算不上什么好人,亏心事做过不少,难道在十八层地狱受刑?没想到人都死了,痛觉还如此灵敏。
胡思乱想之间,沉重的眼皮终于有了睁开的力气,随即便吃了一大惊,这不是她爹吗?还是年轻时候的爹。三十来岁,庄稼人惯有的紫黑面膛,穿着住在大柴村时的麻葛衣裳,半点也没有后来养尊处优的富态,精神奕奕,一身朴实亲切的土气。
她不是在地狱吗?怎么爹也来了,还年轻了好多岁。虽然她跟寇冲诸多龃龉,但她爹跟他娘倒是一直很好,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两个人也没分开。寇冲再恨她,城破之前,他爹应该跟寇冲他娘一道出城了才是,怎么会死?
俞婉糊涂了,转身一看,爹身边可不站着寇冲他娘胡杏娘!同样是年轻时候的模样,脸上的柔光依稀可见。这怎么可能?俞婉不敢置信地看向自己的手,小了一号,头发也是短短的,刚留起来的样子。
“你看这不是醒了?这瘟疫真是刁钻,就瞅着小孩子祸害。林大夫说了,再吃一剂药,就该转轻了。我今天听她二叔说,镇上已经控制住了,想来再不久,这事就该过去了才对。”
瘟疫?瘟疫!俞婉想起来了,还是她十三岁的时候,春夏之交从北边传过来一种呼吸上头的病,得病的人先是咳嗽,痰淤不散,心肺感染,转化到发烧抽搐。高温降不下来,多少人死在这上头,就是侥幸好了,也烧成了傻子。这病专挑小孩子传染,那一年,只他们大柴村,就死了好几个小孩子。
俞婉的病是去看堂妹的时候不小心感染上的,也算她倒霉,堂妹俞罗衣病得比她还严重都能痊愈。她却留下了后遗症,天气一变就发病,常年咳嗽,成了个药罐子。
也是在她生病的时候,进山打猎无往不利的寇冲伤了眼睛,没能得到及时的诊治,右眼落下了终生残疾。不管是不是她故意的,他们的仇恨从这次埋下不死不休的种子。不行,她不能再跟他斗了,毕竟,她死的时候……
她一把抓住爹的衣袖,忍着喉咙的火烧火燎,沙哑道:“寇冲……后山,伤了……眼睛……”
好久没有喝水,病后又没有好好吃饭,这几个字说得无比艰难。俞婉热汗都急出来了,重复了好几遍,爹跟胡杏娘终于听清,两个人争前恐后跑了出去。
俞婉脱力地倒回床上,欣慰地看着暗沉的窗外,天色已经晚了。上一世,寇冲因为受伤,被困在山上整整一晚上,传话的人只说他掉进陷阱里。俞婉当时正跟他斗气,当然不会放过千载难逢整治他的机会,拦下了消息,酿成了终生的祸患。
其实刚开始她跟寇冲并没有那么水火不容,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小打小闹,自从他失去一只眼睛,两个人在互相仇视的道路上越跑越远。
他阻止她跟三叔做生意,公然在人前骂她恶毒坏她名声,毁她嫁入高门的机会。她也不逞多让,害他瞎眼,害死他妹妹,将他娘撵出去,嫁给他后母的娘家,跟他后母联手对付他……
直到死,也是死于最后一次交锋。不知道寇冲是什么心情,俞婉是真的累了,倦了,再也不想招惹上他。趁着一切还没有发生,就这样吧,从此他们桥归桥路归路,就在同一个屋檐下做陌生人。
俞婉这一觉睡得很安心,哪怕只是在做梦,也觉得安慰。再一次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慢慢坐起身子,浑身酸软地撑不住。菱格的木窗外天光大亮,院子里鸡鸣声此起彼伏。
胡杏娘推开窗子,看见俞婉醒了,把碗放在靠窗的桌上,“正好,早上刚熬的鸡汤,趁热喝了,病就好了。”
不说还好,一说起来,肚子顿时一阵肠鸣,好在胡杏娘什么也没有说,转身就出去了。炖得是乌鸡,已经软烂脱骨,作料不多,醇香的鸡肉味夹杂着点党参的药味,正适合病人喝。
碗底躺着几块肉,不过尝个鲜。俞婉夹起来放进嘴里,两口就吃完了,肠胃中一阵温暖的满足。要是以前,她一定会不满,在胡杏娘没有嫁进来时,家里吃鸡,爹都把肉最多最好吃的部分留给她。自从有了胡杏娘母子三人,她的地位便直线下降。
好吃的好玩的,总要先紧着五岁的寇芙,再下来才是她跟寇冲。胡杏娘把着家,偷偷补贴寇冲。她爹是个粗心的,不好意思给她吃独食,最倒霉的可不就是她嘛。
所以她恨寇冲,恨胡杏娘,甚至连五岁的寇芙也喜欢不起来。尤其是寇冲,明明得了便宜,还一副冷傲的样子,着实叫人看不惯。
从爹跟胡杏娘组建新家庭开始,俞婉就跟寇冲各种不对付,小打小闹不断。真正叫他们沦为仇人的,就是因为她的关系,寇冲瞎了一只眼睛。要说刚开始寇冲对于她还爱答不理,能躲就躲,那之后他就彻底恨上她了。虽没有对她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报复,但俞婉在胡杏娘手下讨生活,吃过的暗亏不计其数。
如今,她只想离寇冲远远的,将一切恩怨扼杀。
寇冲伤了眼睛,又掉进陷阱,好在及时得救,镇上来得大夫看过之后,用草药将伤处包扎,据说有八成恢复如初的可能。俞婉听爹这样说,心里舒了一口气,她在房间里养病,这几天一步也没有出去。
她一直在等着梦醒,一觉睡到天亮,还是在最初那个家中,俞婉终于确定,这不是做梦,是真的回来了。她有些激动,但是身子还没完全好,没有精神想太多,也不知该怎么面对前世憎恨了一辈子的仇人。怨恨寇冲已经成了她的习惯,甚至本能,只要他不好,她就开心,她那么不喜欢他,却不得不听到他的消息。
知道他虽然瞎了一只眼睛,却还是一步一步从一个火头兵往上爬,成了永平卫最骁勇的将军。在夷人南下侵略瓜州进攻永平卫时,是他凭一己之力守住了最西北的屏障庸良城,守住了千千万万人的希望,也包括俞婉的。
可是他却独独毁了她一人,那个时候破城的消息犹如一只大手掐在每个人的脖颈上。俞婉本来打算往东门出城,堂妹给她传来消息,说西北门才是安全的。堂妹身为寇冲的妻子,她的消息来源自然是寇冲,俞婉信了,却万万没想到,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死路。
她死了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断断续续留连人间。似乎只要有人跟她说话,或者想起她,她就能出现片刻。第一次是自己死的地方,一身血污、满脸倦色的寇冲注视着满地的尸首,神色狰狞、眼神可怖,一滴泪挂在满是青茬的下巴上。
他叫人收敛了将士们的尸首,将她同样埋在城外,立了碑。还在她坟前杀了一个婆子,正是罗衣身边的婆子,给她传消息的人。俞婉觉得寇冲假惺惺,可是看他深深注视墓碑的样子,又不像装的。
第二次是在坟前,一身绫罗绸缎、珠翠环绕的罗衣在给她烧纸,烧着烧着突然尖声咒骂,“为什么……爱他……却冷落……爱你……去死……”
俞婉自认为是了解寇冲的,偏偏死后的那些事完全颠覆了认知。重来一次,看在他让她入土为安的份上,她不想再跟她作对,反正,几年后他那误传战死的爹找回来,他就会离开大柴村。
俞婉躲在屋里养病,整个人都安静下来,谁也没来打扰。倒是俞罗衣过来看了一次,坐在床头亲切道:“我都能出门了,你怎么还没有下床,天天闷在屋里有什么意思。三叔说去贩东西卖,还真搞来个货箱,咱们不是说好跟他一起去镇上看看吗?长这么大,我还没有去过镇上呢,听说那边可热闹了。我之前买得粉用完了,想自己去挑挑看,跟着三叔一起,再有你,我娘肯定会允许的。”
俞罗衣长得很秀美,小小的人,小小的脸,身姿婀娜,皮肤白皙,鼻翼两端几点雀斑给她增添了几分天然的可爱,在乡下也算难得一见的小美人。俞婉却知道,现在的罗衣还小,等几年后张开了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晶莹如水的肌肤,乌黑漂亮的头发,举手投足间仿佛有仙气萦绕,纯洁美丽。
“你看着我什么?是不是我脸上的斑又印多了,我娘说这两颗大的会生小的,我还不信,不会是真的吧?不行,我一定要跟三叔去镇上看看,不知道吃药有没有用。听说有一种植物粉可以淡化这个,我表姐成亲,姐夫就给她买了一盒,两个铜钱大,要一贯钱,贵得要命。”
俞婉只是想到坟前的罗衣,歇斯底里,怒吼狰狞,与她印象中的温柔从容相去甚远。俞罗衣跟寇冲的改变给了俞婉异样的感觉,或许很多事情,都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寇冲在不在家里,我听说他眼睛伤到了,没事吧?会不会瞎啊。要是瞎了就好了,他娘不就仗着儿子撑腰在你家耀武扬威吗?要没了这个儿子,我看她还神气什么。”俞罗衣看俞婉神情仄仄,特意说些她爱听的话,俞婉还是不声不吭的。
俞罗衣推推俞婉,“你怎么了?她是不是又哪里挤兑你了,你别怕,跟我说,我回去跟我娘说,叫三爷爷三奶奶给你做主。”
要是以往,俞婉绝对就开始大倒苦水了。仔细想想,她朝俞罗衣跟二伯娘诉过很多苦,她们也说叫家里给她做主,却从来没有为了她跟胡杏娘对上过,罗衣在她面前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那对母子的好话,最后却嫁给了寇冲。
“没什么,就是还有点累。”
俞罗衣陪着坐了一会儿,玩着手上一根藤编的手镯,“你之前不是说送给我你娘那个手镯吗?我可不要你的东西,大伯娘就给你留下这么个,没事看着也能想起她。你给我戴戴吧,我玩几天再还给你好不好,我小心收着,不给别人看。”
上一世,俞婉把手镯借给了俞罗衣,不过后来被弄丢了,她伤心了好一阵子。那是娘唯一留给她的东西,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不借,“我忘记放在哪里了,等我病好了想起来再给你吧。而且在那边屋子里,那人住着,咱们怎么去拿?”
“怕什么?那是你的屋子你的东西,凭什么不能进。”
东面的屋子之前一直是俞婉住着的,生病这段时间搬到了上房的小房间,方便照顾。刚好寇冲之前住得西屋临时放了东西,受伤后就暂时安排在东屋养伤。俞婉理亏,胡杏娘偏袒儿子,寇冲住下就没搬出来了。被抢了屋子,她后来还闹了几次,越是闹,寇冲就越不让。
重来一次,已经是二十来岁的大人了,俞婉懒得跟小孩子计较,爱住就住去吧,反正他也住不了多久。安抚好了俞罗衣,回到屋子里,俞婉把床头的小柜子打开,取出一个两寸来长的黑匣子。
这匣子萦绕着一股淡淡的香气,很是神秘贵重,虽是木质,沉甸甸的,雕饰着花草兽纹,一看就价值不菲。匣中躺着一只白玉手镯,花枝弯折的样式,枝蔓缠绕,精巧漂亮,触之生温。
这是她娘留给她的,俞婉自有记忆起就没见过亲娘,有说死了的,也有说跑了的。她爹从来不提,只知道她有胡人血统,是从北边逃难过来的,为了口饭嫁在这里。
俞婉小心将镯子套在手上,细细观摩,泛着柔光的叶片似乎在光下活了一般。
嗯?不是幻觉,是真动了?!
俞婉吓了一跳,来不及将镯子褪下,白玉的手镯已经全部展开,稳稳立在她手中心,慢慢变得透明直至完全融入空气。彻底消失后,仿佛在水中晕开的浓墨,轮廓渐次显现出来,柔柔的光晕明灭交替。最后凝成一株栩栩如生的苍兰。
整枝花连茎带叶一共三寸来高,亭亭玉立在手掌中心,没有实体,像是摸到空气穿梭而过。盛开的花瓣泛着柔柔的光晕,看着仿佛就能闻到它醉人的香气。俞婉想到上辈子俞罗衣身上幽幽的似兰非兰的体香,仅为普通人的堂妹,渐渐展现出神女般的姿容,正是镯子丢了之后!
柔软美丽的花瓣上凝着三颗亮晶晶的花露,圆圆滚滚,极为逼真。俞婉忍不住用手指戳了一下,才挨上去,指尖便感受到微微一凉,仿佛周遭空气被仙雾取代,整个人如入仙境,通体温润舒畅,说不出的美好感受。
她深深吸一口气,凝神看向指尖上圆滚滚的露珠,透明的水色,却没有水肆意的流动性,像是一滴蜜蜡,整个完完整整团在指尖,凝固的一滴,散发着似有若无清淡的兰香。上辈子堂妹的变化想必就来源于此,不用想,这肯定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试探着吃了一点,没有什么味道,却被勾起了馋虫,忍不住便咽了一口唾沫。
俞婉一次性将三滴苍兰仙露全吃了,凉凉的感觉,只是觉得口腔瞬间清新干净起来。没过多久,肚子突然搅痛,跑了四五趟厕所,刚刚回到房间还没喘口气,又来了。
俞婉脱力地趴在床上,有些后悔贸贸然就敢吃,就好像穷人乍富,挥霍起来没完没了。不知是她对这东西排斥还是吃得太多。苍兰花出现的时候仙露就在上面,完全不知来历就敢入口,简直可以说不怕死,看来还没搞清楚这东西的来源跟正确用法之前得慎重对待。
好在拉完之后并没有脱水的无力感,肚子里空荡荡,整个人都轻松起来,就像肚子里陈年的堆积物全部排出来了,只是身上有些臭烘烘的,俞婉暗嘲自己把茅房的味道带出来太多。越闻越嫌弃,找出来盆子跟毛巾,趁着家里静悄悄的,一个人摸到离家半里路的溪泉边去洗澡。
水中的自己果然也是十三岁左右的模样,只不过此刻脸上黑黑的,覆盖了一层肮脏的油脂,极为邋遢,身上布满一层黏糊糊的泥垢。这条小溪泉离家不远,村里经常有人过来打水,俞婉本来打算穿着衣服擦一擦算了,此刻却膈应地只想跳进去好好搓一搓。
找到一处没人的地方,俞婉穿着小衣裳坐进水里。现在还不到五月份,正是中午,大太阳透过树木间隙筛下,并不很冷。十几天没洗澡了,没想到这么脏,足足搓了三遍,水都洗黑了,才觉得足够清爽了。
洗过的肌肤泛着一层柔柔的白,上辈子的俞婉是黄皮肤,随了爹的土地黄。因为有胡人血统,长得比一般女子高一点,只不过还是不能跟大部分男人比,尤其是寇冲,她只到他下巴。经常怒到急处,她都有一种他能一巴掌拍死她的感觉,不过他俩关系差,却从没有动过手。
有时候她气极了还会推他搡他,他破坏她亲事那一回,她气急败坏狠狠扇了他一耳光。他只吐掉嘴里的血沫,像是被人冒犯到领地的头狼,阴狠地盯着她半晌,也没有任何报复的反应。
想到以前,俞婉觉得其实自己也做过很多错事,只不过不愿意承认。这一次,就让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做一对互不搭理的继兄妹吧。
想好了未来,俞婉从水中起来,擦干净身体换上干净的衣裳。她十岁才留头,现在头发长到腰上,打着微微的小卷,漆黑柔软,如缎子一般的稠密。
大柴村处在山窝窝里,来来去去要爬坡下坎,村里人分散而居。距离她家最近的就是隔房的二伯俞家财,过去也要转两道弯呢,俞婉回家这一上路,就没看见熟人。不过这个时候快要收菜籽,家家户户都在田里忙,估摸着胡杏娘快回来做饭了,俞婉加快了脚步。
走到大门前,刚踏上土路台阶,便转出来一个瘦高的影子,差点撞上,正是寇冲。他现在才十五岁,修长的身姿仿佛枝头的柳条,正迎着春风茁壮成长,俊美的五官已经初具凌厉的轮廓。右眼上包着纱布,但无损他出众的仪态。
胡杏娘最是以这个儿子为傲,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送他拜师学艺,生怕大柴村这小地方埋没了她的儿子,最后怎么样,寇冲还不是娶了村里的姑娘。想到胡杏娘目中无人半辈子,儿媳妇却是她最看不上的罗衣,俞婉就要笑死了。
虽然想好分道扬镳,乍见宿敌,俞婉还是忍不住翻了翻白眼,从他身边匆匆略过。寇冲嘴唇动了动,漂亮的女孩便如一阵风似得卷过去了,只余下淡淡的香气,萦绕鼻端。
胡杏娘老远就看见儿子跟继女在门前遇上了,赶紧走过去道:“她又说你什么了?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好好学你的武艺是正经。等你往后出息了,俞婉又算什么。”她看见继女瞪了儿子一眼。
“没说什么。”寇冲现在正处于变声期,嗓音难听,能不开口就不开口。
“这一次还算懂事,那天要不是她传消息,我跟你俞叔都不知道你伤了。也怪柱子,家里这么多人跟谁说不好,就算不在家就不能等等,也太贪玩,跟俞婉不清不楚说了一句就跑了。还好及时找到你,大夫可说了,你这眼睛这次凶险,再耽搁下去,只怕就废了。俞婉就是那个样,别计较,躲着些就是了。”
俞家兴只有这一个女儿,男人家虽粗心,却看得重。胡杏娘不愉儿子跟继女发生矛盾。
寇冲却知道,这一次还真多亏了俞婉,他跟柱子其实关系不怎么好。他从小学武,身手好,爱打猎,又识字,自从他来到大柴村,柱子这个孩子王就失去了威信。他一直在镇上跟着师傅习武,不常回来,大家反而更推崇他,柱子不喜欢他又怕他。
在林子里看到他杀野猪,扭头就跑了,能来说一声,已经很不错了,哪怕是随口一句。
俞婉才真的出乎意料,据娘说,那天她自己还发烧呢,却急得要命,一定要家里去找他,这才没有耽搁他的伤势。以往她虽然老是找他的麻烦,讨人嫌,大事上面却很知道分寸,他该感激她的。
俞家兴是家里老二,爹娘跟着大哥一起住,早年就分了家,只给两个老人家交粮送钱。他有水田也有旱地,还有几亩山林。家里就他一个健壮劳动力,整天在田里忙活也做不完。
中午吃完饭,家里人口多的还能歇歇晌,他却没那功夫,家里喊叫吃饭就连忙从地里回去。
老旧的方桌摆在堂屋中间,桌上一盘盐菜,一个丝瓜汤,米饭里搭着土豆——乡下人都这么吃,省米。五岁的寇芙眼巴巴在桌前,看姐姐摆筷子。俞婉把一碗米饭多土豆少的碗放在爹面前,爹每天从事大量劳动,是这个家的顶梁柱,理应吃好一点。
俞家兴点点头,问了一句她的身体,便沉默地坐下了。他觉得现在挺好,胡杏娘年纪比他小几岁,不管是饭食还是针线都拿得出手,家里摆布地井井有条,将闺女也照顾地好。儿子虽然不是他的,但人不错,又有傍身的本事,往后肯定能帮衬女儿,他现在养家,老了寇冲自然会看顾他,这样就很不错了。
爹一直老实巴交的,上辈子虽然重视寇冲,但也还算看顾她,她死后,爹是哭得最伤心的。想想上辈子满头白发的爹,俞婉就不想计较那么多了。
摆好了饭菜,俞婉打算在爹的左手边坐下,一看少了一双筷子,复又进厨房去拿,等她回来,寇冲已经坐到了她的位置。俞婉又忍不住翻白眼了,也没看他,径直坐到了最南面。
她不喜欢吃土豆,但家里现在这样子也是没有办法,俞婉用筷子戳了戳米饭,发现只有最上面覆盖着一层土豆,下面全是米饭。想想就明白这是胡杏娘给寇冲的,没想到阴差阳错到了她手里,俞婉冷笑着扫了一圈左右二人。
感受到她的目光,寇冲原本缄默的嘴角更加冰冷地抿起来,低垂的视线掩盖住所有情绪。胡杏娘装作没看到俞婉看过来的眼神,低头给寇芙喂了一口饭。
刚刚寇冲坐到她对面去,她就想提醒儿子坐回去,偏偏儿子好像故意跟她作对,一点都不看她,她这么斤斤计较是为了谁?儿子正长身体,不吃点米饭怎么行?他却一点不懂她的心,还觉得丢人,真是气死人。
俞家兴端着饭,狠狠扒了两口,看着妻女儿子,对胡杏娘道:“冲儿的衣裳都短了,你重新扯布给他做一身吧,他经常去师傅家,那么多师兄弟看着不好。”
胡杏娘温柔笑道:“这个年纪,一天一个样,衣裳哪里换的过来,差不多就行了。倒是你,多久没有做新衣裳了,补吧缀着补吧,等闲了,该给你做一身好衣裳才是,过节年下的那么多叔伯兄弟看着才像样。”
胡杏娘这个人就是这样,表面上对儿子苛刻,衣裳都穿得破破烂烂,实际上家里什么好吃的都叫她补贴给了儿子,只是表面功夫做得极好,且也算真心对待爹。俞婉每每找她麻烦,都被轻易化解。
吃完饭,俞家兴将喝完水的葫芦灌满水,拿着镰刀又下地去了。俞婉将碗筷收去厨房,出来看见寇冲在门前磨刀,随后背了个背篓也出门去了,她挎上小篮子紧随其后。
路过二伯家,上了田坎,察觉她还跟着,寇冲回头看了一眼。俞婉仰着头,扭开视线,从斜坡边走开,不用回头看就知道寇冲诧异的目光。以为她乐意跟着他吗?就算他们和解了,她也没有要跟他深交的意思,哪怕刚才饭桌上寇冲顶着胡杏娘责怪的目光将那碗饭堂而皇之地让给她。
她要去找三叔,三叔近来在做生意,挑着两个箱子走街串巷,贩些零碎的小东西。她上辈子嫁过去的周家家大业大,她虽嫁得庶子,分家的时候也得了些田地跟一个杂货小铺面,收益并不如何。
后来她改换了方向,将顾客定位成年轻的小媳妇大姑娘,卖些脂粉香膏,慢慢稳定了客源,这才赚了些钱。之所以将一个杂货铺子改成完全没接触过的另一行,还是因为出身青楼的姨娘婆婆手里有几张方子,俞婉本就对那些东西感兴趣,自己没事就试着做,成品还不错,努力钻研之下,倒叫她摸出来一些门路规律。
东西跟真正的名品差得远,但小地方穷苦人家也买不起好东西,她做出来的在同行里面,价格实惠,质量还行,自然容易打开销路。上辈子俞婉为了跟寇冲作对才嫁得不好,丈夫本就不是个安分的,自她进门后,更是玩的花,她一个孩子没生,姨娘小妾生了一大堆。
这辈子俞婉不想重复上辈子的命运,首先就是要把家里经营起来,至少摆脱看老天脸色吃饭的日子,攒点嫁妆,再也不受人白眼。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做女人的生意,没见就是乡下地方,但凡手里有点余钱的,甭管多大年纪的女人都在乎容颜,爱些脂啊粉啊的,她又有基础,从这里入手应该不难。
俞婉想好了,先跟三叔打听清楚,也给他个思想准备,以便将来合作。现在家家户户都在割菜麻,三叔应该在家,没成想三婶说三叔一大早就出门了,恐怕晚上才能回来。
俞婉有些失望,随即振作起精神,挎着篮子就上了自家的林地。不管是制作胭脂、水粉、熏香都需要从花中提取原料,对于花束的选用也比较讲究,已经完全盛开的花束她只要最完整无缺、没有虫蚁啃咬的花瓣,将开未开的花苞则从根部折断。
将自家林地里的花采完了,又去周边找,反正乡下地方什么花没有,大片的野花根本没有人要,不能吃不能喝的,正好便宜了她。
采好的花束完全不用清洗,去叶去梗装进罐子,加入植物油直至淹没,最好是用橄榄油、芝麻油或者其他味道清淡的油,俞婉手边没有。好在她有一小罐花生油,尽够用了,泡好了放在柜子上,还要等三天才能继续制作。
做完这些,时间就下午了。
胡杏娘自中午回来,再没有下地,家里养着十几只鸡、一头猪,还有菜园子,这些都是她的活。做好下午饭,打发五岁的寇芙去田里,寇芙还小呢,看起来只有三岁差不多,走路颠一颠的,扑到俞婉腿上,仰着头看她。
“我去喊我爹吃饭。”
俞婉在家里从来不做活的,她爹惯着她,连猪草都不叫她打。胡杏娘自然不说什么,反正她只做好自己那一部分,多出来的俞婉不做,自然有俞家兴代劳,再者寇冲在这家里同样是个花钱没什么进益的存在。她管不着俞婉,俞家兴自然也管不着儿子。
“那早去早回吧,把桶拿上,回来叫你爹带桶水。”
她家的几块地是分开的,爹今天在忙活山脚下一块,路上陆陆续续有人朝家里赶,看见俞婉抱着寇芙,纷纷打招呼,“婉儿大好了?去喊你爹回家啊。”
“好像瘦了些,要好好吃饭,赶紧把身子补起来。”
“没事了去婶子家里玩啊,小十儿念叨你呢。”
俞婉一一打招呼,觉得家乡很是亲切,有山有水,气候得宜,虽然上辈子嫁人后吃得好住得好,最想念的还是在娘家无忧无虑的时光。
一天的功夫,山脚最大的一块地就赶出来了,菜麻割倒之后还得再晒几天才能打。俞婉真心觉得她爹厉害,走近一看,原来地里有两个人,一人割倒了一大片。
看见俞婉过来,天色也慢慢暗了,俞家兴直起腰杆,很满意今天的成果。再有两天,家里这几块地就能全部收拾出来了,他朝后招呼一声,那边埋头苦干的人不是寇冲是谁。
俞婉知道寇冲武功学得极好,又能识文断字,但家里的活他从来没有干过,将她爹一个人累得要死要活,她时长骂他都是拖油瓶长吃软饭短的。寇冲气得要死,却从不反驳。上辈子他当上将军之后,给她爹重新盖了房子,置下一个庄子养老,还买了仆人伺候。
爹劝她跟寇冲好好相处,嫁人之后他也算个撑腰的,哪里知道他们早就不死不休了。
上辈子爹对寇冲好,恐怕也是为她打算吧,偏偏她不清楚爹的苦心,有意无意将人得罪死了。
俞婉站在一边看爹跟寇冲收拾东西,寇冲年纪虽小,比她爹还高,挺拔的个子强劲,腰杆极富弹性,四肢蕴含力量。人虽瘦,却不干,露出的手臂上肌肉在皮肤下滚动,微屈的指头骨节突出,青筋纵横,像一只即将跨入成年的幼兽。他脸上布满汗水,被他随意一擦,有一滴悬在下巴上,衬得他红唇秀目,极为出挑。
寇冲有一副非常出色的皮相,总能轻易给人极好的第一印象,虽然他不姓俞,俞家却没一个人说他不好的。就算俞罗衣,一边附和俞婉说他坏话,一边还不是经不住他的家世人才嫁给了他。
说起来,寇冲这个人不管对她怎么样,在俞家极为讨人喜欢,将她的亲人都给笼络了过去,包括她爹在内,真是叫人不爽。怀里的寇芙不安分,看见哥哥就要抱抱,俞婉快搂不住她,吓唬道:“你再闹,掉下去了把屁股摔成四瓣,变成个丑八怪,小花、阿狗儿他们就不跟你玩了。”
这小丫头上辈子也跟她不对付,简直就是寇冲的跟屁虫,很招俞婉的嫌弃。想到寇芙死在了七岁那年,俞婉就闷闷的。当时寇冲已经去了边境最混乱的安西卫从军,有一次夷人联合大食人南下侵犯,怀惠关吃了败仗的消息传来,俞婉正跟寇芙怄气,随口吓唬她,哥哥被夷人打死了。
寇芙信以为真,跟几个小伙伴离家出走,结果冬天路滑,掉在村外的冰窟窿里冻死了。俞婉强自安慰自己寇芙的死跟她无关,可寇芙那张青白交加、毫无人气的小脸却一直晃在眼前,而寇冲充满恨意的眼神也时常出现在梦中。
寇芙委委屈屈地瘪嘴,“哥哥,哥哥抱。”
俞婉垂着眉眼,面无表情地将寇芙朝寇冲怀里一塞,扭头朝爹追去。寇冲慌忙接住妹妹,脚下一顿,追着俞婉而去。
五月中,正是漫山遍野大朵刺玫瑰开放的季节,如彤云一般分布在大柴村,随处可见。俞婉刚开始挎着篮子采,后来干脆背着背篓每天早出晚归。而且她还发现了掌心苍兰花另一个用处,可以直接从花草中提取纯净物,只不过大概十斤玫瑰花才能凝聚成小拇指指甲盖大小一滴玫瑰精油,是极为珍贵的精华。
这一滴虽然小,滴进水里,却能使半人高的一缸水散发出馥郁芬香的玫瑰花香味,好闻而不刺鼻,跟人工淬炼的提取物有天壤之别。有了这东西,她甚至可以提取出任何一种花草的精髓,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香膏、胭脂、水粉甚至入药的吃食。
只是,现在没钱,不说用量巨大的橄榄油、芝麻油之类,就是便宜的玉米油跟大豆油也买不起,还有装香膏的小盒子,制作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器具。先前她制了最简单的白玉兰香膏,在里面加了稀释后的苍兰仙露,托三叔拿去卖,偏偏三叔刚入门,走街串巷都找不到多少客人,三盒香膏还好好躺在箱子底,怎么带出去的又怎么带回来了。
“婉儿啊,我看你这个是好东西啊,比你三婶几十文钱买得香膏还要好,只不过你这定价一吊钱实在太贵了。你说,我见的那些人哪有这闲钱,就是看着东西好,想买也买不起啊。其实还是有不少人问的,依我说,你要不要少一点啊?二百文三百文也好啊,哪有一上来就要一吊的,一吊钱都够好些人家半个月的嚼用了。”三叔擦着额头的汗水,委婉劝道。
他本来也不打算跟小孩子胡闹,俞婉找上他要卖香膏,俞家忠根本不信她一个乡下小丫头能做出什么好东西,一看之下才发现比他卖的那些好,这才收起了敷衍的心思。
只不过生意实在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好做,你一个刚入门的,白眉赤脸地去卖东西,根本没人搭理。阳康镇就那么大,早被其他货郎瓜分了区域,不熟的人家根本不买你的东西。就算是有固定铺面的脂粉行,也有稳定熟悉的进货渠道,自己手上就这两三盒,人家把价一压,完全不给出头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