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适用的具体技术来说,排除条款的效力认定最终落实到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谁更优先的认定上。
 两岸对排除条款态度差异之原因分析
两岸对排除条款态度差异之原因分析一、法院的审判思路不同
我国大陆地区法院在对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的效力进行认定时,一般按照以下的审判思路来处理:

一是笼统适用公平原则。
若认可该条款的效力会使合同双方在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失衡,也就是说认可排除条款的效力有违公平原则,法官会倾向于认定排除条款无效。
二是法官首先判断被排除的法定解除权是不是强制性规定,进一步审查是不是效力性规定。

若是,则判定该排除条款无效。
然而,公平原则本身就没有明确的适用标准,更多需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

同时,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也同样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这使得法官经常在有效与无效之间犹豫不决。
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的效力认定,法院的判决各不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排除条款的效力最后似乎只能依个案由法官衡量把握。
判断标准的巨大弹性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必然结果,给商业实践中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在认定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的效力时则会更多地参照以往的判决,尤其是台湾最高法院的判决。
台湾最高法院1957年台上字第1685号判决书和台湾最高法院2004年度台上字第32号判决书中都明确表达了对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的肯定态度。
对于保留解除权的约定,台湾最高法院明确表示,台湾地区“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的规定,仅为法律所规定的解除权的一种,并非禁止契约当事人之间另有保留解除权的特别约定。

当事人之间有约定解除权的,就其解除权发生的原因,解除权行使的方法,解除后的效果,有特别约定的,应依其约定。
据此,只要合同约定的条款在性质上可以被判断为是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对于排除条款效力的态度均遵循先例采肯定态度,即以合同当事人的约定优先。
二、对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关系的理解不同
对于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之间的关系,我国两岸法院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我国大陆法院认为约定解除权并不排除法定解除权的适用;
而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则认为基于私法自治及契约自由原则,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虽可并存,其适用顺序及效力仍应以约定解除权为先。
台湾高等法院认为,契约之履行,本即包括可测或不可测之风险在内,而私法自治及契约自由原则乃在使契约当事人于不违反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

公序良俗及公平原则之前提下,得自由评估缔约当时之风险损失益,并基于风险控制之目的,于契约中对特定情事之事发生。
预先约定其法律效果,安排其损益归属,此可谓系私法自治及契约自由原则之重要目的之一。
如认法定解除权优先于约定解除权而为适用,则将违反两造缔约时之风险损益评估,破坏双方于意思是合致时有关损益归属之“主观平衡”。

干预契约冲突私经济生活之安排,更将悖于私法自治与契约自由原则之基本原理。
可见,如果认为约定解除权优先于法定解除权,则大概率会支持排除条款的有效性。反之,亦然。
就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有效性认定的处理方式,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孰优孰劣不能匆忙下结论。

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看似一个小问题,实则反映合同自由与合同管制之间的微妙关系。
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一律有效或一律无效的结论可能过于简单,难以适从错综复杂的商业实践。
那么,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什么情况下有效,什么情况下无效,是否存在科学合理的判断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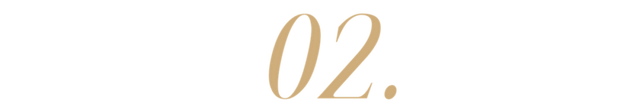 合同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的关系
合同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的关系要明确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效力的问题,首先应当探究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的内在关系。
进而考量合同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法定解除权的行为是否符合合同契约自由原则和公平原则,并以此为依据对合同法定解除权排除条款效力进行判断。
一、两大学说的对立
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解除权产生条件由法律直接规定;后者的解除权条件由合同双方约定。

约定解除可以约定合同的其中一方保留解除权,也可以约定合同双方均保留解除权。
解除权的约定并非必须与主合同的其他内容同时约定,也可以事后补充约定。
在实践中,合同双方对解除权产生条件进行约定可能出于多种因素的考量,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增加违约方的违约成本。

约定解除权同时也存在对法定解除要件进行修正、缓和或补充,让当事人在观念上明确解除权产生条件的功能。
就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约定解除条件排斥法定解除条件说”和“法定解除条件大于约定解除条件说”这两种学说。
前者认为应当优先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通过约定对法定解除条件进行调整;后者认为法定解除条件不因当事人的约定而排除适用。

崔建远教授对此采折衷说,认为在约定解除条件可以涵盖所有解除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合同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法定解除条件。
但如果约定解除条件无法涵盖所有解除条件,便可以适用法定解除条件。
就我国司法实践而言,大多数的法院倾向于采用法定解除条件大于约定解除条件的观点,认为约定解除权并不排除法定解除权的适用。

二、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的冲突
笔者认为,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的冲突可能呈现四种情形,用数学模型抽象地描述可以将此四种情形概括如下:
(1)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的范围包含了约定解除产生原因的范围;
(2)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的范围与约定解除产生原因的范围相交;

(3)约定解除产生原因的范围包含了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的范围;
(4)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的范围与约定解除产生原因的范围相离。
关于情形(1),约定解除本来就应当是法定解除的补充和修正。

如果采法定解除条件大于约定解除条件说,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产生原因的范围仍停留在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的范围之内。
那么其约定的内容便是作为对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的细化和补充。
因此,在此种情形下不存在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的冲突,当事人的约定有效。

如果采约定解除条件排斥法定解除条件说,那么就需要考察被排除的法定解除产生原因是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若是强制性规范则不可允许合同当事人通过约定予以排除。
关于情形(2),需要将模型分为三个部分进行效力判断:
一是约定解除产生原因与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相交的部分;二是排除相交部分后约定解除产生原因的剩余部分;三是排除相交部分后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的剩余部分。

针对约定解除产生原因与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相交的部分,既然法律明确规定的解除权产生原因,合同当事人也进行了相应的约定,那么此部分自然是有效的。
针对排除相交部分后约定解除产生原因的剩余部分,则应当考察超出法定解除产生原因部分的约定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如果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应当根据契约自由原则,以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承认该约定条款的效力。

针对排除相交部分后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的剩余部分,该部分是否因被排除在合同当事人的约定之外当然的无效应当考虑两个因素。
首先,应当判断该法定解除权产生原因是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如果是强制性规范则不允许合同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如果是任意性规范则可以通过约定排除。
其次,应当考虑如果排除了该法定解除产生原因,是否会造成显失公平的后果,此时应当将公平原则纳入考量范围。

关于情形(3),如前文对情形(2)的论述,在合同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权产生原因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解除权产生原因。
则需要考量合同当事人的约定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如果没有,则应当尊重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约定有效。

关于情形(4),此种情形是指当事人通过约定完全排除了所有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的情形,此种情形在司法实践中鲜有发生,因而讨论价值不大。
其效力判断方法也应如前文对情形(2)对于“排除相交部分后约定解除产生原因的剩余部分”和对“排除相交部分后法定解除产生原因的剩余部分”的判断方法一致。
三、约定解除权的界限
《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允许当事人对解除权条件进行约定,出于对合同自由原则和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一般情况下对于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权产生原因法律都予以认可。

但私法自治总有其边界,不可无限度的扩张。
当意思自治的扩张触及法律规定时,其效力便值得商榷了。
在司法实践中,因约定解除权产生的纠纷,多数是由于当事人对于解除权条件的任意约定,导致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衡。

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两种解决的途径。
从立法层面来说,由于我国《合同法》对于约定解除权的规定仅限于《合同法》第九十三条。
规定过于简单,便导致了合同当事人对于解除权条件的约定过于随意,这样便容易导致合同当事人权利以关系失衡的问题。

因此,应当明确约定解除权的条件。
从司法层面上来说,司法机关可以在审判过程中通过对合同的解释或者显失公平等其他制度解决,这也是民法体系化的体现。
公平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的体现是以“程序公平”为主,以“实质公平”为辅。

其中,“程序公平”是指合同法关注的重点在于合同的缔结是否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不特别在意合同履行的结果。
合同法本身注重程序公平,是以尊重合同自由、尊重当事人自主和自治为前提的。
当事人自己是自身利益的最佳裁判者。

双务合同中的给付与对待给付客观上是否相当,涉及因素甚多,欠缺明确的判断标准,应采主观等值原则,当事人主观愿以给付换取对待给付即可。
而“实质公平”是指从合同的最终结果着眼,看双务合同中给付与对待给付是否均衡,如显失公平、情事变更、调整违约金的情形。
约定解除权的界限,究竟应该在实质层面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还是应该仅在程序上对约定解除权的条件作进一步的规定?

归根结底,是对合同正义应当“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的判断。
笔者更赞同韩世远教授的观点,我国《合同法》是以“程序正义”为主,以“实质正义”为辅。
合同当事人是对于自身利益衡量的最佳判断者,只要合同当事人主观上认为给付与对待给付相等值,那么就应当认为双务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均衡的。

因此,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便是解除权约定生效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出现了欺诈、胁迫等意思表达不真实的情况,合同当事人对于给付和对待给付的主观等值判断便不再可靠,那么在合同中“程序正义”的基础便发生了动摇。
此时便需要“实质正义”进行调整,由司法机关根据个案的客观情况对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

此时便不再参考合同当事人的主观判断,而采客观等值原则来判断给付和对待给付是否等价。
综上,约定解除权的界限,关键要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如果意思表示真实,则采主观等值原则,按照当事人主观的判断来调整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意思表示有瑕疵,则采客观等值原则,按照个案客观情况调整给付与对待给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