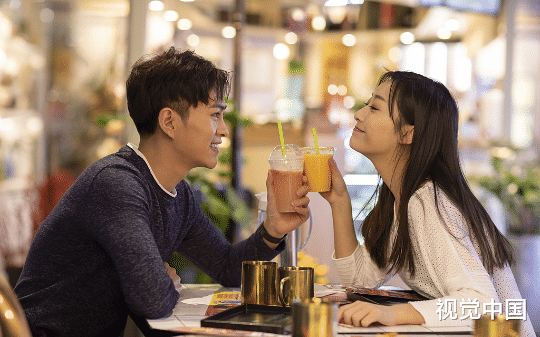“南星,你真愿代替阿月吞下这枚忘情蛊,成为南疆圣女?就此,断绝人间情爱,也断绝与燕星河的婚事么?”圣母羲皇座下,老族长手捧琉璃罐,神情略悲悯。
司南星叩首,身上银饰泛起泠泠的轻响,可她的嗓音却比银铃更清脆决绝:“我愿!”
忘了俗世一切烦恼。
忘记燕星河。
让他和阿月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成圣女,护南疆,是我平生所愿,请老族长,赐蛊。”
老族长叹:“也罢,蛊虫生效需十日光景。”
“十日之内,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你中蛊消息,以免节外生枝,切记,切记。”
司南星俯首受戒:“南星谨记。”
十日后,她再非自己。
从此,只是守护南疆的圣女。
走出圣殿,天光刺目。
剑仙燕星河沐天光踏残阳而来,他白衣胜雪,周身金辉熠熠,眉目凛然,不可逼视。
“你来此作甚?”他目光凌厉如剑。
刺得人生疼。
不像对未婚妻。
倒似对什么邪魔外道。
分不清是蛊虫作祟还是什么,难言的酸涩弥漫口腔。
司南星十指扣紧,一脸平静相望:“那你来做什么,为了阿月,还是我?”
燕星河剑眉微蹙,目光愈冷。
“你又是如此。”
“我从来如此。我们南疆女子直率,想说便说,想做便做。”
这些年来,司南星一贯如此。
所有人都知道,她喜欢燕星河,喜欢这个曾因受伤,误闯南疆的谪剑仙。
自小她就追在燕星河身后,只因他不喜,她便封存了蛊虫不用,转而去学中原的礼义廉耻,捧着晦涩难懂的道经,跟着他去中原仙门修习道法。
但燕星河此人清冷孤傲,天资高绝,被认定为仙门下任掌教的不二人选。
红尘婚姻,本是不配玷污他这样的谪仙人物。
可年前,自从阿月被确定要成为苗疆新圣女的一刻。
他却自称有了心仪之人,顶着三千仙神的反对,也要与备受鄙夷的南疆左道联姻。
指名道姓求娶司南星。
得知消息的她开心极了。
可是直到上个月她才知道,他娶她,不过是退而求其次。
娶了她后,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常驻南疆,看望阿月了……
燕星河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和阿月清清白白,你为什么总……”
“星河哥哥!”
叮铃铃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驾驭着飞马蛊的司北月一阵风似的冲出来。
“太好啦!我不用服下忘情蛊,更不用当这个圣女了啦!”
阿月小脸通红,乳燕归林一般扑进燕星河的怀里。
燕星河身形如山,将她牢牢抱住。
他冷峻的面目微微柔和。
连声音也温柔:“你是苗疆万年来资质最好的苗女,十日后就要正式成为圣女了,他们怎么舍得放你走?”
“族长爷爷说,有个命格与我相同的苗女愿成为圣女,天资虽稍弱些,对方心智坚定,比我这样吊儿郎当的更适合守护咱们南疆。”
阿月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燕星河见之一笑。
一瞬间,冰消雪融,云开雾散,灼灼风华叫人睁不开眼。
哈。
司南星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原来,皎皎如天上冷月的剑仙,并非大爱无私。
他爱众生。
可他也会为一人低眉浅笑。
只是那个人,从始至终都不是她……而已。
司南星垂下眼,敛去眸中苦涩。
“星河哥哥,你刚和南星阿姐因为我在吵么?别吵啦,现在一切都好啦。”阿月笑眯眯地去拉燕星河的手,“和好吧,好么?我不想你们因为我吵。”
她像个女主人,自如地横亘在一对未婚夫妻之间。
而燕星河冷峻如冰的眉目越发温和:“嗯。”
仿佛只有她是个局外人。
司南星的心中仿佛有蛊虫密密麻麻啃噬,喉间似被什么堵住,她微微攥紧拳头,转身欲走。
蓦然被阿月拉住。
“南星姐姐,别生气了。都要和星河哥哥成亲了呢,也就十日光景,到时候请我喝上一杯喜酒,好不好?”
司南星脚步一滞,浑身僵了僵。
“想喝喜酒?那你自己摆一桌。”司南星甩开她的手,笑吟吟压抑住眼眶里的泪。
十日后她成圣女,燕星河便可名正言顺的求娶阿月了。
等阿月和燕星河成亲了,自斟自饮去好了。
“浑话。”燕星河猛地攥住她的手腕,淡漠的眸中浮现出隐隐的愠怒。
“你我……婚姻之事,岂容儿戏?”
司南星笑了笑,没有回答,转身便走。
转过身那一刻,眼里的泪珠坠落。
司南星仰首,扯了扯嘴角。
年前,她听见这话的时候多么欢喜。
燕星河来说,立在那一片千日醉兰花丛中,长身玉立,皎如玉树临风。
她也曾像阿月一般,百灵鸟似的扑过去围着他打转。
踮脚凑在他耳边,坏心眼的吐气:“小相公,终于动了凡心,要被我娶回家做相公了么?”
剑仙一侧身,呵斥:“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你……你成何体统。”
语气虽冷,如玉的耳根却通红。
“说嘛说嘛,你不说,我就当你是喜欢我啦~”
那时的司南星欢心鼓舞地拍起手,全身银饰叮铃铃的脆响,仿佛为一双新人伴奏的欢歌。
“小燕真可爱,连喜欢我都羞得说不出口,嘻嘻。”
呵呵,现在想到这些,就感觉好生可笑。
回到住所,她伸手抹了抹脸上干涸的泪痕。
挺好的,中原有句话,叫君若无情我便休,那就这样吧。
再等九日,她就会忘尽前尘了。
不是司南星,只是守护南疆百姓的圣女。
第三天,仙门的传音灵鹤飞来,通知她已将聘仪送来。
司南星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去。
聘仪中有一件南疆失落已久的圣物——傩面
身为未来的圣女,她即便退婚,也得将这东西讨回来。
南疆神足蛊缩地成寸。
她到时,恰是约定时分。
可刚落地,便见到阿月拿着一张傩面,在自个儿面前兴致勃勃地比划。
侧首,对着一旁的燕星河问:“星河哥哥,好不好看?”
说着,便将那傩面戴上去。
“住手!”
司南星一声冷喝,运足了法力,震得阿月“啊”的一声惊呼,跌在了燕星河怀中。
“南星,你吓她做什么?不过是一张傩面。”
燕星河不由分说,冷声呵斥。
小兔子般的少女,瑟缩在身材高大的剑仙怀中,被他牢牢庇护着。
司南星嘴唇翕动,可是望着面前这一对相拥的璧人一般的男女,那句“道行不足者,必遭傩面反噬”终究没有解释出口。
“没事的,星河哥哥你别怪南星姐姐,是我不好。”反而是阿月扯了扯燕星河的衣袖,有些局促地低下头,“南星姐姐,我不该乱动你的东西,这都是给你的聘仪。”
“我只是情不自禁……”
没等她话说完,司南星冷着脸,上前劈手夺过。
燕星河刚皱了皱眉,想说些什么,便被司南星打断:“除了这张傩面,你想要什么,只管拿去吧。”
“南星,你又在任性了。”燕星河提高了声量,“你的聘仪,也是能让的么?”
司南星手抚着傩面,没有做声。
其实她很想说,若他愿意,聘仪、昏礼、还有他……给阿月又如何呢?
让?是她让阿月,这些本就是燕星河想给阿月的呢?
可她的骄傲终究不允许她开口。
“我想要的,只是这一张傩面而已。”她咽下喉间苦涩,淡淡说。
“只要傩面?珠冠呢?喜服呢?聘仪呢?”燕星河拧起眉,摄人的目光落下来。像谪仙审视臣服在他面前的凡人,声音冷得似天边落下的雪,“阿月已经道歉了,你还在任性?”
“好了好了。”阿月抱着燕星河的手臂摇啊摇,“别说傩面的事了,南星姐姐,你可是新嫁娘,快去试试中原的婚服吧,我还没见过呢,想看!”
“因为我耽搁你们的话,我会于心不安的。”
说着,她拱手作揖,憨态可掬的模样,令燕星河望向司南星的目光越发冰冷。
司南星连张口的力气也失去了。
她能说什么呢?立刻退婚?
但她答应了族长,不能说。
更何况,她就算说了,燕星河大概也不会信吧。
不被爱的人做什么都是错。
算了,还有七天,到时候他们会知道一切的。
她拖着疲惫的身体,不想再跟燕星河争吵。
接过阿月递来的婚服,默默进了内堂。
大红的嫁衣,鲜艳娇美,倒是与燕星河今日一身大红绛绡道袍相映成趣。
曾经,她梦寐以求的,确实是穿上中原的嫁衣,和那位惊才绝艳的剑仙举行一场盛大的昏礼。
但如今不愿了。
何况,这嫁衣上的符文与珠冠上的禁制,是需要巫术认主后才能穿戴。
可因为巫蛊有伤天和,不为燕星河所喜,她早就弃之不用。
燕星河怎会不知,真正精通巫术的是定为南疆新圣女的阿月?
这嫁衣或许本来就是他为阿月预备的。
穿不上也好。
司南星抱着嫁衣,笑了笑,望着镜中脸色苍白的自己,恍惚间,想起百年前遇见燕星河生出的妄念。
她觉得自己真有些可笑。
嫁衣终究没试成。
司南星一身苗女装扮原封不动出去,引得阿月一声惊呼:“南星姐姐,怎么未穿婚服?还在和我赌气吗?”
司南星淡淡道:“没有,只是衣裳不合身。”
“不合身?怎么会……”
阿月一时讷讷。
燕星河却猛地望着她,眉头微蹙,冷淡地睨视,看不出情绪:“既不合身,那再定做一件合身的便是。”
司南星轻笑着看了燕星河一眼,转身离去。
回到屋自家草庐中,长老已派人送来了形形色色的蛊虫。
忘情蛊,是一种特殊强大的蛊。
以人爱欲为食,以蛊为食,一旦养成,就是万虫之王,众蛊之王。
八十年前,燕星河修无我剑时,司南星还想着讨一味忘情蛊助他修行。
燕星河厉声呵斥她:“宁可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他总是这样,脊梁骨仙门礼义锻造出来的,求的是天理公心,哪瞧得上南疆的下流货色?
司南星就是那时候咬着牙放弃自己喜爱的巫蛊,转而去研习他爱的大义、公理、道经、剑诀……学着学着,连她都会觉得燕星河说得对。
人活一世,不能总像她一样任性妄为。
成为圣女,除了想逃避他以外,其实也就因为这个。
南疆生她养她,她也该有所回报。
割破指尖,司南星全神贯注,强忍着蛊虫噬体的不适,全没注意到,燕星河来了。
手腕猛地被他攥住,蛊虫被结界弹开老远。
“你又在养蛊。”燕星河的指尖很冷,嗓音犹有过之,“我不是告诉过你,蛊毒此物有伤天和,少碰为妙吗?”
蛊虫一断,忘情蛊噬心之痛疼得司南星面色煞白。
其实她本不该再动情欲,平白多受苦楚,可她还是忍不住偏头望着他笑:“我养便是伤天害理,是么?那旁人呢?”
“是不是不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错就是错。”
那阿月呢?
她做什么对你来说都是对的吗?
司南星头一次没听他的,扬起头,倔强道:“若我不愿呢?”
燕星河绷着脸,不说话,可看得出来,他生气了。
下一刻,剑气四溢,剑光纵横。
蛊虫四散奔逃着,在屋中哀哀飞翔。
司南星刹那间头脑一白。
“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杀我的蛊虫!”
她尖叫着扑上去,想要护住自己的蛊虫。
可是剑仙的剑,何其厉害?
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漫天蛊虫落下,仿佛一场无声的哭泣。
司南星呆呆地望着自己面前的虫尸,和悬停在自己面前缓缓消散的剑气。
她尖叫一声,扑了上去,绝望地给了燕星河一巴掌。
“你就那么喜眼睁睁看着我为你舍弃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步步变得面目全非的模样么?”
“为什么?为什么——”
明明不喜欢她,还要来招惹她?
明明不爱她,却要来控制她!
很好玩么?
燕星河眼中复杂一闪而逝,半晌后,他徐声道:“要成为仙门的一员,你早该知道,要放弃什么,不是么?”
没等司南星开口,他挺直了腰,复道:“仙门有事,我需要处理,七日之内,必然回来。走的这段时间,你好好照顾下阿月,不要让她受委屈。”
燕星河走了,只剩司南星捧着满地残尸呆坐。
让她受委屈?
司南星凄然一笑。
良久,她才回过神收拾。
她笑着抹去脸上的泪,心中告诉自己,没关系的,反正七日之后,自己已断情绝爱,和他燕星河再无瓜葛。
隔日,阿月雷打不动前来串门。
“星河哥哥怎么不在?他答应了要带我去春狩,猎一只五彩通天雀送我的。”
燕星河虽为剑仙,却并不喜欢滥用法力多造杀伐,对他而言,杀生为护生。
往常司南星杀只通灵妖兽都会惹得他蹙眉,可他却愿意为了阿月轻易打猎取乐。
司南星垂下眼,淡淡道:“宗门有事,他须得回去。”
“真是的,怎么不早说。”阿月发出哀嚎,“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他来呢。”
“南星姐姐,要不然……你陪我去嘛!好不好?”
“不好。”
司南星还要炼蛊,实在没那闲工夫陪她。
阿月一咬牙一跺脚:“都不陪我,那我自己一个人去!”
她骑着飞马蛊一溜烟跑了,司南星反应过来,忙去追她。
春日丛林,万物复苏,危机四伏。
阿月虽天资很好,却从不努力,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嘿嘿,我就知道南星姐姐你会跟来,你真好!”
见到司南星,阿月立刻上前来挽着她的胳膊,笑嘻嘻拉着她,去这个妖兽的巢穴探索,又荡到那棵古树上玩耍,时不时还手欠地招惹两只禽鸟。
司南星从前其实也这般活泼好动,但现在忘情蛊日渐生效,每日要受万蛊噬心之痛,她实在没什么精力陪阿月玩闹。
但为了阿月的安全,也只能强打起精神,看顾着她不要出事。
可正当她冷汗涔涔跟在阿月身后时,兽潮突然来了。
“南星姐姐,救我!”
阿月尖叫着,面前一只巨大的天阶苍鹰俯冲而下。
“阿月,丢掉你手里的蛋!”
司南星不顾身体疼痛,强使剑诀,可是强弩之末,剑诀一出反引起兽潮阵阵骚动。
眼睁睁那苍鹰顷刻间把阿月叼走。
如离弦利箭,再无踪影。
司南星陷入兽潮,花了好一阵功夫,才险险摆脱。
可她却并不觉庆幸。
料峭春风一吹,冷得钻心,她打了个寒颤。
现在这一耽搁,哪里还找得到阿月的影子?
而阿月深陷妖禽之口,她还能活得下来吗?
司南星死死咬住颤抖的唇,咬得鲜血淋漓,她恍若未觉。
不!阿月不会有事,她一定会找到阿月!
无关燕星河,这是她的族人,她一定会救阿月。
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忙用法术、蛊虫找遍山林的每一处。
又用传音蛊通知族人们,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回阿月。
可是,阿月还没找到,等来的却是燕星河的一巴掌。
“我不过离开一天,你就迫不及待带她去春狩。你就这么恨阿月,恨到要害她去死吗?”
燕星河冰冷的目光仿佛要一寸寸将她凌迟。
司南星愣怔了片刻,难以置信地望向他。她顶着鲜红刺眼的巴掌印,喉间涌起一口腥甜。
“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
可是回答她的,只有燕星河冰冷的背影。
他早就化成一道剑虹,冲天而去,寻找阿月去了。
竟是一句也不想听她解释。
滴答!
冰凉的液体滴在手心,不是泪,是血。
为了寻找阿月,她用了噬血燃髓的禁咒,反噬了。
司南星咬牙,硬压下伤势,转身去找人。
可当三日后,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躯体回到村落时,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笑闹的燕星河与阿月。
当她还在与妖兽浴血奋战的时候。
两人早就平安归来了。
可是这消息,却是老族长告诉她的。
他们……早就把她这个人忘在脑后了。
司南星浑身上下,血痕斑斑,五脏六腑被妖兽击打错位,漂亮脸蛋上也斜斜横亘着一道深深血痕。
狼狈得仿佛一条丧家之犬。
若不是她昨夜被那群妖兽围攻得伤痕累累,不得不撤退,可能就连老族长传音都顾不上看,还会继续寻找阿月。
她浑身冰凉地,施法掩去自己狼狈模样,转身便要走。
“南星姐姐!你怎么才回来啊?你去哪儿啦?”阿月出声叫住她。
司南星不答,黑润润的眼睛一瞬不瞬盯紧了她:“你说呢?”
“找我?用不着啦!星河哥哥一回来立刻就找到我了。”阿月嘻嘻扬了扬腰间一枚玉珏。
司南星怔了怔。
她知道的,那枚法宝,这法宝本是一对,唤作灵犀双珏。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一人持一枚玉珏,另一个人就算在天涯海角之外,也能轻易找到她。
心有灵犀,永不分离。
这法宝代表的,便是一双亲密无间的爱侣。
而另一枚,司南星一错眼,果然在燕星河腰间看到了那另一半。
她忍不住笑了。
好一个心有灵犀,好一对有情人。
“星河哥哥那一剑——嗖嗖嗖!可厉害了。南星姐姐,你见过么?星河哥哥用剑,怎么说来着——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我背得对不对?”
“诶……南星姐姐,你怎么不说话?”
阿月见她脸色冷淡,不禁也把声音压低,惴惴:“你在生我的气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怪我——”
“怎么能怪你?”燕星河拧眉,嗓音森冷,“要不是你身上带着通幽辟邪丹,早就出事了。”
所以,还是怪她了?
所以,即便找到了阿月,也故意不告诉她,就是在惩罚她了。
“她身上有通幽辟邪丹,那我呢?我在兽潮里浴血拼杀几度濒死,又该怎么算?”这句话,终究没有问出口。
司南星咽下喉间鲜血,满不在乎道:“随你怎么想好了。”
她转身离开。
这些天一直默默养伤喂蛊,和燕星河互不理睬。
忘情蛊发作愈发频繁,她似乎忘记了许多情绪,但心中却愈发安宁了。
直到昏礼前一日。
族长将南疆圣女的衣冠送来时,修改好的嫁衣凤冠后脚也到了。
圣女袍服是苍蓝底色,缀银饰如繁星,微微一动,便折射出粼粼波光,说不出的清冷高华。
嫁衣如火,绣的也是凤求凰的缠绵图样,红得分外炽烈,也与圣女袍形成了鲜明对比。
司南星失神片刻,将嫁衣收回纳戒之中。
只剩下最后一天。
明日,她就将在南疆最盛大的祭典上,成为圣女,从此守护南疆,忘却前尘。
这嫁衣,还是还给燕星河好了。
怎么说也有百年的交情,做不成夫妻,也好聚好散吧。
可是叩开他临时居所的大门。
房间里没有燕星河的影子,只有阿月一个人伏案写着什么。
“南星姐姐,你来了。”阿月抬起头,哀怨地咬着笔杆,“中原的字好难,学得好累。”
司南星不答,只问:“他呢?”
“给我留下课业就走了,好难……我每个字都认识,可是连起来就一点也不懂,南星姐姐,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司南星蹙眉,信手接过那张字帖,只见那力透纸背的字写着——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刹那间,耳边似响起万千炸雷。
司南星愣了好半晌,后知后觉的,感到蛊虫又开始密密麻麻地啃噬着她的心房,好疼。
她看着这首诗,看着看着,忽然低低笑出声。
早就知道的不是么?
这首诗本是一首情歌。相传,是当年摇船的异族姑娘看到了出游的中原君子,心生爱慕,便用异族语言吟唱起了这首歌。
一开始,君子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却被她歌声感染。找人翻译后,才知道她唱的是:“山上有树木啊,树木有枝桠,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可我爱你的心意你却不知道。”
他被女子缱绻的深情打动,上前拥抱住这个异族姑娘,接受了她的追求。
这是她学中原文化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首诗。
可司南星只说:“我不懂。”
将纳戒匆匆交给阿月,托她转交燕星河。
转过身来时,泪水已簌簌落下。
燕星河还记得么?
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兴冲冲跑去对着燕星河唱了好半天,末了,问:“小燕,你愿意做我的君子么?”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她对燕星河如是,燕星河对阿月亦如是。
他从不回答,因为他从来都不愿做她的君子。
一夜后,忘情蛊吞噬锥心之痛。心绪重归平静。
昏礼当天清晨,司南星身披苍蓝圣女袍服,佩银环,又庄重地将那张圣物傩面戴在了脸上。
昏礼是黄昏时举行,现在还未正式开始。
想了想,她还是决定和他们道别,并说清楚,她不嫁了,昏礼取消,联姻可以另择人选。
她施术唤出一面玄光镜。
可镜中映出的画面,却让她刹那间浑身冰冷。
因为阿月正坐在新嫁娘该呆的青罗帐子里,一身嫁衣红得刺目。
她举着团扇掩面,眼波跟帐外同样身披喜服的燕星河交汇,不胜娇羞。
郎情妾意,无言胜千言。
没有她,一切如常运转,甚至更添了一分喜气洋洋。
无数大能宾客聚集在此,很快有人发现了这道简单的术法,甚至循着玄光镜反追踪到了她的影子。
目光一触即走。
没有一个人发现,她才是原本的新娘。
司南星浑身颤抖着,固执地咬着牙,不让眼泪落下。
明明……明明她都已经放手了!
他们就这么迫不及待?
连通知她一声都不舍得,就这样换了新娘的人?
若非她已经答应成为南疆圣女,若非她是戴着傩面用玄光镜观察了情况,傻呆呆地去了现场……岂不是成了笑话?
燕星河,他好狠!
他就这么讨厌她?连一丝一毫都没有替她考虑过!
哈,哈哈哈哈哈。
泪水顺着指尖滴落,玄光镜关闭的那一刻。
燕星河浑身一震,似有所感,蹙眉抬眼。
司南星低眉,恰好错过了那道复杂的目光。
其后,似乎燕星河发来了几道传讯,可她也懒得看了。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意义呢?
君若无情我便休。
他自娶他的阿月,她自做她的圣女。
从此燕星河与她再不想干。
“圣女,祭典要开始了!”
丢掉过往一切。
再抬眸时,她目光重新坚定起来。
“带路吧。”
苍天之下,群峰之巅,族长、一众长老早已恭候多时。
正午时分,司南星迎着明媚天光,阔步走上祭坛。
族长手握竹杖,轻点她头颅:“天地苍茫,万物生长,皆循天道,法自然理,舍弃俗念,心如琉璃,明澈无瑕。”
“你可愿舍弃小我,背负南疆使命,承我圣职,守护这片土地,世代相传?”
司南星眼帘缓缓垂下,声音坚定而清澈:“我心所愿,无怨无悔。”
她拱手,接过那权杖。
霎时间,天垂紫气,地涌金莲,群山俯首,百川朝宗。
天边一只金色的凤凰破云而来,口衔香花,置于她肩头。
袅袅烟霞之间,众人齐声喝道:“恭迎圣女。”
司南星持杖,阖眸颔首。
永别了,燕星河。
从今以后,世间再无司南星。
只有南疆圣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