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密吗喽!”
事情不太寻常,这个表情包以闪电战的形式攻陷了每个年轻人的聊天框,不论职业、地域、圈层。以至于很多人在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就已经能联想到画面了。

原因?还不太清楚。
它是日后“吗喽文学”的鼻祖,也许斯密吗喽自己也没想到,后来它成为了年轻人的“精神图腾”。
几乎是同一时间,相比于画风潦草的吗喽,卡皮巴拉(水豚,英文的音译)以一种更讨人喜欢的方式出现了:

作为表情包,它们可爱、好用,但它们影响的不仅是我们的聊天框。
你发现了吗?在彼此间互相以猴子、水豚表态和回应的时候,渐渐地,我们的心态和处事方式,也被这两只电子宠物影响了。
简单来说,是这样的:
不管你是指纹、面部、还是 APP,在按下“打卡上班”的时候,我们期待能变成吗喽——成为无情的打工人,拒绝内耗、直接发疯,认清自己平凡的位置,扔掉包袱,屏蔽 PUA,一干到天明。
终于下班了,我们则希望变成卡皮巴拉——作为情绪最稳定的动物,关于水豚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死就死了,没死就活着。”这句话准确吗?不重要,重要的是水豚已经成为我们的精神寄托。“上班已然很累,下班之后,我变成卡皮巴拉,不因任何来搞我心态。”
我们当然不知道猴子和水豚真正是怎么想的。但当大家开始以这两种动物所代表的状态,比拟自己的状态时,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
也许这是第一次,人类从表情包中获得了某种“精神力量”。

image:PIA RIVEROLA
1.
“我下班的时候,还有七个活排着队需要她做。”一位编辑偷偷告诉我,让我看看能不能帮忙调整一下工作量。
我尽力了,因为这位女孩并不直属于编辑部,尽力的结果就是,从下班还需要做大概七个项目,变成大概三个。
本质上没有变化,不是吗?
一个周五,下班,我恰好遇到了她,这位需要同时多线处理许多项目的、新来的设计师女孩。
事实上我有点紧张。那段时间项目很多,这位职场新人顶着超额的工作压力已经有些时日了。当我和她一起踏进同一间电梯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被回避、或者被置之不理的准备。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如果我刚经历了这么高强度的工作,我也许会这么做。
“你还 OK 吗?最近项目真的多。”
“还...好吧?”她有点疑惑,看起来这个问题是我预设过度一样。
电梯间里莫名有一股酒味。
我才发现她手上拿着的是公司刚发的啤酒,突然意识到 Steppy 的大多数女生还挺喜欢喝酒的。她礼貌性地抿了一口,没有疲态、没有不爽,看起来已经计划好了接下来要去那里玩。
确实很扫兴,随后我不得不提前和她透露,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客户又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设计需求,需要她下周做掉。
“哎呀,”她笑着说了一句,“吗喽的命也是命。”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里听到这句名言。
一楼到了,她悠悠然地走了,起码现在还不用变成吗喽,她尽管享受接下来的 Friday Night 就好了。

image:PIA RIVEROLA
从编辑的角度来看,坦白讲这件事不好写,起码它很容易看起来像又一个心累的职场故事。我很清楚也不喜欢这种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也是一只吗喽),每一次因为不可抗力需要让编辑或者其他同事多加班我都会觉得别扭,就算这件事与我无关。
同样的感受却在电梯里被她的回应消解了。她的反应里有一种苦中作乐的底气,让我意识到,其实很多年轻人并没有那么易碎。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是一个值得发愁又处处感觉到对立的时代。
一个月前,广西的一所高校招聘会上,在操场上面试的 HR 当着学生的面扔掉简历。在简历掉进垃圾桶之前,站在桌对面的女生刚刚冒着细雨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挤到台前递上自己精心排版的个人履历。
后来这个女生在垃圾桶翻找简历的照片被传到了网上,“简历是彩印的,很贵,扔了怪可惜的。”

image:TikTok
现实如其所是。我们一边需要检讨自己是不是“没有脱下长衫”才找不到工作,一边需要经历在雨中翻找简历的奇幻事件。在这个巨大复杂的系统里,两种不同方向的言论都有道理?但这个时候认清事实好像并没有用,毕竟它本来就是矛盾的,困惑依然,我们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表情来迎接当下。
但表情包是有的。
我们开始用吗喽文学来屏蔽这些矛盾带来的内耗,当下的情况是:吗喽不仅因为潦草丑萌而成为大热的表情包,配上合适的文字之后,我们开始在工作的缝隙中学会自嘲——
不论什么时候,自嘲都比哀怨更有用。
只是意外的是,这是一只吗喽无形之间教会我们的。
2.
我的吗喽表情包,几乎都是从朋友 D 那来的。
可以说我和他还是因为这个表情包才重新熟络的,我试着滑到聊天框的最顶端,上次聊天是 2021 年。
D 是我的中学同学,在认识的这十多年里,他自始至终都是那个一群人里话最少的人。D 不怎么上网,他的网络纪年大概处在:能勉强理解“社恐”的意思,但完全不懂“i 人”“e 人”是何物。
“你这几年都在干嘛?”在几乎没有联系的两年后,我问他。
两年里他有什么样的变化?很难说清楚,但他更放得开了,开始和我讲他那长长的故事,没有目标的工作,不太体面的工资,刚刚认识不久的女朋友。他说他每天下班雷打不动骑着小电驴去球场,一个人打球。
白色的聊天气泡框中时不时夹杂着几只吗喽。

当时他发给我的表情包
顺着这种自我解嘲,他好像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感觉你比以前能说好多。”
D 接着又给我回了一个吗喽表情。
当然,他还是社恐,还是 i 人——几天后我们见面,他依旧习惯避开眼神接触,说话的时候脸别过一边。
又有什么关系呢?起码他开始抛出内心的郁结,担心说得太忘情,他就发一个吗喽表情包中和一下。
像是一种迂回的自我和解,毕竟没有人能从社恐硬掰成社牛,从 i 到 e。但不管你的 MBTI 落在圆盘上的哪个位置,你可以同时是 i 人也是吗喽,在它的掩护下为自己发疯。

image:PIA RIVEROLA
3.
我们同样期待自己变成卡皮巴拉,准确来说,这种成为水豚的念头会在下班前的几分钟里变得格外强烈。
周周想起她工作第一年的时候,“喜欢在小红书上看早下班攻略。”
“把口红钱包钥匙放进文件夹里,下班的时候遇到领导会以为你是去送材料。
走之前放一杯冒气的热茶在桌前,所有人都不会觉得你下班了。
在工位椅子上披一件外套,看起来就像临时离开一样...”
她如数家珍一般地背起了贯口,我不得不申请暂停,好好消化一下。“说起来也挺好笑的,”她继续说“其实就是按时下班,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心理负担就这么大。”
“所以你真的试过?工位上披外套?”
“真试过...”

image:PIA RIVEROLA
一年之后,她渐渐意识到那些不自在都是“自己加的戏”。“每次快到六点,你动一动椅子都感觉别人在看着你,但你信吗?”她的语气异常平缓,“退一万步讲,真的有那种奇怪的规则,为什么要让自己掉进那种氛围里?”
准点下班,利索地收拾好东西,周周走出写字楼时往往还没到人最多的时候。但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把东西藏在文件夹里,不用倒热茶,不用披着外套,她说自己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水豚化了,“心里盘算着今晚需要买回家的特价菜。”
“我不想刻意对抗点什么,无论是办公室政治还是职场潜规则。只是不在乎那么多东西,你下班的心态会很平静,让下班还给下班,不是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呀。”
周周的微信头像是头顶三颗橘子泡澡的水豚,她发来这段话的时候,有种恰如其分的既视感。
“情绪稳定,没什么好紧张的。”我们都期待这种水豚心态有一天能降临在自己头上。
真正成为水豚之后,周周即便是在双休日也不会把手机调成静音。
她的手机在桌上响起,接着自动亮起屏幕。这一套连招已经让我下意识有点紧张了。她看出了我的反应,“之前我也这样,不对,所有人都这样,总担心是工作。”她把手机屏幕反扣在桌子上,“我现在已经免疫了,其实就是无所谓,它是与不是,在现实中并不会真的影响我的周末。关键是能不能过得了你心里那关。”
她发了一条动态,既没有设置分组,也没有“三天”。在她的朋友圈里,可以看到从高中到现在的照片,都挂在那,所有人可见。

image:PIA RIVEROLA
4.
今年,《纽约客》的感恩节封面再一次把“手机过节”这个问题提上议程。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封面做得并不好,至少题材太老套了。但它也再一次地把一个显然的问题拎了出来:人与人之间愈发疏离,今天如此,日后更甚。
我们必将越活越像单个游离的原子,通过手机、网络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会当面麻烦别人,用一种更文绉绉的说法就是——社会原子化。

image:THE NEW YORKER
这是新一轮的常态。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评价“好与不好”,因为我们就是其中的原子。在这个孤独的设定里,我们自然而然会察觉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给内心搭建一个安全边界。
我们一直在尝试划出这道边界。几年前,我们被人称为后浪,暗示着要形成一股奔涌的势头;再后来我们和社恐、躺平绑定在一起,意味着象征性的放弃;而现在我们更希望成为吗喽、水豚,以期在现实中拥有一个更巧妙的站位,不过分消极也不委屈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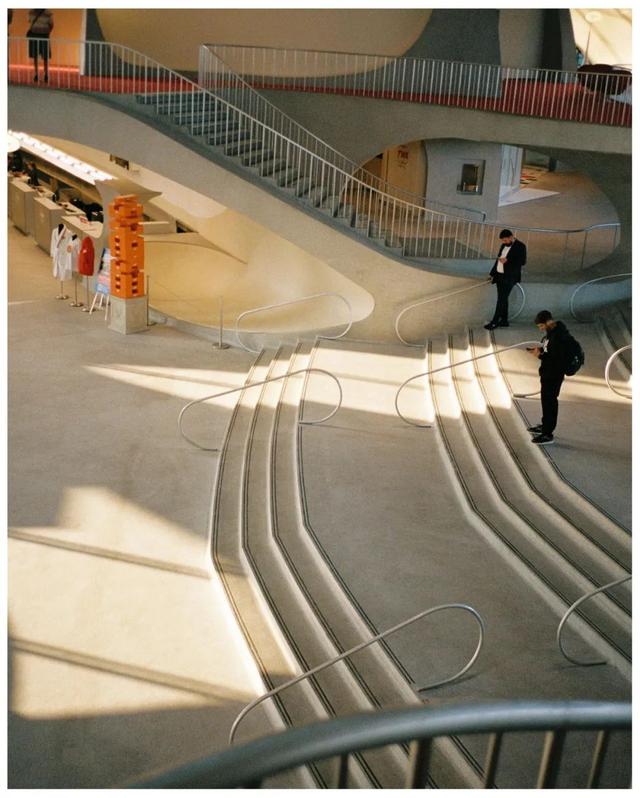
image:PIA RIVEROLA
我们尝试在这两种动物身上找到恰如其分的答案。吗喽、卡皮巴拉,借用它们的意象,试图以不再回避的姿态,面对现实抛来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