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对计算机系统实施诈骗”本身能否构成一般的诈骗罪?
 网络盗窃罪与诈骗罪界限分析
网络盗窃罪与诈骗罪界限分析在我国刑法构架下盗窃罪与诈骗罪是具有很大差异性的两种犯罪行为类型。

这两个罪名尽管都在在财产类犯罪的体系中,但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模式时具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这两个罪名在刑法分则中的体系地位也并不相同,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结构存和行为模式也存在不同,导致二者具体的犯罪构成有所不同。
分析两者不同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模式或者说是行为结构。

盗窃罪的行为模式是:首先需要犯罪行为人的主观行动侵犯了财产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财产。
并且这种侵犯行为是在财产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没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意思表达的情况下进行,表现形式既可以是秘密窃取也可以是在公众面前。
在这这行为过程的关键是是受害人并没有处分自己财产给侵犯人的意识。

而犯罪行为人对权利人的财产进行侵犯,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变为自己所有更改了财产的占有使用状态,可以将其归为“他人损害”型犯罪。
由此可以理解为当行为人出于非法将权利人的财产占为己有的目的,通过非法的手段实施破除权利人对其财产的合法占有行为,并且对权利人的财产构建起新的占有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财产的实际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实际并没有处分财产给犯罪行为人的意思。

当行为人对财产非法构建占有关系并且将这种占有关系持续一定的时间时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盗窃既遂。
而诈骗罪的行为模式或者行为结构是,禁止行为人通过误导权利人的方式,或者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或者采用假冒身份的手段向财产的权利人或者管理人提出给付财产的要求。
其行为致使财产权利人信以为真主动且具有真实意思表达地将财产处分给行为人最终导致财产的减损。

根据这一个行为过程,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的诈骗行为的基本构造是:
行为人对财产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进行欺诈行为,被害人因为欺诈导致自己陷入认识误区,被害人基于被误导的判断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财物的所有者因此失去对财物的所有。
从被害人自主交付财产的角度可以将诈骗罪归为“自我损害”型犯罪。

当权利人因为受骗将自己拥有或者管理的财产给付给行为人归其占有时,即可认定诈骗既遂。
因为盗窃罪和诈骗罪在行为模式上存在不同导致两者之间的犯罪构成不同,同时也决定了盗窃罪属于非自我损害的犯罪类型而诈骗罪属于自我损害型的犯罪类型。
此外在犯罪体系中,我国学者同样认为,盗窃罪与诈骗罪在刑法分则的构架下是不相容的具有各自的特点,因此两个罪名构不成想象竞合。

前文分析了在现实中盗窃罪和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和不同之处,那么当场景切换到网络空间中二者的区别还是一样的吗?
笔者认为,在网络空间环境中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区分在二者固有的不同之处外更具有复杂性。
复杂性的关键在于网络空间的载体——计算机信息系统能否作为诈骗的对象。

我认为,在网络空间的环境下如果行为人实行犯罪行为的对象是传统类别的计算机系统,由于执行单一固定代码,此种计算机系统并没有处分权限。
在面对指令时进行的反应仅仅是一种计算机程序性代码所造成的执行命令的行为,所以从没有处分意识角度,当行为人对计算机系统实行窃取或者骗取行为时,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当行为人进行窃取或者以假象骗取计算机系统获得财产性利益后,又通过将获得后的财产利益作为手段展现给被害人,被害人据此作出处分行为时此时应当认定为诈骗罪。

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系统或者平台被人为欺骗而非法获利的情形发生,对此司法实务部门在认定具体情况的时候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
这一行为有的被认定为诈骗罪,有的被认定为盗窃罪,争论的焦点在于“计算机系统数据平台是否能够作为被骗对象”。
对此,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条文来说我们不能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需要我们针对不同的案件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讨论计算机系统被骗能否成立的问题,实质上还是研究犯罪行为人是否对计算机系统背后的自然人实施了诈骗行为,实际权利人是否因为受骗交付了财产。
通说认为自然权利人“由于犯罪行为人对其进行欺骗,权利人因为错误的认识自主的处分了自己财产”是诈骗罪最本质的特征。
真正权利人可能会受到欺骗,但是执行程序命令的“计算机系统”本身并不具有意思表达能力而不能受骗”。

我国的刑法分则体系中也有信用卡诈骗罪,属于普通诈骗罪的特殊情况,这一罪名以财产性利益或者财物为保护的对象,但是在保护的实质方面和普通诈骗罪相同。
即对财产关系的一种保护,并非是对处理信用卡的计算机系统的保护,所以计算机系统不能被骗也能成立信用卡诈骗罪。
另外,关于针对以类似计算机电脑的计算机系统作为犯罪对象实施诈骗行为时应当如何认定,我国刑法学界也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以计算机系统作为犯罪手段进行非法获利行为并且获利的,被认为构成盗窃罪。
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人在拾取不属于自己的信用卡后在ATM机上取款的,成立盗窃罪。
理由在于持他人的信用卡在计算机系统上取款的行为,属于使用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得财产所有人的财产,所以应认定为盗窃罪。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快速发展有理论认为是时候考虑肯定高级计算机系统有着被欺诈的概率。
也有观点认为,对具有搭载高级算法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人实施欺诈,可构成诈骗罪。
因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越来越成熟,智能计算机系统人已经可以替代人类从事一些固定程序的劳动。

从某种角度上说计算机系统在具有高度复杂的处理系统下具备了人类所有的思维,甚至在某些场域下比人类处理的更加理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计算机系统能够被骗确实存在着现实可能性。
对于以上观点,笔者赞同计算机系统不能被骗的观点,理由在于根据授权说理论,假使财产所有者或者管理人支配其所有或者管理的财产是依据其授权的范围。

此时财产处分人有权利处分财产,这种情况多发生于三角诈骗的情境下。
此时行为人对被授权人实施诈骗成立可以成立诈骗罪。
但是,如果现实中处分财产的受骗人处分的财产在授权范围之外处分财产,这时在超出的范围内受骗人就没有处分权,达不到诈骗罪的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成立盗窃罪。

由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计算机本身无论外观看起来再怎么智能,其终归不能超越管理者对其程序的设定和固定操作指令的授权。
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意识,不能与其他人进行主观意思的表达,即使具有交易处置功能的高级计算机信息系统,也并不具有对财物的自主处分权。
其本身不具有任何的自主意识,虽然具有被授权的权力外观,但是实质上并没有取得财产权利人的真实性处分权的授权。

因此,具有交易功能的智能机终端在能够认定支付或者兑换的情况下仍然不能被认定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类似诈骗的行为时应当被认定为盗窃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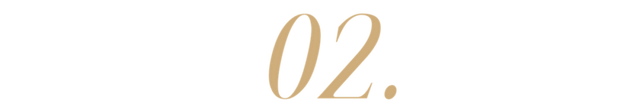 刘某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犯罪对象的结论
刘某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犯罪对象的结论根据前文对相关理论的分析,结合本案刘某强通过编写程序攻击平安集团旗下的“知鸟APP”学习平台获取学习积分。
刘某强盗窃案中所指向的犯罪对象“知鸟APP学习积分”虽然具有经济层面的金钱价值。

但是不能进行自由转移和占有,只能存在于刘某强本人和平安集团之间一对一的转移,不能够产生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流通,不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特性。
所以“知鸟APP学习积分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财务或者财产,只能属于少部分意义上的财产性利益,进而也不属于刑法所要保护的财产范畴。
反之,学习积分产生于计算机系统,“知鸟APP学习积分”作为平安公司旗下平台的活动奖励,显然是具有用户获得奖励意义的数字符号。

这两种数字表示需要输入计算机系统中才可以进行处理,是一种交换表达介质。
根据前文对学习积分应当属于刑法所要保护的一种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可得出刘某强盗窃案中的犯罪对象“知鸟APP学习积分应当被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刘某强在非法获取学习积分后,以学习积分为筹码通过注册虚假账号自己与自己游戏骗过计算机后台的信任获取的“游戏T点”属于游戏币的一种。

因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以及审判机关对其应当属于财产性利益无异议,所以本案中犯罪行为人后面的几个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对象“游戏T点”应当被认定为刑法所要保护的财产法益。
 刘某强在本案中的犯罪数额为人民币
刘某强在本案中的犯罪数额为人民币21万元根据前文对本案罪名认定的分析,本案中刘某强的犯罪数额应当分别认定。
刘某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犯罪数额应当为其给平安集团造成的财产损失数额即38.98万元人民币。

刘某强构成盗窃罪其犯罪数额为21万元人民币。
对两个罪名应当分别认定,数罪并罚。
因为根据刑法中关于罪数的理论,行为人的不同行为触犯不同的独立罪名的,应当数罪并罚。

并且根据我国目前对于牵连犯的处断原则问题上,在有刑法分则中关于行为人数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应当数罪并罚的特殊规定下应用数罪并罚的原则。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适用从一重处罚的原则。
司法实务部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全面把握行为人数个行为的基础上认真分析行为人数个行为之间是否具有方法与目的关系或者原因或者结果的牵连关系。

在本案中刘某强实施非法获取学习积分的行为与其非法获取游戏T点的行为两者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构成了牵连关系。
属于刑法理论中的牵连犯理论,应当采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
从整个案件考量,刘某强非法获取平安集团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给平安集团造成的财产损失是38.98万元。

根据两高解释中规定的数额标准,刘某强给平安集团造成的损失以达到特别严重的情形,在量刑标准上应采用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刘某强在案件中第二个犯罪行为构成的盗窃罪的犯罪数额是21万元人民币。
根据刑法对盗窃罪数额的量刑标准,这个犯罪数额的定性为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综合两个行为所触犯的两个罪名的严重程度,在本案中刘某强前后两个行为构成牵连犯应采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采用盗窃罪的犯罪数额进行认定。
从另外一方面分析,虽然在刘某强第一个犯罪行为即非法获取知鸟学习积分的行为在财产权外观上给平安集团造成38.98万元人民币的损失。
但是在案发后平安集团及时冻结牢刘某强未来得及使用并转换为游戏T点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平安集团实际上损失的人民币为21万元。

在网络空间中盗窃虚拟财产的数额如何认定?
笔者结合网络空间场域的特殊性和行为人实施网络犯罪的目的性去解释网络空间情况下盗窃类似本案中游戏T点这一虚拟财产的认定问题。
网络盗窃犯罪是传统盗窃犯罪在网络空间领域下的扩展,此类犯罪具有犯罪手段的程序复杂性,犯罪对象的隐蔽性,犯罪范围的超空间性的特点。

这些网络空间的特性使得网络犯罪相对传统财产类犯罪具有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节点的复杂性。
由于网络空间中的财产具有占有权和实际控制权分离特征,对这种非实体性财产的占有并不代表能够实际控制财产或者排除他人占有财产。

例如,行为人实施盗窃银行卡的行为,在取得权利人的银行卡甚至在知道密码的情况下,此时权利人及时挂失或者修改密码。
那么行为人虽然占有了银行卡这个物体本身,但是却对其承载的网络空间财产却失去了控制。

根据这一特点,犯罪行为人在网络空间中实施盗窃犯罪过程中行为人取得了暂时性占有了虚拟财产并不代表其能够实际拥有虚拟财产。
网络空间中的虚拟财产的这一属性则可能导致行为人在网络空间中构成盗窃罪数额的真实认定与传统的以实体财物作为犯罪对象的盗窃罪的犯罪数额认定具有不同之处。

根据这一特性,笔者认为网络盗窃罪数额的实际控制说理论更加符合发生在网络空间情况下对发生盗窃罪这一财产类犯罪的认定实际情况。
所以综上所述刘某强的犯罪数额应当被认定为21万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