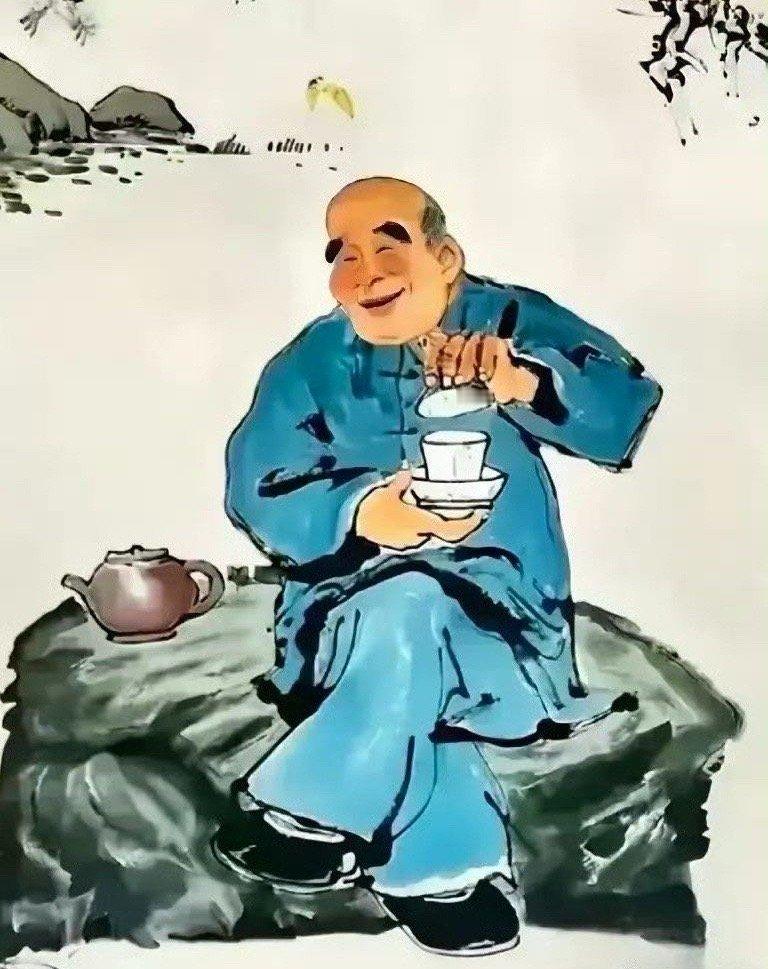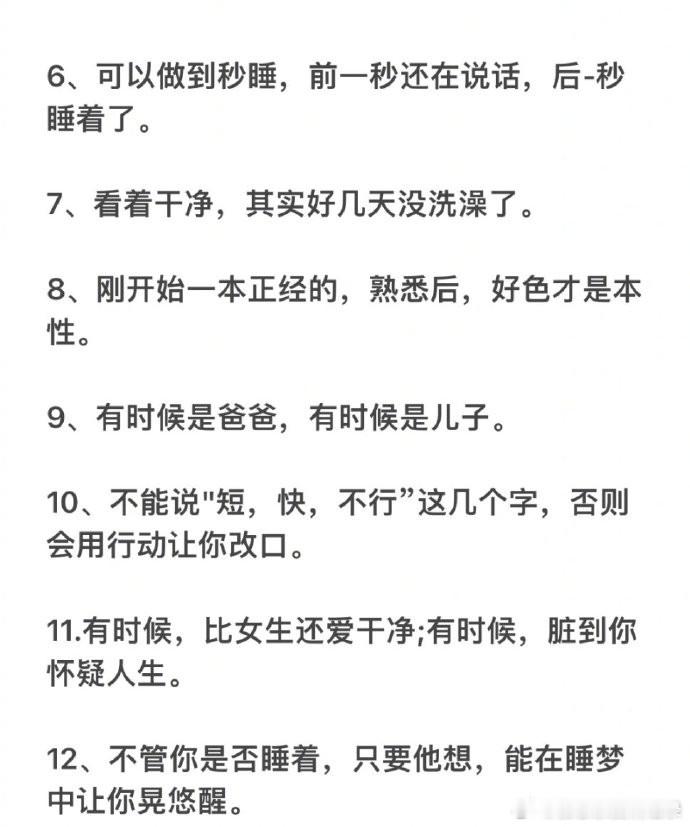所以他看不看得上我,我其实不在意。
我是谢母百金买的瘦马。
秦淮畔的妈妈将我夸得绝无仅有,说我是所有孩子里最出挑的。
谢母看着我安安静静,却不明白这个出挑从何而来。
妈妈叫我扮出娇憨懵懂的清纯情态和媚而不俗的勾人模样:
「这秦淮十里,你再挑不出这么个人才,我当女儿一样清白干净养到现在,媚骨天成又没脂粉气,凭客人喜欢什么样,栖月都包君满意。」
见谢母不语,妈妈笑道:
「听说大郎前阵子沙场立功,可是谢大将军要个床上伺候的人?」
谢母摇摇头,妈妈又问:
「那是二郎预备苦心读书,蟾宫折桂,要个娇娘红袖添香,知冷知热?」
谢母仍不语,啜了口茶:
「两位都要她伺候。」
妈妈愣住了。
谢母却笑着拉过我的手:
「知冷热,要你伺候好大郎,他这么些年身旁没人,指不定哪一日将你纳了去。
「大郎常不在家又惦记他这个弟弟,既然你是个识文断字的,把二郎从锦绣堆里拉出来,能劝他好生读书考功名,大郎也谢你。
「若是大郎瞧不上你,你能劝好二郎,别说赏银,身契我也还你。
「做妾这事别对外说,他看不上你还臊得慌。」
谢母是续弦,虽不是生母,却处处为这两个儿子打算。
我点点头。
我就在谢府住下了,说是谢母远房的亲戚,灾年逃荒来投靠谢家的。
当下我已经盘算好,先将纨绔的谢时景劝上读书的正途,等到大郎谢识礼征战回来,那时我再摸清他的脾性,讨好他。
毕竟能做个妾室,已经算是好命了。
2
这三天,谢时景托着腮看我半日,半个字也没写。
他也算个败家子,虽不看书,半夜却颇费烛火,把他别院点得白昼一般。
再过些日子谢识礼便要回京了,这位沙场上的不败将军是位严苛兄长,对谢时景的课业看得很严。
谢母为谢时景请了先生,又叮嘱我看着谢时景,做不完课业决不许他出去鬼混。
身子不出去鬼混,却可以坐着出神。
我翻了他从前写的字,却是飘逸遒劲。
「写得一手好字,为什么不考功名,走正途?」
「那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耗着?」他将我打量一番,笑道,「难道是对我情根深种?」
「为了荣华富贵。」我将书放在他眼前,「二少爷写完这篇的注疏,我便瞒着夫人,同意你出去半日,但不许赌。」
「一点也不像个女子,古古板板,像个老夫子。」谢时景忽然凑近,看着我一身素净的穿着,嫌弃道,「都说贤妻美妾,你这样不懂风情的女子,会被夫君厌弃的。」
我哑然,秦淮畔的女子不懂风情,那天下何处的女子懂风情?
可对谢时景这样的人风情,无异于对牛弹琴。
「乡巴佬,给你瞧瞧什么叫美人。」
他悄悄拿出一本册子,写的是群芳谱。
画师功底相当深厚,将美人娇怯情态画得栩栩如生,如九天仙女一般。
如果不是有许多熟脸的话。
「当年随吴漕司秦淮夜游,恰好是百花节,美人出游,吴漕司托我画了这一册。
「这位抱着琵琶,一脸愁容的是湘妃,最令人动容的是她送别客人时,眉间微蹙,泫然欲泣的模样。」
他大概不知道,湘妃一脸愁容是被客人打骂,客人将烧了的烟烫到了她最宝贝的琵琶上。
「这位是丽君,娇蛮的样子如扎手的玫瑰花儿,惹人怜爱。」
他应该也不知道,丽君性子柔弱沉静,偏偏眉目明艳,客人最喜她扮刁钻性子,为自己拈酸吃醋。
我心里不是滋味。
想到她们,我的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喂……我开玩笑的,你别哭呀……」
见我哭,谢时景顿时慌了手脚。
「二少爷是在跟我炫耀你猎艳颇多?万花丛中过?」
「不是,只是船上匆匆一面,觉得这些姑娘各具美态,我感慨红颜命薄,所以画了这本……」想必是常常翻看,他轻易翻到那一页,「不信你看这幅,我最喜欢的是这位,娇憨纯净,可惜乘船时擦肩而过,并未得见。」
画上女子只有一个背影,她长发未梳,如瀑散下,趴在亭台边,手上扇子随意拨弄池塘上点点流萤。
因为画师偏爱,所以着色最多,女子身旁一池荷花如星捧月,连发丝裙袂都翩然当风,毫无矫饰。
上头题着一行小字:瑶池仙子,遇安敬拜。
遇安是谢时景的字。
我愣住了。
因为画中人是我。
「你要是有她三分神韵,小爷我肯定……」又想到我刚刚哭过,谢时景忙说,「你要是不管着我课业,也勉强及她二分吧。」
我哑然,忽然想到他的课业:
「这个女子有些眼熟,当初北上时我似乎见过。」
谢时景猛地坐直了身子:
「当真?」
「如果你能把这篇注疏写出来,我应该能想起来一点。」
3
这半月的课上,谢时景确实认真起来了,夫子不住地赞他。
他同夫子读书时,还要我做了许多吃食送去。
夫子是金陵人,很吃得惯我做的桂花糖藕和甜芋儿。
夫子吃了甜的,连戒尺都轻了许多。
倒是谢时景总是挑三拣四,不是说太甜就是太淡,要么就说桂花不香。
桂是好桂,糖是好糖,连这手艺都是当初妈妈让金陵最厉害的厨娘教的。
谢时景只是看我不爽罢了。
直到半月后,他颇为得意地将夫子圈点的注解递到我面前:
「瞧瞧,只要小爷想,一日千里也不是问题。」
我瞧着注脚,他却讨赏地问我:
「那位姑娘现在何处?」
「上次逃荒路过,听旁人说她遇着良人赎身了。」
「你怎么知道是良人呢?」他狐疑道。
我正怔住,不知如何说。
「你也是听别人说的吧。」谢时景很快明白过来,他颇为自得,「小丑月,你不懂男人,他定是看仙子姿色才见色起意,那叫色胚歹人,要说良人,我谢时景才算良人。」
……这可是你自己骂的。
「只可惜没能与她相识。」谢时景看了我一眼,又颇为扫兴地摇摇头,「怎么监督我课业的是你,若是那位仙子,我明日便能蟾宫折桂。」
……行吧。
正说着,谢时景忽然用扇子抬起我的下巴,仔细打量:
「不过也勉强够用。」
「什么?」
「后日是崔太傅次子崔昊的生辰,到时候人人都带美人赴宴,我总不能一个人去。」他想了想,「你得打扮打扮,不要丢我的脸。」
他自说自话地念着我穿着素净,定是母亲刻薄我。
「夫人她很好……」
听我这么说,谢时景的脸忽然冷了下来。
似乎很不喜欢这位后母,他冷哼一声。
谢夫人同意我与谢时景赴宴,还叮嘱我好生打扮,不要给谢家丢脸。
谢时景别具审美,为我买了衣衫首饰。
许久不曾妆饰,我拿着胭脂竟然有些生疏。
谢时景托着腮看我半日,终于看不下去:
「别糟蹋小爷的东西。」
他用手中那支笔,蘸了些胭脂,抬着我下巴仔细地描。
他极善丹青,所以手极稳。
瞧他这么认真,我倒有些不自在起来。
满室灯辉,映着他眉眼。
他专注地看着我的唇,他长睫潮黑,认真时眼上像停了只纤长的蝶,蝶翅随着他的呼吸轻颤。
不知是他有意,还是时间真的过得慢了。
他一点点靠得很近,可是手上的笔却停了,像是欣赏自己的杰作。
近得我连他呼吸和睫毛的轻颤都感受得到,近得我甚至能听见他的心跳。
越是专注,他眼中越是有一点疑惑和迟疑。
我怕他无端想到什么,忙开口:
「画好了吗?」
这一语像是点醒了他的梦境。
他的手抖了一下,胭脂又点在了我的唇边,嫣然一点小痣。
「真笨,还不如我画的呢。」
「知足吧,你这根朽木,费了我好多心思雕琢。」
夏日薄绿衫,流苏金步摇,俨然一个清丽美人。
他想了想,又递给我一柄轻罗小扇。
我心虚地拿着扇子,藏在身后,生怕引发他无端联想。
「勉强不丑,能跟船娘比一比吧。」像是完成了得意之作,谢时景心情大好,「走吧。」
画舫上灯火通明,崔昊请来了这花街上最负盛名的歌舞姬。
其实大可不必请什么舞姬,各家公子的女眷暗暗争艳。
有人会西域传来的胡璇,在金盘上翩跹如蝶。
有人擅吹奏,一曲笛音风雅至极。
从那一次看见画册起,我生怕谢时景把我和画中人联想到一起。
所以从入席开始,我便低头专注地吃东西。
「喂,小丑月,你会什么?」谢时景悄悄凑近,低声问我。
「啊?」
我咬着半个饴饼,后知后觉抬起头,才发现几个舞姬靠在公子们怀里,指着我暗暗地笑。
「背家训可以吗?不然给大家起锅烧油做个拔丝果子?」
看我鼓起的两颊,谢时景叹了口气。
我讪讪地放下手中的饴饼,递给谢时景:
「那你尝尝这个,好吃的。」
一众公子哥儿也憋不住了,终于笑倒在美人怀里。
「……我害你丢脸了?」
我以为素来不肯落人下风的谢时景高低要臊我两句,没想到他竟然勾起嘴角略笑了笑。
我一度怀疑我看错了。
「这个也好吃。」他递过来一盘藕糕,颇有些无可奈何,「吃吧吃吧。」
我将信将疑地接过,还不忘掰开一半给他。
「本以为能让二少爷收心的女子是个妙人,却是个绣花枕头。」崔昊叹了口气。
歌舞正酣时,月亮也升到最高处。
帘外丝竹声至高潮处,却忽然静了下来。
倏忽一阵破空之音,船四角的灯笼皆暗了下去。
「有刺客——」
女眷们尖叫,那河上的灯已经灭了。
月藏进晦暗的云层,一丝光亮也无。
刺客们是冲着崔昊去的。
女眷们衣裙复杂,踩着衣裙倒在地上,男人们只顾着各自逃命,任她们自生自灭。
混乱间,谢时景抓着我藏进船下货仓里。
货仓阴暗潮湿,有木头长久浸在水中,朽烂的味道。
谢时景受不了这个味道,我将衣袖递过去,那是下午时我熏过的,有一点蘅芜的药香,能遮住霉味。
谢时景好受了一些,他抓住了我的衣服,绣花的针脚刮在我的皮肤上,有一点令人发痒。
头顶还有嘈杂的声响,但是渐渐远了些。
黑暗中,我察觉到谢时景的手紧紧攥住了我。
他在紧张,不同寻常的紧张。
我将手轻轻放在他的手背,没有平日里的嫌弃,他顺势靠在我肩头,低声喘着粗气,几次擦过我的脖颈。
黑暗中,听觉和嗅觉被无限放大。
他喘着粗气,双唇却是冷的。
不对劲,很不对劲。
我忽然想到素日亮如白昼的别院。
难道他怕黑?
我试着抽开手,谢时景却紧紧贴着我,不肯松开一丝力气。
一点不像平时那个嫌弃我嫌弃得要死的谢时景。
「二少爷闭上眼,栖月去点灯。」我小声诱哄。
谢时景顺从地闭上了眼,却不肯放开我。
船舱底下是暗的,水流声和呼吸声清晰可闻。
「时景,窗外有荷花,开得正好,我们可以摘一捧回去养在书房。
「荷花丛里有流萤,可惜我抓不住,不然一定要你知道什么叫囊萤映雪。
「月亮很亮,船慢慢地晃,我们要去远一点的湖心看月亮。
「湖心栖月,那里的月色最好,亮澄澄地映在湖上,有零星的星星,就像糖水藕里的桂子。」
谢时景的呼吸平缓下来,他想睁开眼,却被我遮住,我诱哄道:
「还没到湖心,再等等。」
不知过了多久,外头已经静了下来,我却不敢轻举妄动。
静下来,我才察觉到小腿和左臂一阵剧痛,可能是方才逃跑时被什么割伤了。
忽然船略晃了晃,我疑心是不是撞上了什么,正要探身去看。
眼前的门板已经斩断,刀风堪堪擦过我的鼻尖。
那人背着月色,月光照见他冷峻的眉眼。
只是一面,杀气就如最锋利的剑瞬间出鞘,带着北境的厉烈朔风叫人窒息。
察觉到有人,他的长剑下意识抵在我的喉头。
我摇摇头,冲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谢时景已经靠在我肩上睡着了。
看见谢时景安然无恙,他的脸色缓和了下来。
借着月色,我才发现他与谢时景七分相似。
他瞥见了我衣裙下的血,皱了皱眉,将一条干净帕子递给我。
他背过身去,我将裙子撩起来,却犯了难,因为我另一只手也伤了。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指了指垂下的手臂,又指了指靠在我怀里的谢时景。
他一怔,竟然有点无措,握着帕子,好像那轻飘飘的手帕比他手上半人高的剑还重似的。
我轻声说:
「我救了你弟弟。
「所以你要帮我。」
他低下头,每碰到我小腿的皮肤一下,都像触电一般轻轻缩回手。
「很疼,你轻点。」
我皱着眉,他低头闷声帮我包扎。
昏暗摇晃的船舱里,我借着一点月光仔细看他。
他人长得高大,我不算瘦,可小腿在他宽大的手掌中竟然如新藕一般小巧。
他是个武夫,常年握刀剑的指腹粗粝,刮过皮肤有些痒。
若说谢时景带着一点纨绔的少年气,眼前这人却带着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戾气,一个眼神便能止小儿夜啼。
看来这位谢家大郎谢识礼,可比谢时景难对付多了。
「还有这里。」
谢时景枕着我右肩,谢识礼借着一点月光看我左臂的伤口。
他碰到我的手臂,我疼得吸气。
谢识礼却毫不怜香惜玉,看着熟睡的谢时景皱眉道:
「你轻点,别吵醒他。」
???
看来京城人说的,谢识礼偏疼这个弟弟是真的。
「……会留疤吗?」我有些担心。
「衣裙盖住,看不出的。」
「可是你知道啊……」我有些懊恼,「以后我穿裙子,遮住了你也知道,我未来夫君也会知道,裙子和衣服底下……」
他手忽然一顿,正色道:
「……我不会乱想,你放心。」
饶是昏暗,我也瞧见他耳朵有些红。
谢识礼这边红了耳根,谢时景似乎有所感应,他梦呓道:
「栖月……」
我以为他良心未泯,念着我救他的恩情,所以梦里念我的名字。
可他却继续说道:
「湖心栖月,是美景……」
瞧我语塞,谢识礼猜出几分缘由,他想开口再问一句,船猛地晃了两下。
就看见一个少年笑嘻嘻地把脑袋探过来:
「大哥!刺客都抓住了!」
六目相对,那个少年看了看累得睡过去的谢时景,又看了看衣衫不整依偎在二人之间的我,最后目光落在黑着脸的谢识礼身上。
他迅速理解了这个场景,嘴角挂上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对不起大哥,小的不知道您在忙!
「您继续,我给您望风!小的保证两个时辰这里不会有一个人经过!」
4
谢时景醒来第一件事,是被谢识礼罚在院里跪了半个时辰。
谢识礼告诉谢时景,我的伤好前,不许他来瞧我。
大概是打听到了我的身世,又碍于这位主母,谢识礼对我客气又疏离。
他差人送来了北境盛产的鹿茸,为我炖汤补身子。
送汤的丫鬟说,谢识礼还送来了一些野参,但是姑娘的身子不宜大补,所以包起来了,姑娘拆开对个数,看看是不是十支。
我拆开后,却发现十支参子下,还藏着两盒祛疤镇痛的药膏。
药膏旋开,如雪的膏体有松针的凛冽香气。
……和谢识礼身上的香气一样,大约他沙场征战,身上不免落下了些伤,也用这样的药膏吧。
在谢识礼的授意下,府内没人知道我受了伤,只以为我受了惊吓。
大概是我伤口的位置太耐人寻味,女子的清白不能大意。
我心中一动,谢识礼是个很心细的人。
养伤的日子很无趣,只能做些针线。
我听着下人们说谢识礼动了气,因为谢时景不专心功课,却跟一些浪荡子弟厮混。
谢识礼动气,谢时景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这下没有桂花糖藕和糖芋儿也要读书了,既然谢识礼特意叮嘱过,夫子的戒尺可会重重打下哟。
小腿的伤疤好了些,只是天热流汗时,还是发痒。
因我上药不便,肩上的伤好得慢。
半夜,我点着灯,回过头看镜中肩上的伤,伤口有些狰狞,始终没有结痂。
烛火轻晃了一下,我瞥见窗外一个黑影。
不等我叫出声,黑影已经将我笼住,他掩住了我的嘴,低声:
「是我。」
是谢时景。
「你来做什么?」
「嘘——小声点,别让我哥听见。」
我的卧房与谢识礼的书房仅有一墙之隔,要是有点动静,他哥肯定能听见。
我点点头,谢时景放开我,才意识到我此刻对着镜子,衣衫不整。
他一愣,红了脸,忙转过头去:
「你、你干嘛?把衣服穿好!」
「肩膀伤了,不好上药。」
他定神瞧我肩膀,结巴道:
「我、我给你上药吧。」
见我疑惑,他忙解释:
「毕竟你上次救我一命。
「难道我还能对你有什么心思?你也不照照镜子!」
这话说得合乎情理,我把药膏递给他。
外头落了雨,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落在芭蕉上,烛影摇红。
我偏过头就能看见镜子里的谢时景,他在我身后专注地看着伤口,像是勾勒一幅工笔。
那个纨绔的二少爷,原来也有这么认真的样子。
因为贴得太近,他的气息落在我的肩上,让我有些不自在。
「栖月……」
这人奇了,不叫我小丑月了?
「好啦好啦,我知道很丑,二少爷嘴下留情……」按照我对谢时景的了解,我猜到他又要出言贬低我一通。
无非是伤口这么丑,以后怎么嫁人之类的。
「不丑。」
他直接利落地打断了我。
「我又不嫌……」
对上我的目光,谢时景将头别了过去,看起来比我还不自在。
这一扭头,就让他瞧到了桌子上,我做到一半的衣服。
那是件玄青圆领袍,虽未做完,一看也知不是女子的衣衫。
「原来你在偷偷准备礼物。」
我点点头,养伤这阵子,我是在给谢识礼做衣服,谢谢他送来的药膏和鹿茸。
见我点头,谢时景的嘴角疯狂上扬,似乎颇为得意:
「虽然小爷喜欢竹青色,但没关系,这玄青也不差。
「哦对,花纹我喜欢芙蕖,要是太难的话,不绣也好,只是别累着。」
原来这兄弟俩都喜欢芙蕖。
那日我为谢识礼送点心,看见他书房正中挂着一幅偌大的屏风,是谢时景画的满池芙蕖。
「那就绣芙蕖。」我点点头,「也不难。」
听我这么说,谢时景不住地傻笑:
「你慢慢做,我就当没看到啊。
「当然啦,你准备这件衣服,小爷也不会亏待你。」
我不明白,我给谢识礼做衣服,他乐呵什么?
不知怎么的,今天的谢时景有些奇怪。
我疑心他是不是念书被夫子打傻了,却听见敲门声。
是谢识礼在门外。
「江姑娘,你的伤好些了吗?」
谢时景立马给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我拖住他哥,他从后院溜回去。
我点点头,声音如常:
「不大碍事了,但是一直不见好。」
「方便让我看一下吗,若是不好,明日我再去问大夫。」
「等等,我收拾下。」
谢时景已经溜到后窗,他做了个口型:
等我有空再来找你。
谢识礼并不喝我递过来的茶,也不瞧我的伤口。
他目光掠过谢时景溜走的那个窗台,我有点心虚。
「既然江姑娘伤口已经上了药,就不必在下看了。」
闻到了空气中的药膏气味,谢识礼开了口,话里却是冷的:
「你把他照顾得很好,连夫子都不住地赞你。
「第一次见面,我也很欣赏你,临危不乱,不像一般娇弱女子。
「可是我查了,母亲并无江姓的亲眷,倒是花柳巷有江姑娘的名字。」
一案之隔,他忽然抬起眼,鹰隼般的眸子直直地盯着我,像利刃抵在我的喉头:
「你来谢家,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想嫁给你。」我一顿,「做妾也可以。」
「我劝你不要打谢时景的主意,他这样的性子实在不是良配……」
谢识礼脱口而出后,忽然意识到我打的是他的主意。
他一愣,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我来谢家是为了嫁给你。」
听我这么说,谢识礼倒是不知所措起来。
「谢家大娘子买我来,是给你做妾的。」我抬起头,与谢识礼对视,「你若不要我,我就指望谢时景,若是你们都指望不上,我大概会被卖到另一处。」
「纳妾不难,可你嫁给我,只会过得更难。」谢识礼脸上的思虑不假,「你救过时景,我会想办法还你自由身,不必这样委屈自己。」
他能想什么办法呢,一入奴籍,要么拿到身契,要么官家特赦。
沉默片刻,他轻声道:
「……至于上药,可以找我。」
案上茶冷,外头灯也悉数灭了时,谢识礼走了。
灯灭才走,是因为天黑下来,谢时景就不会过来了。
我猜他察觉到了谢时景来瞧我,生怕我们之间有什么不轨,所以突然造访。
可我不明白谢识礼说的,纳妾不难,可嫁给他我会过得更难。
他是威风凛凛的将军,旁人说他素来做事公允,赏罚分明,在军中声望颇高,将士们皆佩服他的为人。
难道谢识礼这样的人会苛待枕边人吗?还是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不禁想到楼里的姐姐们,说有的客人看着斯斯文文不苟言笑,却是嗜好独特的变态,有的客人看着高大威猛,其实比太监还不如,嫁了这样的人就是守活寡。
……谢识礼是哪种呢?
外头雨声淅淅沥沥,我的脑子越想越迷糊。
不管他是变态,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世上总不会有比像个玩意儿一样被卖来卖去,更难的事了吧。
可很快我就明白,谢识礼说嫁给他会过得很难是什么意思了。
三日午后,谢识礼出了门。
他前脚刚走,后脚丫鬟们就送来了一盒燕窝,说是谢大少爷给我补身体的。
拆开盒子,一水雪白燕窝。
而那张身契就静静躺在燕窝下面。
这轻飘飘的一张纸,是一个女子可以被随意涂抹的人生,于我是再造之恩,于他却是一件不必大肆宣扬的事。
我见过大家公子千金买笑,也见过卖油郎救风尘,男人们做了英雄好汉,无一不是大张旗鼓,恨不能昭告天下博个满堂彩。
谢识礼不是。
好像这纸身契,和那两瓶药膏一样寻常,并不值得我独独放在心上。
谢识礼不在,谢时景便来找我,他倚在榻上看书,忽然叹了口气:
「我哥恐怕要娶安平公主了。」
安平公主?那个面首三千,仗着宠爱任性妄为的大公主?
「我哥根本不喜欢她,圣上也知道安平公主的作风,不好强撮合罢了。」
那他说的,嫁给他也过不上好日子,是因为知道自己要娶安平公主?
「你不知道,上次一个侍女给我哥倒了杯茶,我哥谢了人家一句,那侍女就被安平公主砍了手。
「大哥这次去,大概会应了这门亲事,只要是为了谢家,他连自己也能搭进去。」
看我皱眉,谢时景立刻转移了话题:
「不说这些了,栖月你快试试这条裙子和步摇,可是听雨楼的新货,满京城的闺秀都等着他家的成衣,但我敢保证你是头一个穿上的!
「今晚有个诗会,你不喜欢那些人,咱们就不跟他们打交道,可那家酒楼的菜实在好,咱们只管吃,不掺和他们的事儿。」
衣服好看,步摇也精巧。
可我没有心思去打扮,我在想谢识礼是怎么拿到的身契。
他答应了谢大娘子什么?还是答应了圣上什么?
这张身契,他是用什么换来的?
难道是他自己?
我惴惴不安地等到了晚上。
幸好谢识礼回来了。
谢识礼回来,别院外头的门就关得严实,不许旁人进去,连伺候的人都不要。
一墙之隔,我听见了摔东西的声音。
谢识礼人如其名,素来克己守礼,为何会动这么大的气。
而院中幽深,一盏灯也没点。
我有些担心,提着灯笼,小心地敲门。
里头的门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
入目一片狼藉。
先是一地碎瓷片,再是破碎的字画砚台。
天上一丝星光也无,谢识礼孤身陷在黑暗里,手背上是狰狞的伤口,鲜血顺着指尖滴落在地上。
察觉到我手中的光,他在黑暗中抬起头,死死盯着我,像笼中饥饿的困兽盯着猎物,他咽了口口水,艰难地开口,却是:
「你走。」
我闻到了他身上甜腻的杏仁味。
是相见欢。
就是最贞烈的姑娘也抵不过这药,若是买来的良家不从,鸨母就会往饮食中掺一点相见欢。
而这香气浓郁的程度,估计药量连一头狼都能放倒。
他努力别过头不去看我。
我提着灯笼,一步步走近。
头上的金步摇流苏映着烛火。
每走一步,步摇的火光就在他眼中跳一下。
谢识礼哑着嗓子,怔怔盯着我:
「……你来做什么
「你明明可以走……」
吹灭了烫人眼的烛火,书房静得可以听见粗重的呼吸。
我拉住他的衣袖,像仰攀万仞悬崖上那一棵千年积雪的孤松。
「找你上药。」
5
谢时景:
最近谢时景觉得心绪不宁,总做同一个梦。
梦到那日船上摇荡的湖光和覆在脸上的长袖。
就连和栖月在一起时,蘅芜的香气总把他带回那个晚上,说来也奇,明明是又破又旧的船舱,甚至有木头腐烂的味道。
他竟然心安得不行。
而除了湖色,他也开始梦到一个人。
只是刚刚趴在画纸上打了个盹的功夫,就又梦到了她。
梦到摇荡的湖色中,一捧新开的芙蕖在她脚边,她坐在船尾,执一柄轻罗小扇拨弄荷丛,惊起星星点点的萤光。
是他日思夜想的那位瑶池仙子。
可她回过头,分明是江栖月的脸。
怎么可能是她……
绝不可能是她……
可是如果是她……
如果、如果是她……
谢时景忽然发现,自己心底竟然隐隐期待江栖月是她。
不可能,栖月都说了,仙子已经被良人赎身,此生不可能得见了。
不过没关系,有栖月在就好。
栖月会给自己做桂花藕和糖芋儿,能治他怕黑的毛病,会给自己缝制衣衫。
栖月是真的在意他。
这么想来,仙子可比不上栖月。
唯一要烦恼的是他跟那位后母的关系并不好,要如何开口要人。
因为讨厌那位后母,所以一开始连带着对她也没有好脸色。
其实他一开始并没有想过娶她,只是那一日宴席,是他最开心的一次。
他谢二爷自诩风流,哪次聚会不是请最红的姑娘,把旁人都衬成俗物。
可她什么也不会,低头吃着东西。
把自己亲自为她画的唇,价值千金的流苏簪子都糟蹋了。
他可能喝多了酒,竟然觉得她这样真是可爱。
他去问崔昊,崔昊却说喜欢的话就收了做通房。
谢时景回去琢磨了三天,觉得这话说得不对,又不知是哪里不对。
崔昊白他一眼:你还想娶了做正妻不成?
谢时景半晌不语,忽然点头:是了,就是这里不对劲。
崔昊以为他明白过来了,谢时景却说:
大哥要先娶亲,我才能娶她为妻。
如果以后娶栖月为妻,他不能像从前一样贪玩,跟别人厮混。
大哥袭爵战功赫赫,他就得考个功名,在朝堂上有番作为。
想到这,眼前画纸已经铺开。
满室灯辉,亮如白昼。
往日让他心安的烛火,如今竟然让他心乱。
谢时景的心里有一种挣扎的痛苦和旖旎的情愫,让他忍不住去想江栖月。
他从小就与兄长有些心意相通,兄长受了伤他会觉得痛,他着急时兄长也会焦虑。
那这种情绪是他的,还是兄长的?
兄长在做什么?今夜被公主召见,过不了多时便要娶她。
那兄长今夜情动,是因为公主吗?
谢时景不知道,他知道自己此刻想见栖月。
他要告诉她很多事情,比如好看的是她而不是自己挑的衣裙,比如那天为她上药他并不那么光明磊落,他有一点见不得人的龌龊心思。
比如今晚没有诗会,只不过是找个借口想带她去吃些好吃的,再趁着暮夏带她去湖心泛舟,趁着芙蕖还没谢。
还要跟她道歉,因为做了很多虚张声势,不过是怕她不爱他的幼稚事。
谢时景提了灯笼,脚步匆匆。
原来有了想见的人,夜晚也不是那么可怕。
可栖月房内一片漆黑,她不在。
冥冥中,他又闻到了栖月身上蘅芜的香气。
他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兄长的院子。
谢识礼应该也不在。
谢时景忽然想到了书房有一幅巨大的屏风,是他为兄长画的满池芙蕖。
他忽然想去看看花。
谢时景推开书房的门,一抬眼,只觉得全身血液都凝固了。
他见仙子坠落凡尘。
不,是被他敬重的兄长拉下凡尘,贪婪地禁锢在怀中。
而自己画的巨大屏风,密密匝匝的芙蕖竟然开得糜艳,如当年初见心动时,无穷碧色的湖上。
日思夜想的身影此刻近在咫尺,她背对着自己,如多年前惊鸿一面那般。
长发未梳,散落如瀑。
仰攀高枝,如坐莲台。
她绯艳的侧脸和画上慵懒模样渐渐重叠,令他目眩。
下午还为她精挑细选,插在鬓边的步摇,此刻弃置在桌角,就像他一样,被她随意丢掉。
他呆呆地定在原地。
没人发现他,他却宛如一个卑鄙的小偷,觊觎着不属于他的宝物。
为什么?
不是说给他做媳妇吗?
湖心那一晚难道不是表白吗?
不就是爱慕荣华富贵吗?
他能给的我难道不能给吗?
灯笼和衣服都跌破了,谢时景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
他在窗边,怔坐了很久,笔下还是她的模样,连颜料都没干。
画上的她依旧笑意盈盈,满眼是他。
假的。
都是假的!
什么瑶池仙子!什么良人赎了身!
她看到自己被蒙在鼓里还如此深情,恐怕只觉得可笑至极吧?
难怪第一次见面她不在意自己的讥讽,难怪她那日拿着扇子不敢看他。
他早该知道这都是假的!
她把我当傻子耍。
谢时景忽然很想放声大笑,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牵扯不动嘴角。
甜蜜和痛楚两种情绪在心头如刀绞,来自兄长的甜蜜情愫是刀上淬的毒。
疼得他滴下泪来。
谢时景想划烂那幅画,可是看到她的眼睛,又顿住了。
脑海中有两个声音在拉扯他的心。
他说,她本来就是这样,谁能让她过得好,她就选谁。
他说,她这样的女人,哪个花楼里寻不到?
他说,当初是你嘲讽人家,给你做小你也不要的。
是啊,这都是他说的,那个纨绔浪荡的谢二爷说的。
可是还有一个声音。
他说,谁能让她过得好,她就选谁,难道有错?兄长是顶天立地,有担当的男儿,谁会放着他不选,选你呢?
他说,花楼里是有许多姑娘,可这世上哪有两个月亮?
他说,只要她要他,哪怕给她做小呢……
这是他谢时景,谢遇安说的。
一地宣纸泛着冷冷的白色,如不化的霜。
一点点铺陈水色,他的脑子越乱,心越痛,笔却越稳。
可等他回过神来,一地散落的画,都是她笑她嗔。
谢时景惯会画圣洁不染的仙子
唯独身下这幅,芙蕖仙眼梢都泛着潋滟的绯色,她被人揽入怀中。
而那个折花入怀的人,分明是他的脸。
我也很干净的……
为什么不是我呢……
明明、明明应该是我的……
书房那触目惊心的一瞥让他知道,原来她不是不懂风情,只是不愿给自己看罢了。
谢时景在一地的画中木然坐了一夜,自虐般放空自己,任由谢识礼的情绪灌入。
天已经隐隐泛出蟹壳青。
一夜冷风吹彻,满地狼藉。
谢时景将画一张张捡起。
骗他也好,虚情假意也好。
虚情假意拆开,也是有情意二字的。
再说那些回忆也不是假的……
至少不全是假的……
那件衣服总是做给自己的吧?
那桂花藕和糖芋儿,甜得结结实实,怎会有假……
那晚的风声和湖色怎么不真?他都切切实实在她怀里了,听她温柔哄着自己。
如果那晚没有睡去就好了。
不对……
如果那一晚死在她怀里就好了。
6
谢识礼:
谢识礼醒来,眼前少女正在桌旁准备早点,是清粥并着些小菜。
她动作很轻,似乎是怕把他吵醒。
她已经将昨天令他痴迷不已的长发挽起,那支金流苏簪子也一丝不乱。
好像昨晚的旖旎都是幻梦一场。
她一瞥,看见他醒了,柔声谢他:
「身契我拿到了。
「早饭是我做的,没惊动旁人。」
若不是他眼神好,险些要看不见她脸上转瞬即逝的红云。
不等他开口,她将一个包袱递给他:
「这是前几日病中为将军缝的衣服,应当是合身的。
「燕窝和人参我都没动,药膏的钱,要是太贵,可以等我缓些日子给您。」
谢识礼想说些什么,眼前少女却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您不必挂怀,只跟您一个人睡觉就可以换来自由身,已经很好了。」
谢识礼很难把眼前这个不卑不亢的她,和昨天在他身上啜泣求饶的她联系到一起。
「你既自由了,要去哪?」
发觉自己这话似乎在撵人,谢识礼忙补上一句:
「你可以一直住这,我不会娶别人。」
「那安平公主……」
她是不是以为这身契是跟安平公主的婚事换来的?
「我和时景商议后,答应了母亲,请旨把爵位让给她亲生的三弟弟,她就把身契给了我。
「昨日安平公主下药,本是想让旁人撞见,这样我就不得不娶她。」
「那将军要小心,不知安平公主会不会罢休。」
又是沉默。
「你要不要留下、在这里……」
「我要回金陵了。」
「为什么?」谢识礼发现自己有些失态了。
「我阿娘葬在金陵,我要回去看她,走运的话再留在金陵,凭着手艺开个茶楼。」
谢识礼才发现自己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
察觉到他的好奇,她笑一笑:
「十二年前,我们一家逃荒到金陵,一家子吃不上饭,我娘又生了病,就卖了我。
「我爹说卖的活契,最多给楼里的姑娘当个粗使丫鬟,等以后我娘治好病,家里有钱了就赎我回去。
「我很听话,没挨过打吃过亏,学着认字,又攒了些钱,等着我娘哪天来接我回家,可我等了很久,她始终没有来。
「我倒不怕她不来接我,我只怕阿娘的病怎么一直不好,她病得那样重,疼不疼。
「后来妈妈看不下去,说我爹当年签的是死契,妈妈没有骗我。
「阿娘在我被卖掉的那年秋天就病死了,阿娘也没有骗我。
「唯一识字的爹骗了我们。」
他想问一问那个畜生不如的男人是何下场,她却已经不打算往下讲:
「这世上不是善恶有报的。
「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对吧?」
谢识礼怔住,点点头。
谢识礼还想问什么,比如她如何看待他,如何看待他们的关系……
「大哥!陛下说要找您南下同游。」
但是不等他问,那个没有眼力见的下属程飞又冒冒失失地闯进来。
「……你能不能,等我回来。」
见她疑惑,谢识礼努力想了想,
「这药确实很贵,我、我怕你赖账。」
程飞挠挠头,平日里将军自掏腰包贴补将士们,眼皮也不眨一下,什么时候这么抠门了?
她一愣,点了点头:
「我等你回来。」
她说等他回来,她说她等他回来。
谢识礼的心情莫名愉悦起来。
他动身陪圣上南下,两日便要启程。
因为那副相见欢,宫中起了轩然大波,事关天家体面,圣上训斥了安平公主,罚了禁足又降食封,这两日为她选了位好性老实的驸马,匆匆嫁过去了。
也算给了谢识礼一个交代。
路上费了些时间,到金陵已是初秋。
她给自己做的衣服正好可以穿了。
玄青衫子用同色的丝线绣了芙蕖,乍一看是看不出的。
里衣用蕊黄线绣了一轮新月。
新月像她,也像那日她留在他肩上的甲痕。
谢识礼脸上一热。
所幸旁的画舫叽喳吵闹,无人在意他。
不知哪家携家眷出游,女孩子们笑闹也不避人。
如果栖月也有这样的家人,她大概会一生顺遂,不必漂如浮萍吧。
奇怪,他为什么总能想到她?
远远闻见桂子的香气,有人要去湖心岛上折桂。
谢识礼想到第一次见栖月,也是在船上。
她身上有血,却镇定自若。
甚至一眼就看出了他和谢时景的关系,理所当然地抬起下巴:
「我救了你弟弟,你要帮我。」
还以为她很坚强,然而自己粗糙的手指碰到她的小腿,她就皱着眉头说疼。
他明明已经很轻了,还是说女孩子都是这样细皮嫩肉的吗?
谢识礼没碰过女人,他不知道。
他曾想过自己的人生轨迹,自己既然能在尸山血海里挣出功名,就把爵位留给两个弟弟,等战事平了,也许会娶一位看得顺眼又门当户对的夫人。
「很疼,你轻点。」
她抱怨的声音竟然让他烦躁,所以干脆找个理由让她闭嘴:
「别吵醒他。」
「会留疤吗?」
……应该会吧,可是女孩子不是穿裙子吗,看不出的。
「可是你知道啊,我穿裙子遮住了你也知道,我未来夫君也会知道,裙子和衣服底下……」
她天真地抱怨着伤口,谢识礼忽然想到今后看见她穿裙子,自己都会下意识想她轻盈或繁复裙摆下的伤疤。
回去先罚了谢时景跪,她送来了桂花藕和糖芋儿。
与此同时,她的身份情报也压在了糖水下。
她是后母在金陵买来的,目的略想也知,父亲去世后,她一直惦记着儿子袭爵的事。
谢时景不喜欢这位后母,是因为他无法接受往日深情的父亲竟然会在母亲病逝后另娶。
而自己对她也只是客气恭敬,父母为孩子计谋理所应当,只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他往往不计较这些。
那晚谢时景翻墙上药,他是察觉到了的。
因为那份来自谢时景的悸动,他怎么也压不下去。
他们在做什么?
怕谢时景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他才半夜敲了门。
原来只是上药。
他质问她的来历,以为她是想利用谢时景。
他没有瞧不起她,只是觉得他这个弟弟现在这样,实在不是可以托付的人。
哪怕做妾。
她说不是谢时景,是他。
见自己不为所动,她忙说:
不是你,谢时景也行。
这种人尽可夫的言论,经她说出,谢识礼没有鄙夷或轻视,只是很同情眼前这位姑娘。
谢时景是锦绣堆里长大的,他大概无法懂这位姑娘的苦处。
要他明白,大概还要吃过许多苦。
这爵位他不要,顺位也是谢时景的,还轮不到那个牙牙学语的三弟弟。
他问谢时景,爵位和栖月必须选一个,他会如何选。
他没有说要换栖月的身契,只说换她自由。
但聪明如谢时景,已经想到了缘由。
谢时景说如果自己争气,不必留爵位给他,如果不争气,那留爵位给他也无用。
何况栖月于他是救命之恩,他该报。
他愿意用爵位去换。
明明到这里,他们三个已经互不相欠了。
可偏偏。
偏偏她放下灯笼在他脚边,小心翼翼地仰起脸看着自己。
她明明什么都知道,却一点设防也没有。
察觉到了闪躲,她吹灭了灯,房间内静得能听见她的呼吸,近得能闻到她身上若有若无的蘅芜香气。
她在耳边一字一顿:
「找你上药。
「你说过,可以找你的。」
有时万仞雪山崩塌,也许只是有一片雪花恰到好处地落下。
千年积雪的孤松折腰,可能也只是因为一阵寻常微风穿过身体,令它战栗。
「大哥,一个人在想什么?」程飞的手臂忽然大喇喇架在谢识礼肩上,「咦,怎么脸这么红?」
在破坏氛围让谢识礼失望这件事上,程飞就从没让谢识礼失望过。
可真的怪程飞吗?难道不该怪他今夜一直在想她吗?
他见月是她,见湖是她,连桂子的香气都比不过她新蒸出的桂花藕。
「程飞,你会不会经常想起一个人?」谢识礼想了想,「不该如何跟她说话,毕竟说白了也是一场交易……」
程飞一副了然于心的表情:
「那他一定欠了将军很多钱。
「上个月副指挥使欠了我十两银子,我可是连续三天梦到他。」
不是这种想。
「那就是有血海深仇!」
也不是。
「女的?」
见谢识礼不语,程飞挑眉:
「那就是爱——」
「……不。」谢识礼立马反驳。
「——而不自知。」程飞促狭一笑,「被我说中了,如果你们互不相欠,又没深仇大恨,你凭什么想她。」
是啊,凭什么呢……
「帮我查个人。」
「难道就是大哥您惦记的……」程飞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不,这个是血海深仇的。」谢识礼想了想,「若是他走运死得早,就把尸骨掘了,若是不走运,也不必安葬了,但要给他立个碑,明年兴许会带人去看他。」
「如果他要做个明白鬼呢?」
「就说他素未谋面的女婿要杀他。」
7
江栖月:
谢时景不肯见我已有半个月了。
我不知自己哪里得罪了他。
更让我摸不着头脑的是,他一边生闷气不见我,一边送我东西。
每次都是敲敲我的门,打开门人已经跑了,地上不是衣裙就是首饰,每件东西都附着字条,像是《罪己诏》:
「我才是二流货色,不配站在你面前。
「你不丑,很好看,是我一直不敢承认。」
原来是为了从前的事情道歉吗?
说实话,谢时景说的那些话我从未往心里去过。
毕竟名义上我是他讨厌的后母的远房亲戚,还逼着他念书,他讨厌我这件事完全在我意料之中。
可是为什么要忽然道歉呢?
我细细思索,终于意识到——他太想要那件衣服了。
那天他一定误会了,以为衣服是做给他的。
我想了想这些日子他送的礼物,也有些过意不去。
便做了件竹青色,连花纹都一样的送去他那里,也算我们相识一场。
可他在门缝后探出头,看到衣服竟然先红了眼圈,似乎不可置信:
「真是送给我的吗?」
我点点头。
「……那你还讨厌我吗?
「我会改的,我不会再这么任性了,也会听你的话努力上进,这次春闱我一定能中,只是你别不理我……」
瞧我不语,他伸出手去拉住了我的衣摆,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我只是觉着算术有趣,又跟我爹怄气,并不是不学无术地滥赌。
「我也只是真心欣赏那些女子,并没有肌肤之亲。」
说罢他先红了耳根,又结巴道:
「我、我还是干净的。」
他说这些做什么?
「我知道兄长……我知道我现在处处比不上他,可是我长得像他,可以很像他……
「你不理我, 你选他的时候, 我心里很疼很疼……
「那我努力上进,再求一求兄长,将来给你做小, 你、你要不要……」
谢时景支支吾吾。
见过他浪荡纨绔,顽劣专行的样子, 乍一看现在脆弱哀求。
说实话有一丝心软。
不等我开口,却听见身后谢识礼恼怒的声音:
「谢时景!你在说什么?」
见谢识礼来了, 谢时景竟然开了门。
他是匆匆赶来,额头已经渗出薄汗。
气氛有些微妙。
谢识礼看到了谢时景怀里的衣服,和他身上穿的几乎一模一样,有一点不自在。
他们本就相像, 若不是谢识礼更高大些, 到时穿上一样的衣服, 恐怕一时竟难以分出二人。
他们站在我面前僵持不下,索性同时对我伸出手:
「这个给你。」
兄弟俩掌心各是一只玉镯, 很容易看出来原是一对的。
「这对镯子是母亲留下的, 我们一人一只,等以后遇到合适的姑娘, 做定亲礼。」
说话间,谢识礼眼疾手快,已经将玉镯放在我的掌心。
「哥!」
「时景, 哪怕是兄弟, 有些事是不能让的。」
「我没有要你让给我!」谢时景急了, 忙拉过我的手, 将那手镯很轻巧地塞进手腕, 「这样不是正正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分开呢?栖月都没有赶我走, 你凭什么说不可以?」
这两只玉镯我想还给他们, 结果兄弟二人默契地抱臂别开身去,没人肯先接过。
「我要回金陵, 镯子我会收好, 如果明年这时你们还愿意, 可以来寻我。」
那时过了春闱, 北境的战事也平了。
我也是自由身, 有安身立命的本钱。
那时再开始, 应该不像现在这么多顾虑吧。
天气转凉, 一切事毕。
我收拾了行李,一路南下。
回金陵祭拜了娘亲,又寻了家茶楼栖身。
日子忙碌起来就过得很快, 听说北境打了胜仗,将军不日就要回京了,为他那位探花郎的弟弟庆贺。
谢家这是双喜临门, 贺喜说媒的人几乎要踏破门槛。
谢母一一推了,只说二人不在, 且都已定了亲, 不在京中长住了。
而谢家两位郎君俱已南下, 共赴约。
南方桂子这时开得正好。
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正适合夜里赶路。
因为这世上是有两个月亮的, 一个在天上,一个映在湖中。
一个照他策马疾驰,一个照他轻舟过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