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底以来,叙利亚新政权与国际和地区多国间的外交互动,以及新政权领导层宣布延长举行选举的时间表,均标志着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进程将是漫长而艰难的。海湾国家看似立场统一,但实际上因各自利益诉求不一,在看待和处理与叙利亚新政权关系时也会呈现出有差异的方式方法。无论怎样,叙利亚内部的复杂权力争斗未来不会缺少海湾国家的身影。

叙利亚新外长抵达利雅得
2024年12月30日,乌克兰外交部长到访大马士革拉开了国际和地区多国政府高官与叙利亚新政权开展外交互动的大幕。自同月8日阿萨德政权倒台后,土耳其外长Hakan Fidan、美国负责近东事务的国务院助卿Barbara Leaf、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Geir Pedersen先后现身大马士革,此外还有利比亚负责通讯和政治事务的国务部长、卡塔尔外交国务大臣、埃及外交部长以及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国家的外长等等。
有去也有来。2025年伊始,叙利亚新政权的外交部长Asaad Hassan al-Shibani以及新任命的国防部长Murhaf Abu Qasra就到访了利雅得,沙特也因此成为了叙利亚新政府高级官员首次出访的目的地。紧接着,叙利亚外长Asaad Hassan al-Shibani在12月下旬与阿联酋外交部长Abdullah bin Zayed通电话后,又于本周亲自到访阿布扎比与后者举行面对面的会晤。
此外,1月2日,土耳其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有意与叙利亚新政府的国防部建立战略关系。而在叙利亚新政府这边则是对阿联酋、巴林、沙特、阿曼等8个国家位于大马士革的大使馆恢复外交工作表示了感谢。至于卡塔尔和土耳其,则是早在去年12月中旬就重新开放了各自的驻叙利亚大使馆。
海湾国家共同立场下的暗流涌动
乍看之下,海湾国家对待叙利亚新政权的立场和态度是团结的、务实的。但对于叙利亚国内政治过渡进程走向、叙利亚维护领土完整和打击极端主义等问题,则似乎分歧大于共识。
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的长期统治在短短数日内土崩瓦解,这是让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始料未及的。相似的一幕让他们想起了当年“阿拉伯之春”浪潮冲击下的Ben Ali、Hosni Mubarak、Muammar al-Ghadhafi、Ali al-Saleh以及前些年的Omar al-Bashir和Abdelaziz Bouteflika。当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对叙利亚“变天”都感到震惊。因此,海湾国家最初的反应十分谨慎,恪守着一般性原则,只是发表简短声明,支持维护叙利亚政府的稳定以及人民的团结。
如果事态发展就到“沙姆解放组织(HTS)”重夺阿勒颇为止,那么海湾国家这样的表态也没什么问题。特别是阿联酋、巴林和阿曼这三个海湾国家,它们在各自的声明中均提到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也算是一定程度上对阿萨德政权诉求的呼应,符合2018年以来这三个国家对于阿萨德政权的政治支持大趋势。
大马士革陷落以及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将事态发展引到了另一个方向。且不论此前的表态尴尬与否,单从海湾国家的利益诉求来看,这些国家和其他与叙利亚接壤的国家一样,都对这个沙姆地区重要国家的“地震”感到忧心忡忡。从领导层到普通民众,人们担心的是叙利亚可能再次爆发内乱或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进而输出动荡经由邻国伊拉克和约旦向阿拉伯半岛蔓延。
正因如此,海湾国家内部有声音呼吁强化对叙利亚事务的介入力度,既缓和与叙利亚新政权的关系,也对土耳其形成一定制衡。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就有了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巴林等阿拉伯国家外长在亚喀巴举行的叙利亚特别会议上共同发表的声明,承诺为叙利亚过渡政府提供更强有力的援助和支持,同时强调叙利亚新政权需要进行全面和包容的全国性政治对话。
站在地区国家间关系的角度,海湾国家领导人毫无疑问会着重权衡伊朗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地缘政治地位此消彼长所带来的影响。但在这背后,还有一个暂不会拿到台面上但却十分重要的因素也在海湾国家领导人的考量范围内: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长期统治家族被一场民众起义推翻,而这场起义的领导者有着很强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属性,这对于海湾国家乃至整个地区意味着什么?
网上能够找到的一些视频资料显示,当HTS的军事领导人Abu Mohammad al-Jolani在倭马亚清真寺发表胜利演讲时,民众聚集在一起高唱着“阿拉伯之春”时期的歌曲。对于诸如此类信息的解读,如同棱镜的反射一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于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在中东地区的复兴,哪怕只是微弱的火苗也足以吸引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并对局势演变进行更加系统的评估。
发端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引发了民众起义,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老一代政治强人被迫下野、流亡甚至丢了性命。这股浪潮的冲击对海湾地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阿萨德政权治下的叙利亚在“阿拉伯之春”后因内乱无暇他顾,从一个地区老牌强国变成了近年来毫无存在感的“小透明”。只不过,当我们在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作为“事后诸葛亮”来回溯,发生在叙利亚的一切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就像是整个中东错综复杂矛盾纠葛的缩影。这里有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犹太人、波斯人之间的民族冲突,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之间的宗教冲突,也有逊尼派、什叶派之间的宗派冲突。当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解读出政治左派和右派等冲突。正是这些不同捉对厮杀的矛盾冲突搅合在一起,将叙利亚变成了域内外政治势力的角斗场。
海湾国家看似铁板一块,却因为不同的地缘利益诉求而在叙利亚表现为内斗频频。这种内斗不仅仅有政府的身影,也直接牵扯到不同海湾国家的民众。
在卡塔尔,一位著名的人道主义活动家因资助叙利亚境内的基地组织分支而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在科威特,有多个机构和个人开展广泛的募资活动,为叙利亚境内存在竞争关系的不同派系叛军和慈善机构提供资金。在沙特,曾有数十名神职人员公开呼吁对阿萨德政权发起大规模圣战。在巴林,该国公民Turki al-Binali成为了“伊斯兰国(ISIS)”的主要理论家,发表了大量支持在叙利亚建立现代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的言论。在科威特、沙特、阿曼,都发生过ISIS对当地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式袭击的惨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萨德政权恢复了对叙利亚部分地区的控制,加之也门的胡塞武装牵扯沙特等国太多精力,叙利亚境内的叛军与来自海湾地区的金主们渐渐“失联”。
是“失联”并不是“断联”。比如卡塔尔,这个海湾国家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与土耳其协调配合,向叙利亚多支反政府武装提供物资和后勤支持,迄今也未切断与这些势力的联系。相较于其他海湾国家,卡塔尔与HTS领导的叙利亚新政府之间的渊源更深,即便后期对其支持有限,也远远超出海湾国家那份敷衍了事的联合声明。
卡塔尔曾在多哈举行会议,为有关各方就俄罗斯和伊朗撤回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提供了谈判桌。阿萨德政权甫一倒台,卡塔尔就立即启动了人道主义空中通道,为叙利亚民众提供物资援助。更重要的是,战后叙利亚的最大造局者——土耳其,是卡塔尔在中东地区最重要、最亲密的合作伙伴,这也暗示出多哈方面未来在叙利亚政治过渡和战后重建过程中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阿联酋的角色略显尴尬。该国此前在海湾国家中一马当先修复与阿萨德政权的关系,还在2022年邀请巴沙尔到访阿布扎比。对于叙利亚新政权,阿联酋的官方表态十分“官方”。值得关注的是曾任外交国务部长的总统外交顾问Anwar Gargash前不久的一番公开评论。考虑到他的身份,这番评论势必深思熟虑且经过了高层审核。

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Anwar Gargash
Anwar Gargash表达了一些担忧。他认为,“(叙利亚)新政权的性质、与穆兄会的关系、与基地组织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相当令人担忧的因素”。
对此,“我们一方面必须保持乐观,继续向叙利亚民众提供各类援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该地区以往曾发生过的类似情况,需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他补充说道。
显而易见,对于HTS能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弃极端主义和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意愿,以及该组织作为叙利亚新政权核心团结不同政治力量的能力,阿联酋人是抱有极大的问号的。
沙特的立场又似乎更加矛盾一些。与阿联酋不同,利雅得方面此前没有回应阿萨德政权的声援诉求,因为它已经在HTS挺进大马士革前就嗅到了阿萨德家族统治的摇摇欲坠。
更重要的是,沙特始终视阿萨德政权为“眼中钉”,哪怕此前与其关系缓和还同意叙利亚重返阿盟,这也是极不情愿的拧巴之举。从时间线来看就十分清楚,沙特恢复与阿萨德政权间的外交关系发生在2023年,比阿联酋和巴林晚了四年多。
沙特的矛盾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谨慎,这与该国在“阿拉伯之春”后未能借机颠覆阿萨德政权的失败有极大的关联。彼时,利雅得方面与美国、约旦协调行动,在叙利亚境内支持部分反政府武装。这样的做法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和沙特国内都引发了较大争议。更关键的是,沙特失败了。
这场失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时任情报总局局长Bandar bin Sultan从沙特的权力圈中被彻底踢出局。此后,沙特偃旗息鼓,在叙利亚未再有大动作。但无论是前国王阿卜杜拉还是现在的萨勒曼父子,都对阿萨德政权没有好感,也对叙利亚感到十分头疼。从宏观战略来看,沙特与叙利亚虽不直接接壤,但“2030愿景”的核心项目之一——“未来新城(NEOM)”坐落在西北角,一旦叙利亚局势动荡外溢,势必影响NEOM的周边环境,对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造成不利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来自叙利亚的走私毒品屡禁不止,给沙特政府带去了不小的麻烦。
正因如此,虽然有沙特民众私下里为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筹款募资,也有热血的沙特青年志愿加入对阿萨德政权的圣战,但沙特官方总体上十分审慎,对这些做法的默许更多出于掌握公众情绪的考量。现如今,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沙特国内媒体上越来越多出现声音呼吁支持和拉拢叙利亚新政权。对于沙特领导层而言,这似乎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地区影响力的良机,也是巩固和提升自身在沙特民众乃至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地位的好机会。
叙利亚新外长Asaad Hassan al-Shibani前不久访问沙特的言论,似乎也代表着新政权向利雅得方面敞开了大门。他对沙特此前支持叙利亚过渡的“积极”声明表示感谢,并指出沙特的态度对帮助稳定局势产生了影响。
无独有偶,叙利亚新政权领导人Ahmed al-Sharaa在接受采访时不遗余力地强调沙特对于叙利亚的重要性。他指出,沙特“在叙利亚的未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强调他“为沙特为叙利亚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为了体现与沙特的联结,Ahmed al-Sharaa在采访时提到他的童年是在利雅得度过的。
叙利亚政治过渡时间线只会拉长
最近的一系列事态发展表明,有关各方正就阿萨德政权倒台后的叙利亚未来走向展开一场激烈的博弈,一场在叙利亚内部和外部同时展开的双重博弈。
英国学者Patrick Seale在其著作《叙利亚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Syria)》中曾试图梳理决定叙利亚独立建国后的关键政治力量。时过境迁,这本书写作和其分析的年代都与今时今日有显著不同,但作者描述的一些影响因素依然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他在书中提到的“内部权力斗争和更广泛舞台上的冲突之间的双向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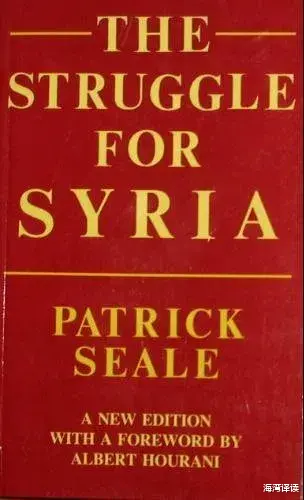
Patrick Seale的著作
彼时,笼罩在叙利亚上空的两股力量一个来自埃及,另一个来自伊拉克。如今,同样有两股主要力量,一个来自土耳其,另一个来自沙特(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从地缘政治重要性来讲,叙利亚似乎已经不是Patrick Seale书中所描述的那种“大奖”,但这个国家的内部紧张局势依旧可以“立即输出给邻近国家”,而这些受到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国家势必或静观其变或出手干预,塑造叙利亚内部动态。Patrick Seale的上述观点在今天依然适用。
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进程很可能会在类似的内外纠缠中曲折前行。
也许是意识到了最初承诺的临时政府时间表只有短短三个月太不切实际,Ahmed al-Sharaa在接受Alarabiya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过短的权力移交期会带来危险,因此明确将大幅延长过渡期期限。他透露,选举的筹备工作将需要4年时间,起草和批准新宪法将需要3年时间。
暂且不论HTS是否在移交权力方面有私心,肉眼可见的是过渡期较最初大大地拉长了。
一方面,较长的过渡期给了现政权充足的时间去对话、整合叙利亚境内各种势力,重建对大部分地区的管控。其中,较为积极的一点在于Ahmed al-Sharaa强调不允许建制外的民兵武装,他还特别指出库尔德人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与美国在叙利亚东北部打击ISIS的军事伙伴。
另一方面,较长的过渡期也给了外部势力充裕的时间,让它们得以从容地重新整合代理人势力介入叙利亚内部事务,这也将导致叙利亚的意识形态路线、内部权力竞争态势等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
即便是最理想的情况,即各派通过对话谈判而非武装争斗来实现国家军队的整编重建,叙利亚的和平过渡期也将持续数年甚至更长时间。
不那么理想的情况则是,各方围绕叙利亚政治过渡主导权的争斗白热化,在宪法草案、选举规则、政党发展、人口普查、经济控制等各条战线上全面铺开。外部势力介入并注入大笔资金以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议程,反向恶化叙利亚情况的复杂性。这将是一个令人担忧、动荡的过程,并有可能随时受到临时政府的扭曲。
有人认为叙利亚的情况可以借鉴邻国伊拉克这个先例。仅就战后重建前景而言,叙利亚远远比不上伊拉克,很难获得重建所需的数百亿美元资金支持,因为它没有伊拉克那么庞大的石油财富做支撑。
穷山恶水出刁民。一旦战后重建进程不畅,HTS或其他政治势力会否在意识形态上向极端化转变,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哪怕只是意识形态上或治理体制上的微小调整和转变,都有可能对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进程构成干扰,导致权斗不息。
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叙利亚新政权接下来在政治过渡进程迈出的每一步。从防范周边动荡影响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海湾国家理应帮助叙利亚新政权维护国家的稳定。HTS的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些挑战,因此对外发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援助诉求,而不是引入外国的军事干预。
Ahmed al-Sharaa首次接受媒体采访选择的就是沙特背景的《中东报(Asharq Al Awsat)》。他首先向所有海湾国家保证,“叙利亚革命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而宣告结束,我们不会向任何其他地方输出革命……叙利亚不会成为攻击或引起任何阿拉伯或海湾国家关切的平台,无论是谁。”

Ahmed al-Sharaa接受《中东报》专访
Ahmed al-Sharaa的呼吁随后扩大到一个隐晦的投资和经济支持请求。他以略显奉承的口吻说道:“我们支持并期待海湾国家在当前的发展道路上取得的成就,也渴望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朝一日也能实现这一目标。沙特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拥有一个我们也十分艳羡的发展愿景。毫无疑问,我们两个国家有许多共同目标,完全可以在经济、发展合作或其他方面进行协调。”
目前来看,Ahmed al-Sharaa的计算是正确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如果得不到实质性的政治和财政支持,就很难避免在外部施加的竞争性干预下再度内部分裂。相较于十几年前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时刻已然结束。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对外态度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对于叙利亚以及他所领导的现政权,或许最优解是将战后重建项目与海湾国家当前主导的各类发展项目结合起来。
中东地区和解潮中断后的未来走向
2023年3月,在中方调解下,沙特与伊朗在北京签署文件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开启了此后新一轮中东地区和解潮,直至当年10月7日巴以冲突再度爆发。
彼时,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沙特与伊朗在中方斡旋下的和解是前者面对后者及其主导的“抵抗轴心”咄咄逼人而作出的让步。的确,当时的伊朗在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等势力的拱卫下,其在中东地区的崛起势头正盛。
然而,如今的地区形势变化清晰无疑地展示出了伊朗地区影响力的自由落体般下跌。中东地区的地缘格局也因此呈现出现了3条支线并驾齐驱的局面。其中一条支线旨在维持2023年10月7日前的均势(主体是伊朗),另两条支线则分别希望建立起有利于自身的新中东(主体分别是以色列和土耳其)。

中东地区新版“三国杀”
相对于这三个国家,沙特等海湾国家尝到了过度参与地缘冲突而错失经济发展红利的苦头,因此表现得较2018年以前更为克制。
先说伊朗,2016年1月15日正式生效的《伊核全面协议(JCPOA)》并非只是暂时限制伊朗发展军事核能力的一套技术性协议,而被西方国家以及许多阿拉伯国家视为国际社会对德黑兰方面的让步,为后者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大开“绿灯”,从支持阿萨德政权恢复元气,到利用胡塞武装牵制沙特,均是JCPOA的产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他通过“极限施压”在经济层面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而2023年10月7日后以色列“肢解”消灭“抵抗轴心”有生力量的军事行动则是在政治和军事层面打击了伊朗,导致伊朗在地区的野望收到了极大遏制。
在这一过程中,中东地区形势出现了充分利用伊朗衰落的两条新支线。第一个是以色列总理Benjamin Netanyahu提到的“新中东(New Middle East Project)”,另一个是土耳其历来主导的政治伊斯兰。只不过,土耳其所倡导的政治伊斯兰在“阿拉伯之春”受挫后也一度陷入沉寂,直到近期阿萨德政权倒台方才重现江湖,但形式上比以往更加务实。
那么,问题来了?伊朗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吗?新形势下,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又会如何走?
首先,伊朗已经开始在国内、地区和国际这三个层面上重新洗牌,希望止损并最大程度保留其在地区赢得的影响力。以色列虽然仍旧在伊朗的敌对势力榜单上名列前茅,但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土耳其在这一榜单上的排名快速攀升。
在官方场合,伊朗和土耳其两国政界高层还能够保持基本的外交礼仪,但彼此在涉及地区的诸多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在伊拉克,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在过去几年中多次遭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袭扰,体现出的是两国在油气资源丰沛的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尖锐利益冲突。伊朗人眼中,土耳其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和尼尼微省的军事存在对于伊朗在当地的布局构成威胁和挑战。而在土耳其人眼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库尔德工人党在历史上有着不少渊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伊拉克接下来发生不利于伊朗的政治演变,土耳其很可能会努力填补伊朗留下的空白。
在叙利亚,伊朗认为土耳其是阿萨德政权被推翻的幕后黑手,而土耳其则坚信是伊朗从中作梗才导致巴沙尔拒绝与埃尔多安会面、拒绝与土耳其恢复正常关系。
在黎巴嫩,土耳其利用沙特退出黎巴嫩政坛留下的真空,与那些反对真主党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当地的逊尼派政治人物建立起了密切联系。
除了这些阿拉伯国家外,还有一个广义上的中东地区边缘国家也有可能成为土耳其和伊朗关系恶化的导火索——阿塞拜疆。这又与伊朗和亚美尼亚间的关系,与以色列对阿塞拜疆的军事支持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伊朗的国内安全也常常与阿塞拜疆扯上关系。
综上,伊朗国内开始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土耳其未来对伊朗的威胁可能远比以色列更大。
尽管土耳其和以色列经常隔空喊话释放敌意,但这些嘴仗放到当前的中东大环境下几乎不会掀起什么大的水花。以色列“新中东”的战略重点聚焦在打击伊朗,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会给土耳其带去一些利好。此外,以色列还着力扩大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范围。特朗普重返白宫在即,《亚伯拉罕协定(Abraham Accords)》很可能在未来迎来新的阿拉伯国家加入。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在某些方面有交集,比如前面提到的阿塞拜疆,甚至对伊朗的打压遏制。两国也有不少分歧,比如在巴勒斯坦、库尔德等问题上。当前,伊朗影响力大幅下滑,土耳其和以色列将很快发现两国需要面对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竞争还是合作。美国作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域外大国,特朗普2.0版本的中东政策将影响甚至左右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整个中东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地缘格局。
我们作为中东地区的新玩家,如何经略中东也势必要处理好这些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促成沙伊和解是一步妙棋,但走一步妙棋并不难,难的是每一步都不要走出臭棋。什么是臭棋?比如想把巴勒斯坦人捏合到一起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