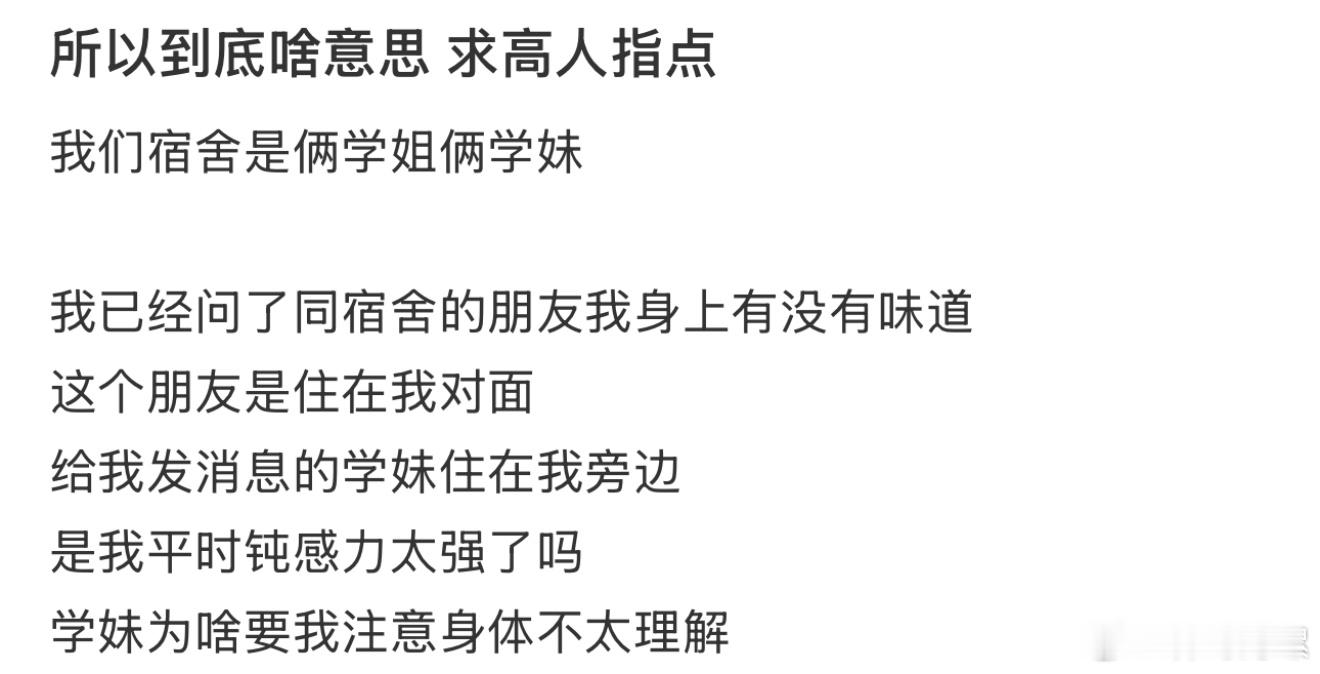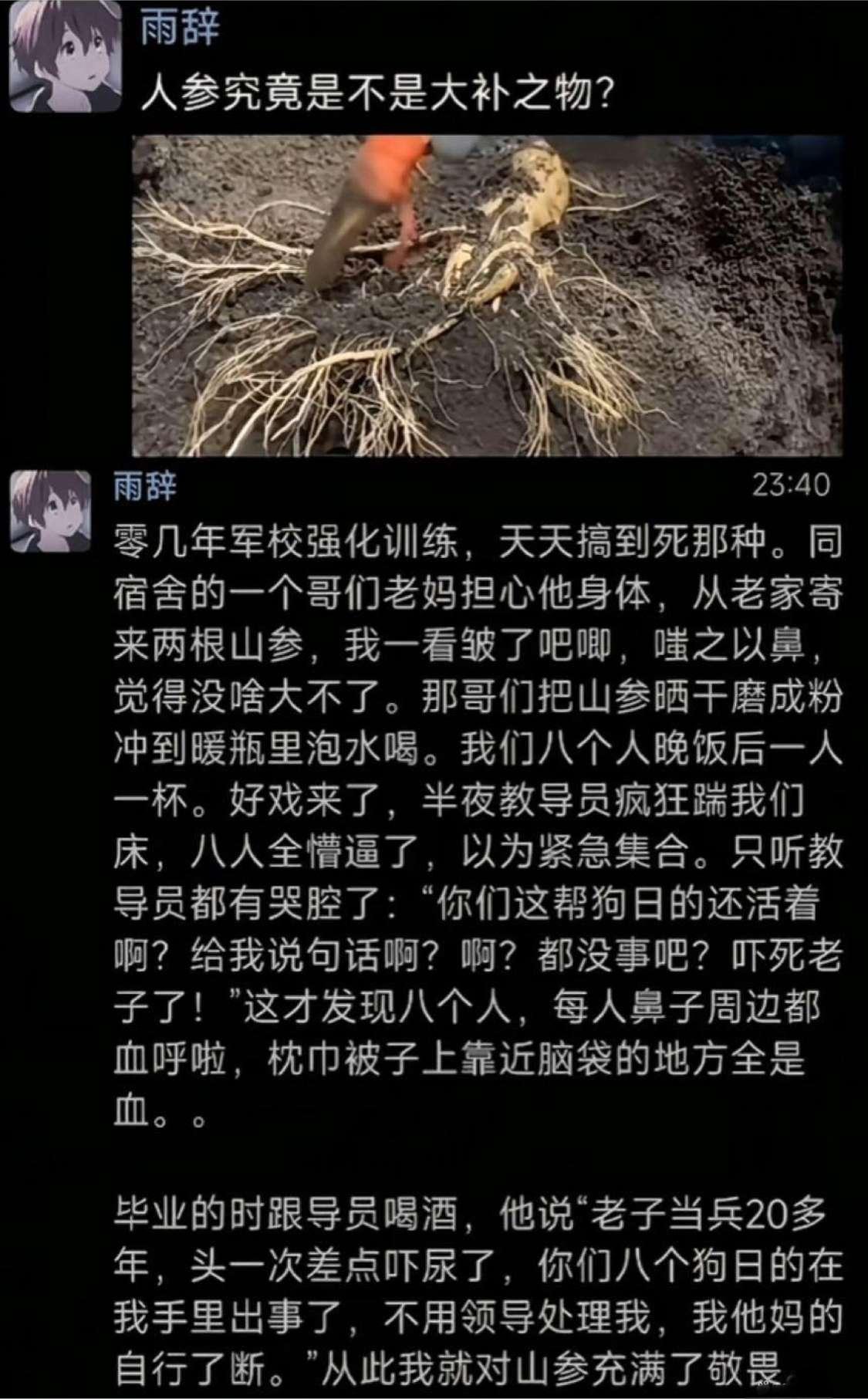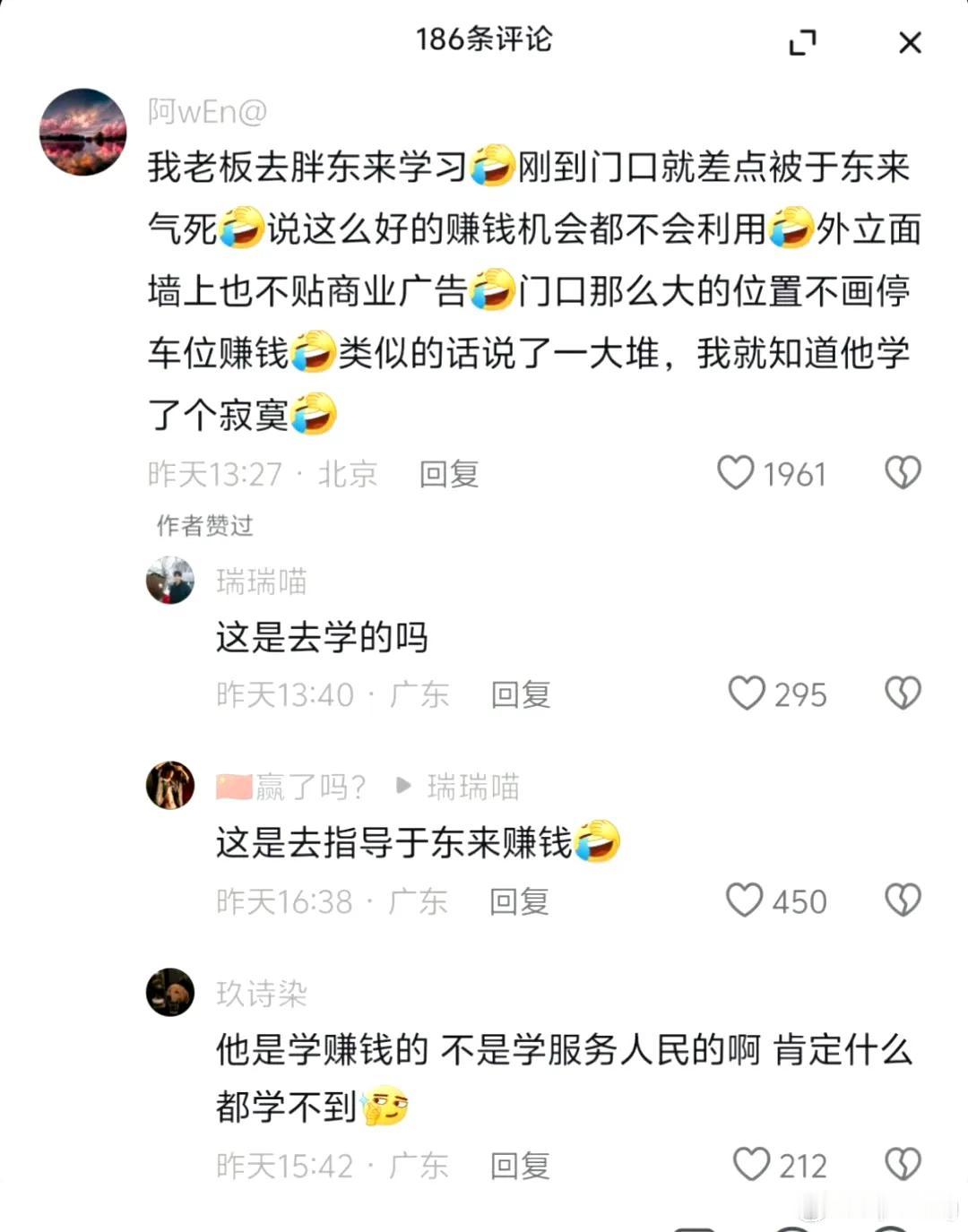《化神》
作者:山栀子

简介:
“她妄图以无情之身,诱他修行毁于一旦。”
——
“听说赵家那个小女儿霖娘不知被什么掏了心,扔进黑水河里死了。”
“谁说的?她根本没死!”
“心都掏了,还能不死?”
霖娘非但没死,还性情大变,穿得春红柳绿,不分昼夜地游荡在黑水河畔。
有人说,她中了邪,丢了魂。
一日烟雨朦胧,一位衣着整洁,容颜秀整的年轻修士来村中义诊。
几个村民帮着赵家夫妇合力将女儿霖娘抓来修士案前。
檐外雨露沙沙,修士伸手摘下她额前的朱砂黄符,问她:“你叫什么?”
她想起自己在黑水河下打瞌睡时曾听一个呆书生背的诗句——
“神丹不老姮娥鬓,乞取刀圭驻玉容。”
她听不懂。
但她缓缓一笑:“我叫阿姮。”
她不是霖娘,而是天生的妖邪。
阿姮想要这个凡人修士的心,来填补自己这副新躯壳胸口的血洞。
——
程净竹师承上清紫霄宫,肩负药王殿重责,为解人间疾苦入世之初,他便遇见阿姮。
她穿得春红柳绿,被人按在他的案前,肆无忌惮地冲他笑,从此以后跟在他身边打转。
见过阿姮的都说,她对一个修道之人痴心一片,实在可怜。
不,她才不可怜。
程净竹一直知道,她那副人的皮囊之下,是妖邪的本源。
“我爱她,
我知道她想要我的心。
但我——绝不会给她。”
——
“神本无相,万法从心。”
精彩节选:
月出东岭,光华淡薄如霜。
霖娘推开自家后头歪斜的柴门,她尽可能地让它发出的“吱呀”声轻一些,只开了一道窄缝,她苗条的身子一侧,很快钻出去。
她家后面是幽僻狭窄的山径,道旁皆是翠绿的松竹,霖娘身上背着一个小包袱,手中提着灯笼往前走了几步,又忽然停住,她回过头去,月光顺着半开的门缝钻入昏黑的屋中,泛着孤清的冷意。
霖娘面上不禁浮出一丝不舍,但想到那个人,她不由抬手摸了一下鬓边的一根木簪,原本伤怀的神情收敛起来,眼睛亮晶晶的,唇边溢笑。
爹,娘。
柳郎要带我出去见一见世面,至多三五个月,我们一定回得来。
霖娘心中这样想,也不再多看家门,转过身顺着那山径去了,夜半露水已生,霖娘提灯照见路边晶莹水泽,她一路行来,裙摆也沾染了不少水痕。
山间薄雾笼罩,霖娘独行其中,穿过遮天蔽日的山林,当中总有些蛰虫鸣叫,她一边往前走,一边又从那虫声里听出些别的声音,她很难判断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却总觉得这林子里有太多双发光的眼睛在窥视着她。
霖娘从未独身走过夜路,此时胸腔中心脏突突地跳,她不禁加快脚步,很快摆脱了昏黑的山林,前头豁然开朗,是一片布满碎石的河滩,一条长河横亘在两片山林之间,月光之下,薄雾之间,河水犹如浓墨般铺陈,泛着粼粼光泽。
河边一棵老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浮动的雾气里,霖娘远远望见树下那道颀长的身影,她顿松了口气,露出笑颜,快步朝他奔去:“柳郎!”
树下的人始终站在那片雾气与月光交织的朦胧阴影里,霖娘走近他,手中的灯笼也很快照见他的脸。
他五官生得俊秀极了,天生透着一股文气,但偏偏他的肤色有些略深,破坏了他眉目几分温润秀致,但霖娘记得,他从前还是很白净的,只是在外头待了几年再回来,就晒成这样了。
但还是很好看。
霖娘扑进了他怀里,他的怀抱其实有点湿冷,还带着些若有似无的泥土味,但霖娘抬头望他:“柳郎,真的三五个月,咱们就能回来吗?”
柳郎闻言,垂眸看她,微微一笑:“不相信我吗?”
“我自然是相信你的,”霖娘摇摇头,又说,“那么多人出去,就只有你回来了,我只是担心,我若出去得久了,爹娘他们……”
柳郎那双桃花眼依旧温润,此时看着她,却有些不解似的,他道:“你是真舍不下爹娘,又何苦与我出去呢?”
“可你说,外面有连接天地的琼楼,有十尺高的巨人,有数不清的瓜果,开不败的花……”
好多好多。
那么新奇的事物,霖娘从来没有见识过,她看向柳郎:“我爹的腿越来越不好了,我看他夜里总是疼得厉害,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去外头给他请一个更好的郎中。”
“柳郎,你说,外面的郎中可以医好我爹的腿吗?”
柳郎总是温温柔柔的,无论霖娘说什么,他那双眼睛都始终柔和地看着她,哪怕不说话,他也依旧有令人心安的魔力,可此刻霖娘在他怀中,仰头与他对望,她却发觉那股熟悉的,令人心安的东西不见了,她手中的灯,天上的月,映照他的神情,竟然与他的怀抱一样湿冷。
可他衣袂分明是干燥的,甚至衣摆也没有沾染一丁点的露水。
霖娘的心忽然突突地跳,他的一只手抬起来,霖娘才发觉他自始至终根本没有回抱过她,他的手指轻抚她脸颊的刹那,那种深邃的冷意刺激得霖娘头皮一麻。
“霖娘。”
河水如墨,月照粼波,柳郎漆黑的眸子犹如不见底的漩涡,河风吹起他的衣摆,他的声音轻飘飘的:“你别走了。”
脸颊上那种手指冰冷的触感没有了,霖娘后知后觉,低头看见自己胸口一片血红,那种红静默地吞噬着她衣襟原本的颜色,湿润地蔓延。
而他的那只手就在她胸口被破开的血洞里。
霖娘觉得自己浑身很冷,像在雪地里被冻了很久,她像一座冰雕,只能僵直地站立,包袱从她肩背滑落,连带着灯笼也一块儿脱手。
灯笼烧起来,连带着包袱一块儿,燃成一簇张牙舞爪的火光。
霖娘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手指攥住了她的心脏,但奇怪的是,她竟然不觉得疼,瞳孔震颤着,她不敢置信地望着面前的情郎:“柳郎,你……”
柳郎淡色的唇微露笑意,手指节蓦地一用力,霖娘终于感受到剧痛,可她已经没有机会叫喊出声,她身体不受控地后仰,倒下去的瞬间,她睁大通红的双眼,看见柳郎那只血红的手攥碎了一团血肉。
迸溅的鲜血顺着他指缝滴滴答答地落,他眼皮沾着血痕,阴冷地凝望她。
“扑通”一声。
霖娘掉入水中,瞬间被浓墨似的河水吞没,鲜血如缕,从她胸口的血洞不断地蔓延,被涌动的波涛铺开。
岸上的柳郎正欲走近水边,但月华映照漆黑水面,水声越发汹涌,他的脸色骤然变了。
河上雾气变得浓烈,灯笼的火光烧尽了,天水几乎一色,波涛汹涌的河水底下一缕黑雾如同游鱼一般疯狂地前行。
黑雾所过之处,浪涛声重。
骤然触碰到如缕的血气,黑雾似乎顿了一下,瞬间疯狂地缠上去,越往前,血气更重,那具人的躯体浸泡在水中,发丝如海藻般浮动。
河鱼涌向她的刹那,黑雾袭来,鱼群瞬间受惊四散开去,雾气迅速包裹住那具躯体,钻入她胸口的血洞之中。
水中弥漫的血气散发出暗红的光芒,星星点点跃出水面,如同在浓雾中穿行的萤火虫。
水下,原本已经失去生息的女子骤然睁开双眼。
“砰”的一声,河面炸开层层水浪,女子破水而出,落身在河岸边上,她发髻已经散了,湿润乌黑的长发披散,一身春绿色的衫裙沾染斑驳血色。
湿润的浅发贴在她苍白的面颊,脚上的鞋子已不知被水冲到哪里去了,她赤足坐在水边上,那双眼珠缓缓地转动一下。
水中,霖娘发觉自己身体变得半透明。
她惊恐地望着自己的双手。
又猛地抬头。
岸上,女子依旧坐在那里,周遭是漂浮的暗红萤光,她胸口的血洞仍在滴血,滴答滴答,点在水面。
月华溶在浓雾里,昏黑的天色,阴冷的波光。
同样的脸,同样的身躯。
她们隔水相望。
“妖怪!有妖怪!”
忽然的尖叫声惹得河滩尽头林中倦鸟惊飞,杂乱的鸟鸣声中唯有乌鸦的叫声是最尖锐的,坐在岸边的女子转动僵硬的脖颈,回头望去。
几只乌鸦扑翅融入树荫,夜雾当中,一道佝偻的背影惊慌失措地朝林子里奔去。
浮烟漫漫,女子看着他的背影,目光又忽然回落至自己春绿的裙摆底下,那一双被浅水浸泡的赤足。
接着,她试探着站起来,勉强稳住身形,她一只脚迈出去,却像个肢体僵硬的提线木偶,或者说,是一个初次尝试走路的婴孩。
一步勉强踏出去,身子立即踉跄不稳,那支松松勾在她湿润长发间的木簪滑下去,落在地上,竟瞬间变作了一滩湿润乌黑的淤泥。
水中的霖娘惊恐地望着那滩淤泥,那明明……明明是柳郎送她的簪子,是柳郎从外面带回来给她的簪子!
柳郎……
霖娘立即朝河边树下望去,浓雾弥漫,那里哪还有个柳郎,月光冷冷地照在碎石滩上,只有那团被碾碎的血肉。
那是她的心脏。
这果然不是梦,霖娘猛地惊声尖叫起来,她想要往岸上去,却像是被层层的水波死死地困在水中,无论她怎么挣扎,竟也激不起河中一点水花。
甚至她撕心裂肺的叫声也不能惊动任何鸟兽,只有岸上那个僵硬站立的女子微微偏头,看向她。
“你是谁?”
霖娘声音沙哑而颤抖。
女子用一双与她如出一辙的眼睛望着她,一粒暗红的莹光犹如萤火虫般忽然飞去水中,覆在霖娘的喉咙。
“你到底是谁?”
霖娘浑身寒刺倒竖,发抖地喊。
暗红的莹光在她喉咙闪动,那女子一瞬不瞬地盯着她:“你……到底,是……谁?”
她学着霖娘,发出生涩的声音。
苍白的唇勾起一个僵硬的弧度。
那应该不可以称之为笑容,尤其是在霖娘自己的脸上,那是诡异的,是不合常理的。
霖娘看着她身上春绿的衣裙,那是她亲娘亲手裁的布料,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但那胸口的血洞却弄破,弄脏了衣裳,但此刻,鲜血竟已不再汩汩地涌了。
“把我的身体还给我!”
霖娘尖叫起来。
可无论她如何拼尽全力,也始终不能靠近岸边一步。
岸边的女子则好奇地审视了她好一会儿,像是终于有点掌握了人类的发声方式,她缓缓开口:“你的壳子,还你,你也回不来。”
霖娘浑身一震,抬起头,涛涛水波尽头,碎石浅滩上,浓雾与月华交织,那女子抬起手,手指沾了一点胸口的血液,她低头,像是因那种血腥的味道而有一瞬沉迷。
霖娘甚至有一种她即将伸舌舔血的预感,但女子并没有那么做,只是双指捻了捻,擦干净了。
“回不去……是什么意思?”
霖娘眼眶通红,泪如雨滴。
岸上暗红的莹光浮动,女子那副与她一模一样的脸却显得诡秘而冶艳,她伸手拂开颊边湿润黏腻的浅发,眉宇是不谙世事的天真:“你已经死了。”
——
天上初日才照,松竹林中一妇人匆忙奔出茅舍,篱笆门外晨雾为散,她在外头站定,四下张望了一番,又赶紧转过身回屋里:“老赵,老赵!”
那老赵拄着一根竹杖,正要往后头去抱柴火,听见妻子的喊声,他回过头来,见她那副慌张的样子,他眉心拢起川字:“又跑出去了?”
林氏点点头。
老赵惯常是个沉默寡言的,这会儿也什么话都不再说,转身一瘸一拐地出去,闷头将柴火抱到灶房中。
“老赵……你说这怎么办啊?”
因为没少哭,林氏的眼睛这些日都是红肿的。
“什么怎么办?”老赵坐在凳子上,将柴棍一根根掰断,“又不是丢了,这些天,咱们捆过她,也关过她,她还不是天天地往黑水河跑?”
老赵年近四十,眼皮还不是很松弛,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黑洞洞的灶口,继续说道:“那日咱们在黑水河边找她回来,她连路也不会走了,还要你手把手地教她走路,至少这几日,她能跑能跳的。”
何止是不会走路,穿衣吃饭,也是样样不会。
林氏走到灶口边上:“可张家和李家那两个烂舌头的媳妇儿正跟人家说咱霖娘的闲话呢,还到处传咱女儿是妖怪变的,老娘真该找上门去,将她们的嘴撕烂了!”
若不是女儿出了事,林氏这副泼辣的性子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哭哭啼啼的,此时一说起那几个长舌妇来,她都快将牙咬碎了。
“都是那柳行云骗得咱霖娘,这种出去过的人,果然换了副烂心肠回来,我早该劝霖娘收心的,”老赵手中柴棍断成两截,夫妇两人之间忽然无比静默,淡薄的晨光从门外斜照而来,落在老赵有些轻微皱痕的脸上,他脸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叹了口气,“如今咱霖娘落水后成了这样,那柳行云又不知所踪,谁知道是不是他害得咱女儿……”
林氏很恨道:“如今村中都在传咱霖娘的闲话,他柳行云一个大男人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他就是钻到地下,老娘也非把他挖出来不可!”
黑水村环山抱翠,清晨的露水还没被日光烤干,晨起吃饭的村中人聚在一个石碾子边上,你一嘴我一嘴地说着话。
“老鱼头,不会是您老眼昏花看差了吧?你说霖娘被掏了心,可这被掏了心的人,还能活着?”
端着碗清粥就咸菜的中年人挨到那浑身鱼腥味儿的老翁边上。
“那比干没了七窍玲珑心,不也能活吗?”
因为他以捞鱼为生,年纪又已接近七旬,所以村中人都唤他老鱼头,他见村邻不信,便将碗往石碾子上一放,接着道:“那天晚上我忘了收渔网,所以才去的黑水河,可还没走到河边儿上,我就看见那树下有一男一女……”
他做足了说书人的姿态,哪怕这几日,他已与这些村邻讲过无数遍:“那男人背对着我,我没瞧清,可那天晚上月光很亮,我看着那女子形貌十分像那赵家的女儿,正要细看呢……突然!”
他声音一瞬放大,哪怕这些村人都习惯了他的一惊一乍,也还是有几个被吓了个激灵,老鱼头又继续道:“那个男人伸手就从那女子胸口抓出来一团鲜红的东西!接着那女子就掉进了黑水河里,我心里害怕,正要跑,哪知道那女子竟然又破水而出,活生生地坐在了岸上!”
“可人若没了心,哪里还能活呢?”
一名村汉并不信他。
可赵家近几日的境况,他们全都看在眼里,那霖娘非但不会走路,要她娘林氏手把手扶着教,教会了,人却天天往黑水河边跑,拦都拦不住。
“我看哪,老鱼头那天晚上见到的年轻男人,也许就是那柳行云呢!”张家媳妇儿说道。
一提起柳行云这个名字,众人面面相觑,那张家媳妇儿继续说道:“咱们都晓得,霖娘与那柳行云早几年就眉来眼去的,分明是彼此有意,若不是柳行云出去了一趟,只怕他们早都成亲了。”
“咱这儿是与世隔绝的地儿,村里出去多少人,都那么不明不白地死了,这么多年,只有他一个从外头活着回来,他既有这样的本事,说不定是在外面走了什么邪道,要不然……霖娘怎么如此疯傻?”
李家媳妇儿拧着眉接话道:“这几日,你们有谁见过柳行云?”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摇头。
那老鱼头想起那夜,他单单只看那男人的背影,便心有余悸,柳行云回来的当日,在村长家中露过面,老鱼头想了想,似乎和那晚的男人身量真的差不多,他心里突突地跳,半晌,吐出一口浊气:“还是村长说得对,凡是出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众人心中裹覆阴寒,脸色都不太好,他们虽并未尽信这个爱喝酒,爱说大话的老鱼头,但霖娘中邪,却是实打实摆在他们面前的。
天上忽然落下小雨,细微的沙沙声中,村人本欲四散,各回各家去,却忽然听得一阵清脆的清音。
那是珠玉碰撞发出的声响。
小雨如细丝,四下雾色朦胧,众人转过脸去,只见那潮湿的雨雾中,一道高大的身影缓步行来。
他衣袖的白,几乎要与雾气相融。
他越是走近,人们便越是看清他银灰色的长发,半梳成发髻,戴白玉莲花冠,余下一半皆披身后,长长的发带随他步履而动,飘逸非常。
冷白的皮肤,清绝的骨相,他的五官是极致的漂亮,但这种漂亮,是不染尘垢的,人们看到他眉心一点红色的印记,那印记更衬他不食烟火,宛若临凡圣者。
那是一种天然的神性。
他雪白的襟前是一串水青色的珠串,哪怕是在雨气里,珠子也颗颗晶莹剔透,好似将澄澈的湖水盛满其中。
他倏尔抬眸,越过诸般目光,望向远处苍翠林木,蜿蜒山道尽头,依稀可见横贯两峰之间的那条黑水河。
仅仅一眼,他收回视线,
他停在人们面前,一路从山道行来却并未使他脚染分毫尘泥,人们几乎不敢呼吸,怔怔望着这个陌生的年轻人。
细雨沙沙,他略微低首,胸前的珠串轻响,人们此时方才发觉他身后还坠着一条翠绿宝珠背云。
他开口,嗓音如磬:“可否向诸位讨碗水喝?”
黑水河畔,烟波粼粼。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做人,不是什么难事。”
氛雾弥漫,霖娘几近透明的身躯半隐水面之中,她仰面望向岸上的女子:“你何时才肯救我出水?”
时至今日,霖娘仍不能习惯如此直面岸上那张她自己的脸,那仍旧是一张鲜妍的脸,相反,水中的霖娘却变了些样子。
她在水中断气,死后自然化为水鬼。
她的头发变得很长,皮肤惨白,额头还生出些像细小鱼鳞般闪闪发光的印痕,半个身子都融在水中,仿佛水便是她的双腿,也因此,她离不开这条阴冷潮湿的黑水河一步。
“你生来就是人,”
岸上的女子虽然皮肤苍白,却仍有血气,她的笑容不再僵硬诡异,反而烂漫极了,“不论你们做什么,都是你们人的本能,对你来说自然不难。”
她垂眸看了一眼纤细白皙的手指间缠绕的乌黑发丝:“可我又不了解你们。”
霖娘在水中看她,几乎是她话音才落,女子抬起脸来,那双琥珀色的眼瞳顷刻闪烁暗红的光芒,与此同时,一阵轻烟仿佛自她袖中而出,混入河上雨雾,却钻入水中,顷刻搅动波涛万顷。
水声剧烈激荡,霖娘猝不及防地被上涌的河水托起,那烟雾竟然裹住了河水,连同她在其中,不受控地飞向岸边。
轻烟擦过岸上女子腰间衣料,瞬间化为一只通体暗红,精致小巧的葫芦,将霖娘连同河水收入葫芦中。
而浑浊的雾气中,黑水河的水面竟低下去一半,裸露出河岸底下更为湿润的泥土。
女子摸着腰侧的葫芦,缓缓转身。
她才走出几步,沾了雨滴的耳朵倏尔轻动一下,她抬起那双暗红的眸子,望向不远处的那片林子。
林中杂声渐起。
很快近了。
那是人纷杂的步履声。
他们接二连三地钻出林子来,冒雨往河滩上跑,老鱼头最先看见站立在不远处的那个女子,她穿着绯红的衣裙,又配着一件翠绿的外衫,臂上还挽着鹅黄的披帛。
真可谓是一种惨不忍睹的鲜艳。
老鱼头看见那女子的双目,竟然是暗红的,他倒吸一口凉气,抹去松弛耷拉的眼皮上的雨水,再定睛一看,那女子眼瞳盈盈,犹如点漆。
原是他看错了。
但老鱼头心中仍突突地跳,身边几个年轻人也瞧见那女子了,他们连忙奔过去喊:“霖娘在这儿!”
十几个村民很快将女子团团围住,女子那双眼睛一一扫过在场这些人的脸,她可以看清他们或松弛,或紧致的皮肉,或清明或浑浊的眼睛,但她暂时还不能彻底分辨人类的样貌的不同。
不过都是一双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
湿润的衣袖间,女子苍白的指节轻轻一动,暗红的莹光时隐时现,正是此时,一个极年轻的男人有些腼腆地走近她一步,说:“霖娘,你别怕,咱们这儿来了位小神仙,说不定能治你的邪……不,治你的病!”
霖娘是黑水村中最美丽的姑娘,没有哪个黑水村的年轻人心中不喜欢她,这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在她面前,又是脸红红,又是结巴:“是……是啊,霖娘,兴许教那小神仙看了,你就好了!”
“都让你不要这么穿衣裳,这些颜色都是我娘裁了我不喜欢的,都压在柜子最底下,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翻出来的……”
霖娘有些发闷的声音自葫芦中传出:“你每日穿成这样到处跑,难怪村邻都觉得我中了邪。”
“不好吗?”
女子垂眸看向这身鲜艳明亮的衣裙,她有些不解。
没有人听见霖娘的声音,几个年轻人只听见女子这一声突兀的问话,他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个挤出笑容,道:“好,我看好得很呢!”
霖娘亦是黑水村中最会精心装扮自己的姑娘,以往谁也没见过她如今这样一股脑儿地将所有鲜艳的颜色都往身上披,看起来十分不伦不类。
但即便如此,她也依旧拥有一副美丽的容貌。
女子听见他的话,一瞬将那双水盈盈的眸子看向他,朝他露出一个笑容。
那年轻男人的脸瞬间红透了:“霖娘穿什么都好看!好看极了!”
他显然已经因为女子的笑容而迷醉。
葫芦里,霖娘发出崩溃的声音:“男人的破嘴!”
“霖娘!”
忽然这样一声唤。
连绵细雨中,女子还没抬起头,葫芦中的霖娘已经激动地出声:“娘……是娘的声音!”
老赵腿脚不便,林氏扶着他姗姗来迟,女子抬眼看向他们的刹那,那老鱼头跟条泥鳅似的,很快上前扯开几个只知道傻笑的小子,“啪”的一声,一道朱砂黄符骤然拍在女子前额。
老鱼头飞快地缩回手,却撞上黄符之下,那女子的目光,他心中蓦地一窒,竟然软了双腿,一屁股坐在了泥地里。
“老鱼头!我女儿只是病了,你干什么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林氏见此,怒不可遏。
“老赵媳妇儿快别生气!”
一个老翁见她挽袖子,便上前拦住她道:“这会子最要紧的,还是快让那小神仙给霖娘瞧瞧,不论是病还是……反正,兴许他都能治呢!”
那老赵听了这话,便握住林氏的手,随后他抬头,看向那穿得春红柳绿的女子:“霖娘,跟爹回去,就让那神仙瞧一瞧,也好教人放心啊。”
女子并不说话,却也没有动。
老赵与林氏干脆上前,一左一右地扶着女儿,一边轻声哄她,一边带着她跟村邻们一块儿往回走。
黑水村中有一座常年上锁的庙宇,庙门前,人们已经排起了长龙,这点细雨,他们连伞也不撑,全都伸长了脖子去望屋檐底下。
檐下,一张简陋的桌案后,那是一个衣衫胜雪的少年,说是少年,却又不知为何头发银灰,人们见他胸前一串宝珠剔透,而他抬手搭脉时,衣袖边缘又露出一截冷白腕骨戴着如盛绮霞的手串,随着他的动作,淡色的流苏偶尔扫过桌面。
他身上一点尘泥都没有。
哪怕是这样的雨天,他的衣袂,脚上也不沾分毫湿泥。
久未在人前路面的老村长此时坐在檐下另一端,双手撑在拐杖上,沉默地注视着那个凭空出现,又在此义诊的外乡人。
很快轮到一名年约十二三岁的少年,他却并不凑近案前,只站在雨里,十分好奇地打量着那年轻的修士,小心翼翼地说:“神仙爷爷,我没病,是我爹,我爹他身患腿疾,不良于行,我又搬挪不动……”
“我说过了,我并非神仙。”
年轻修士抬眸先是看了他一眼,随后又往他身后望去,这些黑水村人当中竟有不少男人拄拐:“你可请人去将你爹带来。”
少年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好说话的神仙,因为他并不慈眉善目,反而眉目冷得像雪,那双眼睛看着人时,亦无分毫波澜。
但少年才见过他用一副金针就让几个跛脚的村邻嘴里不再喊疼,他立即请了几个相熟的长辈,赶紧跑回家去。
“村长,您也来看看吧!”
队伍里,忽然有人喊道:“我看这位外头来的小神仙是很有本事的!”
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去檐下,那位黑水村的老村长天生一副不苟言笑的脸,松弛的眼皮半遮他的眼瞳,使其看起来更加严肃。
一直站在他身边的儿媳妇垂眸看向他。
老村长像是年纪大了,反应有点慢,这种迟钝却削弱了几分他那副皮肉堆起来的严肃,他后知后觉地对上那年轻修士的目光,覆盖着老年斑的手不由摸了摸自己的膝盖,道:“我不急……”
话还没说完,众人却听雨中一阵纷杂的声音近了,有人转过身去,只见一群人簇拥着那穿红披绿,无比显眼的女子过来。
年轻的姑娘和妇人们艰难地将目光从那位年轻修士的脸上挪开,看了过去,一见那乱七八糟的鲜艳颜色都堆在那女子身上,她们不由轻声发笑。
但又见女子前额的黄符,她们又心中发怵,不敢再笑。
“你别生气,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爹娘,不要伤害村邻……”
葫芦里,霖娘喋喋不休。
女子被一行人拉到队伍中去,她脸上一丝笑意也没有,黄符之下,那眉宇隐有一分不耐,老赵与林氏毫无所觉,一人抓着她一只手臂。
老赵低声哄她:“霖娘,咱们就是让那神仙看看,你放心,爹还有些璧髓……”
“老赵,哪用得着璧髓啊,这外头来的活神仙,什么也不要你的!”那老鱼头拍了他后背一巴掌。
老赵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不要璧髓?”
“真不要。”
老鱼头说道。
女子听不懂他们所说的璧髓是什么,她见老赵扬起笑脸,眼尾的褶子深了几分,再抬起头,她发觉很多姑娘妇人都在望檐下的人。
他们说的小神仙。
前面有好些比她这具身体高大许多的男人,她起初并未看清那人的脸,只见他衣袖很白,像她在黑水河中无数次仰望过的云。
直到前面几人让开,中间有一瞬多出一道缝隙来,女子看清他的头发,和年轻的人类不一样,和年老的人类也不太一样。
天气最冷的时候,黑水河中曾结冰,正如这神仙的眼睛令人生寒,但偏偏他的眼比他胸前那串剔透的宝珠还要漂亮。
女子手指间悄然跳跃的暗红莹光忽然消失了,她指尖轻扣腰侧的葫芦:“什么是美丑?”
老赵与林氏正与前面的村邻说话,没人听见她这声低语。
葫芦里,霖娘有些摸不着头脑:“……什么?”
暗红的浮光微闪,霖娘几近透明的身体如雾般轻飘飘地从葫芦里钻出,河水托着她的身躯悬在半空,而无一人察觉。
霖娘第一眼最先看到自己的爹娘,她眼眶中顿时含泪,作势要喊,却听女子轻快的声音响起:“你说,他是美是丑?”
霖娘茫然地抬起一双泪眼,视线越过人群,落去檐下,朦胧中只见那年轻修士一副轮廓,她便立即将眼泪挤出眼眶。
视线终于清明。
霖娘倒吸一口凉气:“这……当然美!”
“美极了!”
她忍不住强调。
女子闻言,再度抬眸看向那修士,忽然间,她觉得人类的五官也不是那么难以分辨。
腿病不是那么容易治的,那修士不过只号了号脉,便让前面那些一瘸一拐的男人到一边坐下,很快,老赵见前面没人了,便一瘸一拐地拉着女儿上前:“神仙,还请神仙给我女儿瞧一瞧……”
雨水顺着檐瓦下落,滴在底下的缸中,竟如黑水河的水一般浓烈如墨,但人们显然习惯了这黑山黑水的黑水村,这一点也不稀罕。
稀罕的,是那位坐在破桌前的神仙,还有,那额头贴着黄符纸,在雨中一动不动,浑身色彩明亮的女子。
没人敢真正靠近霖娘,只有林氏紧紧抓着她的手,正要哄女儿上前,却见她自己忽然动了。
被打湿的黄符分明遮住了女子的眼睛,但她依旧自如地缓步走到檐下,那雨水顺着她的发,没入她苍白的颈项,鲜红的绣鞋边沿抵在石阶下,她像是一个踉跄,倾身倒在桌上。
年轻的修士轻抬起浓密的眼睫,注视着她额头那张朱砂黄符,他起初没动,只将手中一粒圆润冰蓝的珠子捏碎。
碎裂的珠子尖锐的棱角划破他的指腹,一滴鲜血的血冒出,他却眉眼未动,只将碎屑丢入琉璃盅,里面不知是什么液体,碎屑落进去,瞬间都融化了。
黄符纸下,女子被遮住的一双眼睛骤然闪动暗红的光芒。
修士伸手,摘下她前额的黄符,顷刻露出女子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睛。
雨水沾湿她的鬓发,濯洗过她美丽的面容,檐外雨露沙沙,修士提笔,预备录名,又垂眸看她:“你叫什么?”
人类都有名字。
女子无端想起自己在黑水河中打瞌睡时,曾听一个抱着书本摇头晃脑的小书生反复背过一句诗——
“神丹不老姮娥鬓,乞取刀圭驻玉容。”
她听不懂。
但她缓缓一笑:“我叫阿姮。”
她的目光始终停在他指尖的血珠,因为他握笔的动作,那血沾上了笔杆,越是看,她喉咙越是渴。
她的脸,离他的手很近,仿佛只要再近半寸,她的唇就会触碰他手中的笔,而她多么想要舔干净那滴血。
“什么阿横阿竖的,老赵,你家霖娘果然中邪了!”
老鱼头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惊叫一声。
人们一时间不由退得更开些,脸上或多或少的,都带了些惊恐,就连坐在一边的老村长眼睛也睁大了些,上下打量着那霖娘。
“……都让你不要乱说话了。”
霖娘看着爹娘惊疑的模样,声音有气无力。
年轻的修士纹丝未动,他沉静的眸子有一种天生的冷漠,修长的手指随意地一动,鲜红的血珠被他抹了个干净,他搁下笔,就着那张黄符,沾着琉璃盅里蓝色的液体,手指在黄符上描画几笔:“中邪倒不至于。”
他的语气平静。
将黄符递到老赵手中,道:“回去烧了,化水服用,可以固魂。”
老赵忙双手捧过,连声道谢,正要拉着女儿走,林氏却拦住他:“快让神仙也看看你的腿!”
老赵这才看向那修士,却听他道:“坐下。”
老赵不明所以,却也老老实实地与那些个都有腿疾的男人一块儿排排坐,阿姮被林氏扶着,此时抬眸一扫,方才注意到这些身患腿疾的人,竟有几十人之多。
“将裤腿卷起来。”
修士手中握着那琉璃盅,道。
几十个男人听了,立即将裤管卷起来,发灰的天色底下,他们有的人是左腿,有的是右腿,或膝盖以下,或连着整条腿,皆是一片青黑的颜色。
非但如此,他们附着青黑颜色的腿明显比另一条腿要枯瘦许多,颜色只到膝盖底下的人还好些,那些年老的,整条腿都青黑了的,皮底下,只剩骨,奇怪又诡异的骨刺从里面刺破皮肉,长到外面来,虬结得像树根,蜿蜒蜷缩,又像人没了皮肉,只剩森白骨头的手。
畸形而可怖。
阿姮却看得饶有兴味,她一一扫过这些人的腿,又落在老赵身上,老赵还算年轻,那骨刺还没长出来,皮底下还有些肉,青黑的颜色只到他膝盖底下。
“骨刺不除,药石无医。”
那修士并未露出分毫或嫌恶,或惊惧的神情,他十分平淡的在这些人中来回扫了一眼:“你们自己来,还是我来?”
此话一出,众人脸色大变。
周遭忽然静了下来,唯有细密的雨声依旧,那老村长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双掌撑在拐杖上,沉声:“外乡人,你可知这是什么病,就敢贸然让他们除骨刺?”
“神仙,您不知道,这是山神给的诅咒。”
一个坐在后头的老翁,一条腿基本只剩下松垮垮的一层青黑色的皮,骨头细得可怕,骨刺虬结在他腿肚子底下,他哑着声音道:“我们叫它青骨病,凡是想要离开黑水村的人都会死,非但他们会死,他们犯下的错,都会报应在自家人的身上。”
“之前不是没有人自个儿动手除了骨刺,”老翁坐在椅子上,半边裤管空得厉害,他抬起头,“可骨刺除了,还会长,会更快地往上长,直到这刺在里头戳烂五脏六腑……人也就死了。”
那修士从简陋的桌后出来,手中持那琉璃盅,竟有一种身持法器的庄严,他眉清目冷,轻抬下颌:“我有我的办法,你们试,还是不试?”
口口声声喊人家神仙,但到了这个当口,谁也没那个勇气在此人手中赌命,他们面面相觑,一时间都静默了。
“我先来试!”
老赵忽然打破沉默。
“老赵……”林氏心内一紧,握着阿姮手臂的手一个用力。
阿姮看了一眼她。
“担心什么?我都还没开始长那骨刺,”老赵安抚她一声,又看向自己身边的村邻,比他年长一些的人已经从皮肉底下冒出来尖尖的刺,“以往,咱们连赌一把的机会都没有。”
这话戳中了好些人的心。
但他们还是沉默。
修士垂眸,看向老赵青黑的小腿,他没有骨刺,自然用不着切除,他手指轻蘸琉璃盅里蓝色的水液,顷刻掸出去。
不过一滴水珠落在老赵腿上,他几乎还没反应过来,便觉得自己小腿竟莫名变得无比清凉。
水珠滑落的瞬间,在他小腿上划出一道纤细的血口子,血液争先恐后地涌出来,修士走到他身前,匕首自袖中出,刺入血肉,直逼腿骨。
人们屏息注视着这一幕,不少姑娘妇人都偏过头去不敢再看,林氏满眼含泪,伸手去挡女儿的眼。
阿姮看得津津有味,却忽然被林氏挡住视线,她偏过头,见林氏落泪,索性往旁边挪了一步,继续看。
修士的匕首刮过老赵的骨头,鲜血更涌,但老赵却毫无知觉似的,只是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地看着自己的腿。
直到蓝色的水液浸入伤口,老赵终于感受到一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就像是他整个小腿都被架在火上烤,他难耐,他青筋暴起。
修士的刀锋撤出,血红的肉里,竟然淌出来青黑色的液体,滴落在地上,犹如水入火中,发出“滋”的声响。
“他腿上的颜色淡了!”
有人惊奇地喊道。
所有人都清楚地看见,老赵小腿上青黑的颜色渐渐减淡,待修士给他止血包扎过后,他的小腿竟一点青黑都不见了。
“多谢神仙,多谢神仙!”
林氏见此,喜极而泣,不由俯身大拜。
修士回身看她一眼,目光又倏尔落在她身边的阿姮身上,但仅仅只是一瞬,他道:“带他回去,卧床三日,不要挪动。”
林氏连忙应声,起身一手扶着丈夫,另一只手拉着阿姮往回走。
“神仙爷爷!也救救我们吧!求您,求您……”
檐瓦底下,人群当中爆发出迫切的声音,他们当中不少人带着哭腔,显然是被青骨病折磨得太久,又看不到希望,此时亲眼看见老赵的腿退去青黑,他们皆激动到失态。
阿姮回头,看见那些饱受青骨病折磨的黑水村人无比激动地从凳子上起身,他们的裤管仍挽得高高的,露出他们青黑的,枯瘦的,畸形的腿,蜷曲尖锐的骨刺。
他们将那年轻的修士围在中间。
跪下去哭求。
细雨绵绵,他却滴雨不沾,衣襟洁白,宝珠剔透,腰间镶宝的银饰闪闪发亮,圣洁如斯:“还没长出骨刺的,此法尽可医治,至于你们这些已经长出骨刺的人,我可暂保你们骨刺不再生,剩下的,再等等。”
回到家中,林氏将老赵扶上床歇息,又赶紧将小心放在怀中的黄符纸拿出来在碗中烧成灰,又冲了水,见女儿喝下去,林氏方才松了口气,又转头去另一边的卧房里看丈夫。
阿姮见林氏走了,便将符水吐了出来。
霖娘还在葫芦里哭:“太好了,我爹的腿没事了……”
阿姮撑着下巴,手指在梳妆台边扣了扣,霖娘便入一缕雾气,从葫芦中钻出来,浮在半空中,阿姮抬眼,见她还在抽抽嗒嗒的,阿姮不明白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么多的眼泪:“若你那晚真出去了,那山神岂不是会报复你娘?”
“不会!”
霖娘抬起微红的眼:“山神对女子有怜悯之心,不会轻易报复女子,只有男子才会被山神迁怒……”
“那你爹是因为谁而被迁怒?”
阿姮问她。
“我小叔。”
霖娘说道:“三年前,我小叔与人一块儿出去,死在外面了。”
霖娘本就觉得她这身衣裳太刺眼,再看到那张跟她一模一样的脸,她就更糟心了,忍不住道:“那神仙虽治得了我爹的病,却看不出你的端倪,但你如今既佯装喝了符水,你多少装得用心些,不要再让人怀疑了。”
阿姮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霖娘也不知道她听没听进去,只能飘着身体干着急,正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好,却见阿姮伸手摸着胸口的位置。
衣衫底下,那里仍是个血洞。
外面晦天暮雨,阿姮想起今日那修士的脸,他的眼睛,想起他白皙修长的指节,微微泛粉的指腹,那一滴沾在笔杆的血。
后知后觉,她觉出一种极为隐晦的,特殊的香味,目光下移,落在地上那滩被她吐掉的符水,她眼底流露出一分后悔的意味。
这符水里,有一丝他血的味道。
“霖娘,”
阿姮忽然唤她一声,手指擦过梳妆台边残留的一滴符水,她缓缓说道,“我想要他的心。”
“……谁?”
霖娘有点没反应过来。
“那个小神仙。”
阿姮说。
霖娘浑身一个激灵,她有些不敢置信似的,早几日这妖怪还美丑不分,怎么这就……她不由道:“你才见他第一面,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
阿姮抬头看她。
他的血有一种奇特的香味,他的心应该是一颗上好的心,若是用来填这具壳子胸口的血洞,那么她便可以一直寄居其中。
霖娘沉默一瞬,阿姮虽占了她的身体,但说到底,此事并非是阿姮的错,而她虽不清楚阿姮到底是个什么,但这些天她也能感觉得出,这阿姮十分不谙世事,纯真至极,霖娘又想起自己是如何化为水鬼的,眼中流露悲伤之色,便也与她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听我一句劝,情,不是好东西,人心隔肚皮,你并不了解他。”
“那就掏出来看看啊。”
阿姮一手撑着脸。
“……能别说‘掏’这个字吗?”
霖娘的脸扭曲了一瞬,她是正儿八经被人掏了心的,还是被情郎掏的,如今听见这个字就心中犯怵,但此时,她并不以为阿姮说的也是这种“掏”,还以为她初识美丑,便为色所迷了。
阿姮又问她:“情是什么东西?”
霖娘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这些情啊爱的,她哪能轻易说得出口呢,憋红了脸颊,好一会儿才支支吾吾地说了句:“就是那个,你方才说的,你想要那小神仙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