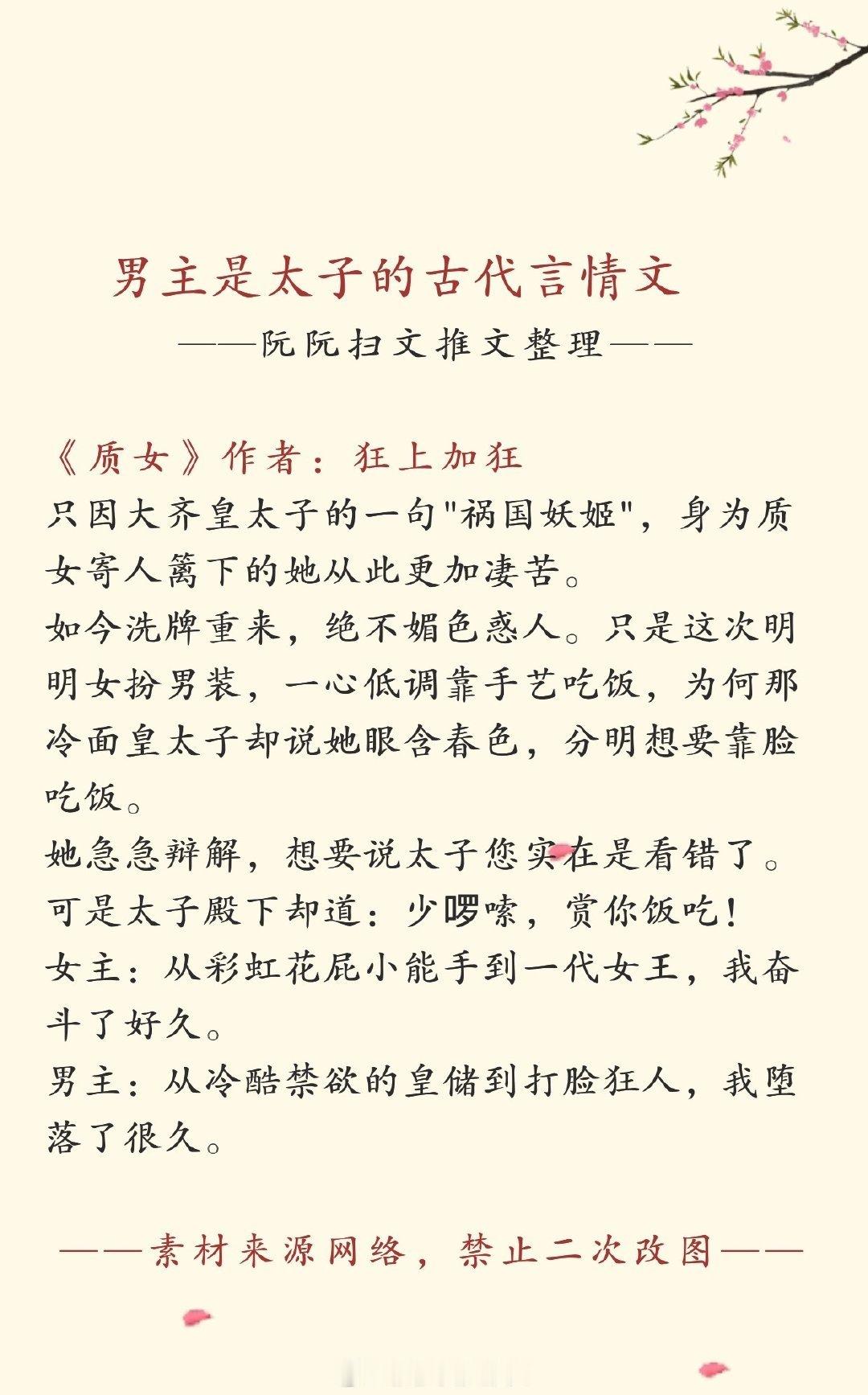成亲那日,太子丢下我去看装病的白月光。
我直接穿着喜服追在他身后:
「好啊,在妹妹屋里洞房更刺激~」
太子骂我疯癫,以为我爱惨了他。
可在他登基那天,我双膝跪地,手捧休书:
「臣妾恳请陛下废后!」
他却不愿放手让我走……
1
喧嚣的宾客已经散去,入夜良辰,龙凤烛下,太子陈寒揭开了我的盖头。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冷冷的眸子,随即盖头被没好气地扔到了床上。
来人正是我的夫婿,东宫太子殿下。
「我喜欢的是王怜,是父皇让我娶你的,我不会碰你,也不会赶你走。」
「但别期望本宫会对你产生感情,本宫只有王怜。」
哟,这太子连装都懒得装了。还在这扮深情种。
也好,省得我和他虚与委蛇了。
得得得,深情戏码就不用给我看了,不耐烦地点点头:「嗯知道了!」累死了,我要睡觉了,你别瞎咧咧了。
沉沉的凤冠压得我头疼,卸下冠带,脖子终于松了口气。来之前我就知道了,做好了心理准备,本以为陈寒至少会和我应付一番,我们二人做一对客气的夫妻也能勉强过得去。
但他这样一说,我们之间的那层面子也就撕破了,正好不用陪他啰嗦。也不用洞房。
他对我没意思,我也不拿他当外人。自顾自脱下外袍就要往床上钻。
屋外传来婆子的嚎叫:「殿下,不好了,才人又病了,您且去瞧瞧。」
还伴随一阵哭腔。
这态势,不知道的还以为要咽气了呢。
还好我知道。
陈寒闻言脸色焦急,甩开袖子拔腿就往屋外去。
「站住!」我头也不抬,一声喝道。
陈寒转身看着我怒气升腾:「怜儿有事,我没空搭理你!」
我冷笑一声:「殿下若今天出了这个门,我们就绝了这桩婚事!」
陈寒闻言瞪大了眼,怒气比方才更盛:「你说什么!你这悍妇怎能如此不讲理?!」

「我不讲理?太子殿下也不看看自己是否还有半分理性!」
「我是殿下明媒正娶的太子妃,太子对我却没有半分尊重和情义可言。」
「新婚之夜,只因宠妾一句抱病就要弃我而去,留我一人独守空房。」
「太子殿下置太子正妃之位于何地?置我广陵侯府于何地?置我于何地?」
「太子殿下丢得起这个人,我广陵侯府可丢不起这人!」
陈寒被我的夺命连环问敲打得涨红了脸,死死地捏着拳头,却发不出一句话。
婆子见状,又接起了前面中断的嚎叫声,一声比一声烈。
好家伙,这新婚夜真热闹。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丧礼呢。
见陈寒拿不定主意,我向前再逼近一步:「殿下今日要是出这房门,莫凝即刻就与殿下和离。」
「若是圣上知晓今晚发生的事,想必也不会怪罪于我。」
陈寒一双眼睛瞪得通红:「你不要发疯了!」
我平静得很,是你们的皇帝陛下求我嫁给你,不是我求着嫁给你。
「殿下且试试看,我们将门儿女说得出便做得到。」
我两眼瞪着陈寒,丝毫不退缩,别人畏惧他是太子,我可不怕。
我乃广陵侯府嫡女,我广陵侯府多是征战沙场的男儿,自父兄牺牲后,侯府只余下我一个。
我身为女子,虽能文能武,却没法和父兄一样建功立业。军中也有好男儿,可这个世界的女子命运却不由自己做主……
当今皇上膝下唯有这一独子,极尽宠爱,导致太子骄奢不堪大用,于是,皇帝打上了我的主意。
明争暗夺,将我许给了陈寒做太子妃,嘱咐我好好教导太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一个女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为了广陵侯府世代荣耀,为了大陈后世安稳,我忍了,嫁了。
反正我最爱的男儿,永远不可能来了。
但这陈寒却是个拎不清的。
他今日出了这房门,明日我广陵侯府就会成为天下的笑话。
这屈辱,我不能受。
眼见陈寒没了动作,我递给春蝉一块腰牌:「去,拿这腰牌,把太医院的林太医请过来,就说东宫的王才人病了,请他速来,让他今夜就歇在东宫,以防万一。」
王怜身子弱,我一早打听到了。

那王才人家世低微,父亲只是东河县的七品县官,这才人之位已是高攀,怎轮得到太医来瞧,我这已然是给了她莫大的脸面。
那婆子还在嚎哭,我瞥了一眼;「不怕你家主子死了吗,还不去跟着春蝉请太医。」
婆子巴巴看着陈寒,跪在地上不肯挪动:「殿下,才人她……」
我向春蝉使了个眼色,春蝉厉声喝道:「太子妃娘娘已经赏赐了腰牌,请太医来给你家才人照看,怎么?太子殿下是大夫?去了你家才人才能好?」
那婆子一口气哽在喉头,生生说不出话来。
陈寒只死死地抿着唇,也不敢再有所行动。
春蝉替我们关上了房门,我爬到床上,陈寒直直坐在椅子上,连个眼尾都不给我。
「你真是个刻薄的女人。」
大婚之日,礼仪繁琐,我实在累得紧,只得敷衍他:「是是是,我是毒妇,你既不愿合离,凑合过呗,还能咋的?」
陈寒:……
我倒头要睡了,他要坐一晚上当菩萨,那是他自己的事。
2
第二日一大早,天刚微亮,陈寒就迫不及待地出了房门。
我让人房内不准留被,那椅子又冷又硬的。后半夜他实在是扛不住,和衣睡在了我旁边,我无所谓,反正我睡得很好。
这太子对王怜倒是一心一意。
陈寒上朝前赶去了王怜那处,不用想也是去哄他的心肝,我懒得管,由着他去,只让春蝉替我梳妆。
如今这东宫只有我和王怜两位,她今日还得来向我请安。
谁知没等来她,倒是等来了昨夜那个婆子:「参见太子妃娘娘,我家才人身子不适,今日就不来请安了,已经特向太子殿下禀明了。」
这是哪门子事儿,给我请安不向我请示,去告诉太子替我答应,直接就不来了,反了天了。
我浅浅道:「既然太子妃不来给我请安,那我便去瞧瞧她吧,她身子不适,理应关照。」
那婆子一脸惊恐地抬头瞧我,半晌才嗫嚅着道是。
「春蝉,昨儿个林太医守在这,叫他一并去王才人处吧。」
春蝉点头离开。
那王怜的住处倒是奢华,陈列摆设,比我那正宫还要上档次,不愧是陈寒的宠妾。
王怜见我来了,一脸惊讶。本无血色的脸上更添了几分惨白。看起来倒真像是病了。
见着我,王怜装作几欲起身,却堪堪又坠回床榻之间:「太子妃娘娘恕罪,嫔妾身子不适,实在是难以下床。」
我摆摆手:「无妨,身子不适就不必拜了。等养好了身子该拜的一份都不会少你的。」
「林太医,再给王才人瞧瞧,到底所患何症啊?」
那林太医擦擦脑门的汗,昨夜就已经瞧过了,无事却还留他夜宿宫中,今日我又亲自请来,没事也得有事。
林太医把把脉,王怜在一边假意咳嗽了几声。
「回禀妃娘娘,才人乃是心火气旺,喝点败火清热的汤药即可。」
我笑了笑:「那就是无甚大事了?」
林太医一脸尴尬,说话都哆嗦了起来:「才人娘娘身子柔弱,不算得什么大事。」
王怜有些急了:「胡说,妾身病得紧,昨夜都呕出血了。」
林太医急忙跪下,双手伏地:「是臣无能,诊断不出得的什么怪病。」
王怜入住东宫一年多盛宠不衰,这林太医也是得罪不起。
我摆摆手:「罢了,林太医辛苦了,回去吧。」
这林太医赶忙拎着药箱拜别,逃离这是非之地。

3
我且悠悠坐下,端起茶杯:「既然连宫中太医都诊断不出妹妹所患何病,妹妹还呕血了,殿下知道了如何放心。」
王怜唇角含笑,略带挑衅地瞧着我。
我看了看春蝉:「太子殿下此刻正在上朝,无暇顾及妹妹。好在我在军中长大,学了一身医术,不比太医差,正好为妹妹医治医治。」
春蝉把备好的东西拿了上来。
这下轮到王怜急了:「不必了,嫔妾这点小病就不劳娘娘费心了。」
「都咳血了哪能算小病呢?这不连安都请不了了?况且妹妹这般虚弱,怎能服侍殿下?」
「我在军中常为将士疗伤,身边的丫鬟也非寻常,难不成妹妹是信不过我?」
王怜眼见无法再拒绝,只得硬着头皮听摆布。
我上手给她把了把脉,确实是身子虚,寒凝严重,应该是娘胎里带来的。
难怪入东宫一年多,夜夜专宠也未曾有孕。虽不影响日常活动,但难有子息。
王怜低着头,眼珠子乱转。
我朝春蝉使了个眼色:「春蝉,给才人施广陵针。」
春蝉打开布袋,一长串白花花的银针铺在众人眼前。
屋内所有人都惊讶地瞧着我,王怜更是瞪大了眼睛:「这?你们要干什么?」
春蝉抽出几根明晃晃的大针走到王怜跟前:「做什么?当然是给才人治病呀!」
「你敢!」王怜吓得大叫起来,直呼救命,身边的婆子也惊叫护在她跟前。
我几脚踢开婆子,春蝉立马将王怜按在床上,几根大针稳稳扎在她身上。王怜一阵哀嚎,却根本反抗不了,春蝉飕飕下去又是数针,几下的功夫就扎了十几针,才肯罢手。
王怜已经惨叫挣扎的力竭,汗水湿透了头发和衣衫,看着着实狼狈。
婆子被我踢散在地,哎呀着尖叫,吵得我耳朵疼。
王怜缩在床角,一双眼睛含着泪颤抖:「你……你敢这样对我?」
我连步都未挪动:「本宫乃堂堂太子妃,亲自为你诊病,对你,这算恩赐,你不是病重咳血吗?如果还未见好,本宫愿意不厌其烦为你扎上几针!」
王怜闻言脸色惨白,忙下床跪在地上叩头:「嫔妾没有咳血,已经大好了,不必再劳烦太子妃姐姐了。」
「哦?没有咳血,那妹妹就是装病咯?」
「春蝉,赏!」
王怜抬头愣住了。
春蝉走过来,抡起手就给了王怜三巴掌,王怜屋内的人被打懵了。
真当我是泥捏的,区区一个九品县官之女,竟敢到我头上造次!
王怜捂着脸,双眼含泪:「你,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放下茶杯:「我过分?昨夜太子大婚,你装病蓄意将太子从新房叫出,欺骗殿下,欺骗本宫,此罪论礼当杖责,本宫只打了你三巴掌,你说,这是不是恩赐?还不谢恩!」
王怜不敢再顶嘴,跌跪在地上叩头:「多……多谢太子妃娘娘赏赐。」
「既无事,就别成日窝这床上,身为才人,不尊太子妃,目无礼法,将《女则》抄个百遍,好好学学怎么为人妾室。」
满屋的人谁也不敢再置喙。
处置了王怜,真是神清气爽。
「待王怜告完状,让太子到梅园来寻我。」
春蝉点头:「是。」
皇帝身子不好,堪堪四十才有了陈寒这么一根独苗,实在是溺爱得太过,几乎是要什么给什么。
但这样的人,做儿子或许可以,如何做得了君主。
是以成婚前,皇上和皇后让我教导陈寒,皇上年迈,恐要不了多久就要退位,如今的陈寒,怎担得起大陈数万百姓?
4
我坐在梅园雅间吃着点心,看着前方戏台升起一块白幕,皮影戏就位。一位角儿头戴红花,花枝招展,妥妥的娘子扮相,另一位风姿卓越,一身大红婚服,是位新婚郎君。
春蝉俯身看向我:「娘娘,太子到了。」
我只嗯了一声,就见到陈寒怒气冲冲地进了雅间:「莫凝!你实在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