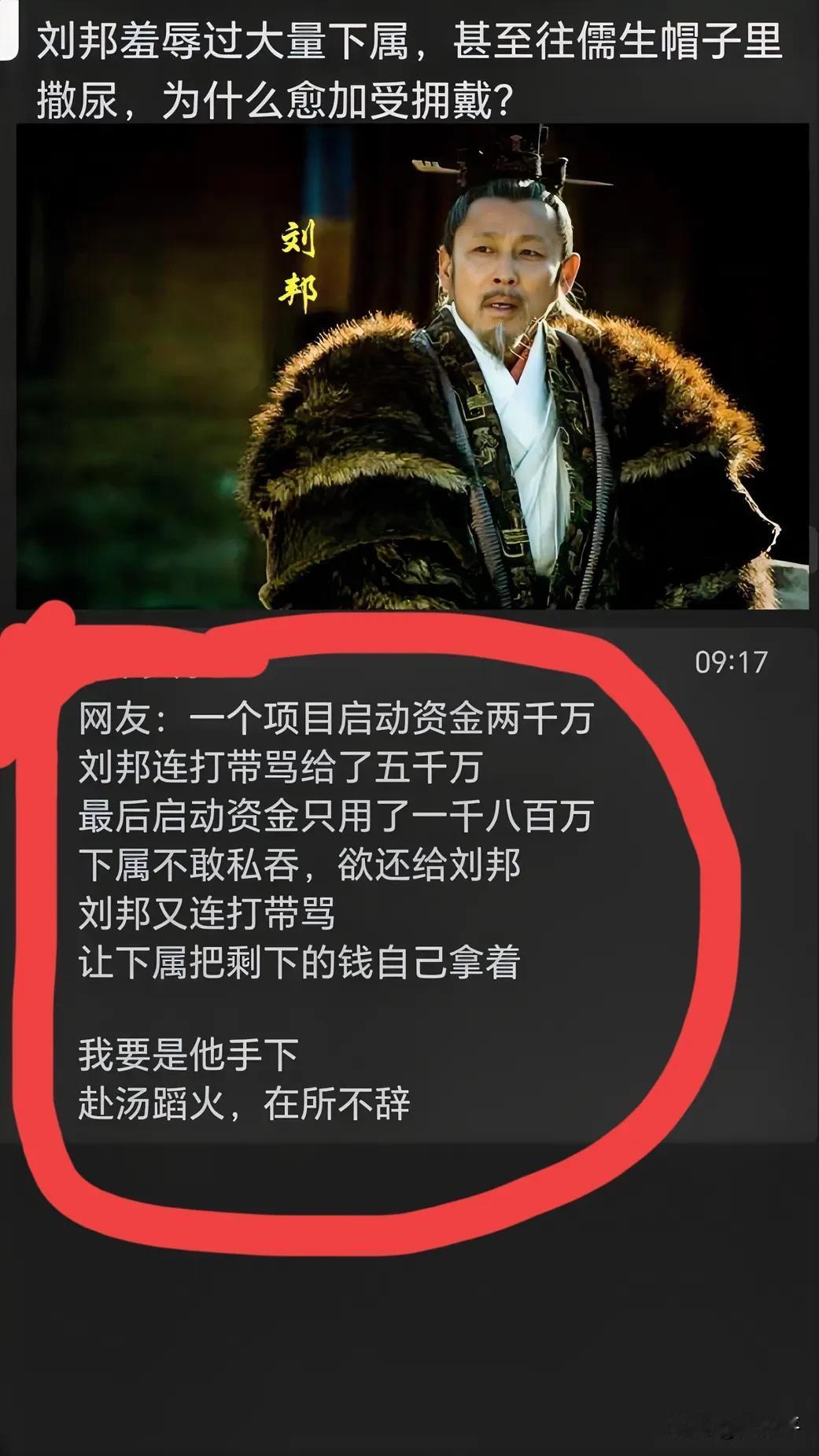1908年11月14日至15日,清王朝最后一位身负改革救国理想的悲剧帝王爱新觉罗·载湉和那个怀有强烈权力欲望并以一己之力将整个国家推向封建专制覆灭的背后推手慈禧太后纷纷驾鹤西去。

一个是曾经变革帝国政体的最大希望,另一个则是变法图强的最大阻力,这对充满争议性的“君后”母子二人集中离去,无疑让当时本就骤然变化的帝国皇权格局变得更加迷茫而充满各种不确定性。
首当其冲的是军机大臣袁世凯。这个曾在“戊戌政变”中向慈禧揭发光绪的“不端”行为而后又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极力推行改官制而成为清朝当权者,尤其是满清皇族成员的众矢之的。其中矛盾最为尖锐对立的当属新登场的摄政王载沣。
载沣与光绪皇帝同父异父,自幼感情基础深厚,目睹了戊戌年袁世凯首鼠两端和临阵倒戈的“无耻”行径后,他内心的仇恨种子也算是彻底埋下了。但真正让他下决心对老袁除之而后快的,却是现实存在的巨大政治威胁。

袁世凯当时的官方身份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对内是仅次于庆亲王奕劻的二号实力派人物,但后者又是公认的为老袁金钱所驱使继而听之任之的存在,因此他几乎成了权倾朝野的人物;对外则一方面通过利益互换与重要省份的封疆大吏结成同盟,另一方面凭借北洋新军创始人的身份地位影响,晚清政权最负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依旧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更重要的是,那个曾经让自己心神不宁的光绪帝和投鼠忌器的老佛爷都已撒手人寰,其余现有的力量再难对他形成致命性威胁了。
大权在握,波澜不惊应该是老袁此时内心的真实写照。相比之下,初出茅庐的摄政王载沣就显得有些稚嫩了。他有除掉老袁的念头,也有杀掉他的条件,但却处处被掣肘而无可奈何。
一来接替慈禧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缺乏前者的老谋深算和政治远见,遇事除了向朝中重臣求教外没有其他更高明手段,妥妥的一个“政治小白”;二来是清朝实权派和北洋系将领大多站在了反对极端方式处置袁世凯的一面。抛开那个上了老袁“贼船”的奕劻不谈,上任不久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即袁世凯若亡,北洋军极有可能发生兵变。

缺乏主见的隆裕太后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新帝登基杀戮旧臣影响当权者的仁政形象倒是次要的,真的酿成流血事件,背负王朝覆灭的责任,自己恐怕日后于九泉之下都难以心安理得,尽管3年后她在所难免的被迫接受了这一现实。
于是,原本在皇亲国戚鼓动之下,由载沣出面准备的那道遍布“包藏祸心”、“图谋不轨”等严厉措辞的“诛杀”谕旨,变成了“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的“革职”谕旨,听起来多少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在被“患足疾”的上谕指示下,开启了返回河南项城老家养病的旅程。
这是清王朝新晋最高掌权派载沣与袁世凯的首次正面激烈斗法,看似以袁世凯退出权力核心层而宣告暂时胜利,但载沣却没有丝毫轻松愉悦之感。究其原因,心腹大患未能彻底根除,老袁仍旧是一颗随时可能爆发的“定时炸弹”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治标不治本”的操作会毫无疑义的给世人留下一种摄政王有意“重满排汉”的印象,很有可能让未及施展政治举措的自己进退维谷。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遗憾,才有了两年后载沣与袁世凯的那次“终极斗法”,并最终让清王朝这个摇摇欲坠的将倾大厦彻底坍塌。
1911年10月12日,蔓延了三天的武昌起义炮火让载沣为首的掌权派们再次开启神经高度紧张模式。当天下午,载沣做出了抽调新军两个镇兵力由陆军大臣荫昌统率南下驰援武昌城的决定。
尽管荫昌自知北洋新军只认老袁而不认清政府,也预感到此行会处处受制于人而陷入尴尬境地,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这恐怕也是载沣所能提供的最优解了。
事后的经历果然如自己所料,南下军队的各级军官竞相消极怠工、违抗军令,行进速度极其缓慢。更让载沣焦躁不安的是,南下部队进入河南境内后便迟滞不前了。

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河南是老袁的家乡,也是他时下闲云野鹤的清净之地,尽管这背后是自己鹰视狼顾般的伺机而动。于此处裹足不前,显然是北洋系将领们要将老袁出山的压力重新丢到载沣面前,让他不得不尽快作出决断。
一边是北洋新军的实力抗衡,一边是满清皇族中已无力挽狂澜之人,这个时候的载沣算是真正尝到了进退维谷、步履维艰的滋味。尽管从内心深处来讲,他不愿向那个与自己夹杂恩怨情仇且象征擎天保驾的袁世凯低头,但又不得不逐渐认清这样一个现实:除了袁世凯,似乎没有人能为这个即将倒下的帝国大厦注入一丝扶助力量,虽然谁也无法确保这股力量能为帝制王朝延续多么持久的生命力。
正在此时,以贪腐著称的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袁世凯故交徐世昌等人一道向载沣进言启用袁世凯,英、美、德、法等国公使也基于各自的在华利益维护目的纷纷向这位摄政王施压。

连同隆裕太后在内,当权者们似乎感受到了重新启用袁世凯似乎并不只是消除外部革命党人的武装危机那般简单,一旦下定决心请他出山,就不可避免的要接受“引狼入室”带来的危机和隐患。可话虽如此,但放眼整个王朝的核心权力层官员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对此回天乏术。
束手无策的隆裕太后略显幼稚的请奕劻作为担保袁世凯“没有别的问题”的中间人,殊不知,为了钱可以不顾身后名节的这位老王爷,又岂会真正为这个看似事不关己的朝廷设身处地的做长远考虑?这也难怪在他去世后溥仪给出了“谬”、“丑”、“幽”、“厉”四个深恶痛绝的谥号,若不是奕劻后人找到载沣说情得到个中规中矩的“密”字,估计自己将被永远钉在家族和社会的双重耻辱柱上了。
形势紧张程度已不言而喻,但载沣依旧不甘示弱于袁世凯。在他的精心操作下,有关袁世凯的华而不实的任命呼之欲出了。这份上谕的内容很简单:让袁世凯和此前与其政见不合的岑春煊分别出任湖广总督和四川总督,袁世凯节制的军队均需与陆军大臣荫昌会商后再行调遣指挥。

载沣的目的显而易见,用汉人岑春煊来牵制汉人袁世凯,再由荫昌来监督掣肘袁世凯。
但他显然低估了老袁的在线智商。此刻的他关心的并不是这两个无伤大雅的牵制力量,而是自己下一步的走向。换句话说,大清朝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自己荷枪实弹的与革命党交锋,不仅会与对方形成不可调和的仇恨矛盾,也会在功成名就后免不了再受朝廷的杀伐威胁,而与革命党人就此握手言和也不是最佳选择,至少要考虑到自己的本钱和脸面问题。
思来想去,他提笔给清政府写了一封拐弯抹角的回应电文,表达自己旧病未愈的同时,冠冕堂皇的婉拒了“湖广总督”的任命。但在摛藻绘句之间,又无不传递出一种自己随时待命出山的决心暗示。

这是最让人抓耳挠腮的。好比时下的年轻人谈恋爱,男方对女方百般示好,但女方既不明确同意,又不直接拒绝,不置可否的态度让对方急不可耐却又一时不得其法。
估计此时的清政府上层大概也是这种感受。
恰在双方处于一种拉锯态势的情况下,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正式拥护黎元洪就任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都督,并在保护外国商民的行动中得到了各外国驻华领事的地位承认,这无疑对载沣这位摄政王爷形成了具有致命一击的舆论力量。
他不得不接受向袁世凯妥协让步的现实,即授予袁世凯全权指挥南下的所有部队的特权,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尽归其调遣。

老袁知道自己出山已成定局,借机提出条件抬高自己身价的机会也来了。除了征兵、拨款、点将等与战事密切相关但又有些狮子大开口的条件外,他着重开列了六项条件:
“明年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次兵变诸人;解除党禁;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给予充足之军费。”
如果放在平常,很难想象这些“苛刻”条件会是一个组织内部人员煞费苦心后争取到的成果,除了坐实趁火打劫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更是一种权力欲望极度膨胀的真实表现。
只是,无论忧心忡忡的隆裕太后,还是余憾未消的摄政王载沣,都已不再具备内外交困形势下制衡袁世凯的行为能力了。

万般无奈的载沣在完成对袁世凯所提战事要求的满足后,老袁向嫡系部队将领冯国璋下达了行动指示:“慢慢走,等等看”。
为什么要“慢”,又为什么要“等”,此时已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只不过,象征各种力量错纵交织的民国历史序幕,一旦被人拉开,将再也无法关闭了。
“终极斗法”失败的载沣自然清楚来年袁世凯组阁后等待他的将是一种怎样的结局,以及对于这个自己赖以彰显至高无上身份地位的帝国王朝即将面对的是怎样一个走向,只是,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正如远在大洋彼岸那个一力促成帝制终结的孙中山在多年后面对钱塘江大潮时心潮澎湃写下的千古绝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载沣,都无法逆转这奔涌而来且坚不可摧的民主革命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