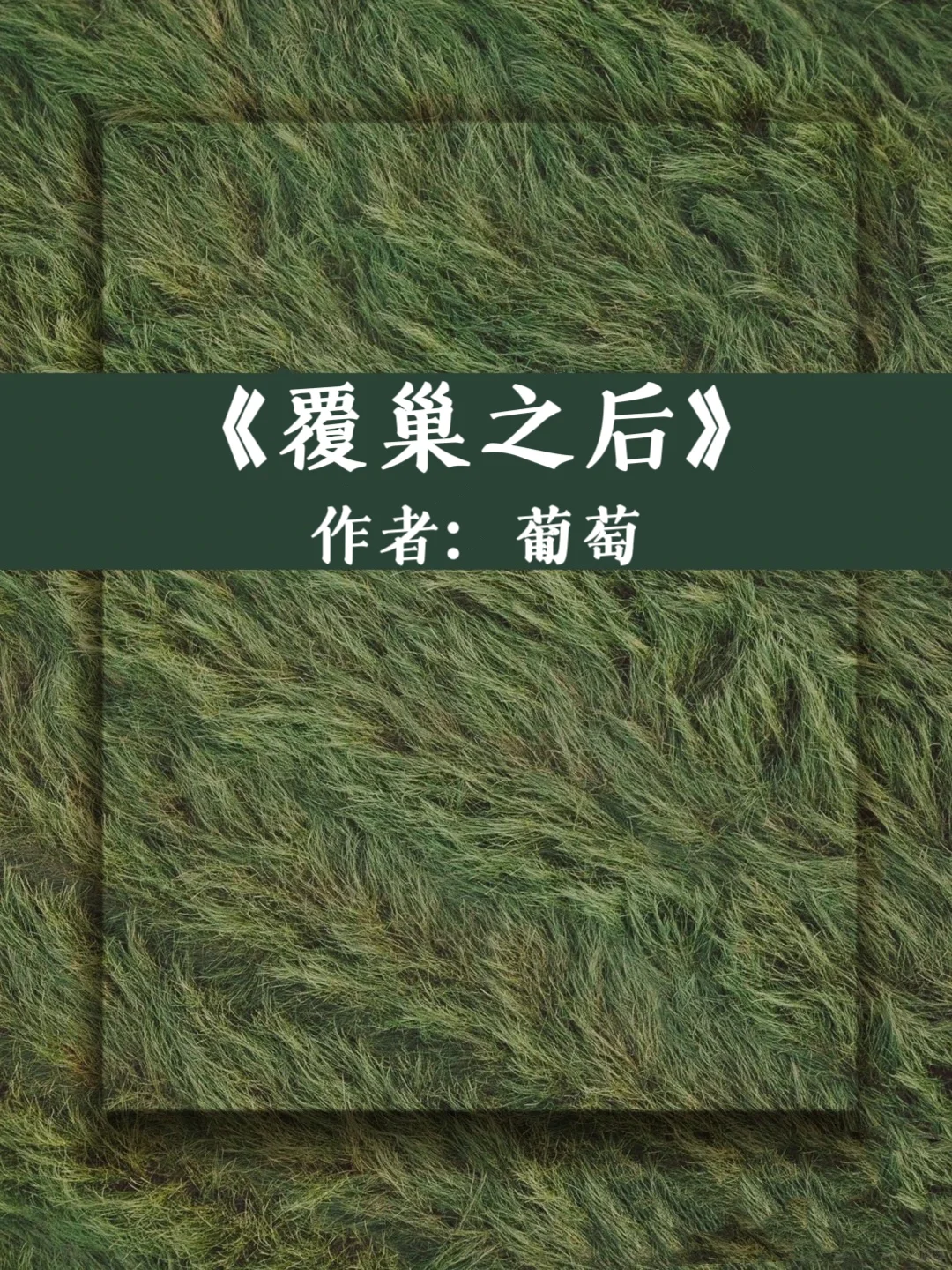妓院里,所有都讥讽我卖艺不卖身,当了婊子还立牌坊。
直到有天,我爬上了当朝宰相的床,以青涩之身却极尽浪荡之姿。
宰相尝遍了各种滋味,独独对我很感兴趣,夜夜召唤。
妓院里的人又都开始唾骂我。
没人知道,我一次又一次吻上宰相的唇,沾染了什么。
直到后来手刃仇人后,我也被换上了大红嫁衣下了葬
两块牌位,行完了三年前我和夫君未行完的婚礼。
这一刻,我终于成为了夫君的妻。
1
我取了个桶子去到后院厨房,打算给自己打点热水洗脸。
厨房里的妈子一把抢过我的水勺。
“哎哟安娘,这热水可是给前面那些接客的姑娘们用的,你金枝玉叶,也只能麻烦先将就用冷水啦。”
旁边浆洗衣服的婶娘立马接过话茬。
“啥金枝玉叶呀,还真当那个赶考的举子会回来呢,也不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谁家贵人看得上妓院里出来的。”
烧火的吴婶看不下去,抢过水勺给我往桶里舀了好几勺水。
“就你们嘴巴多,安娘卖的是琴技,又不卖身。安娘的琴技十里八乡都出名,金玉娘都舍不得安娘这双手受累一点,你们还给她用冷水,等下金玉娘知道了,小心赶你们出去。”
我接过水桶,轻声道了声谢。
妓院里面都是露水情缘,最不值钱的就是真情。
像我这样忠守承诺的,她们看不上。
我叫安娘。
三年前,抱着一把古琴撬开了金玉楼的大门。
金玉娘开门的时候很是诧异。
许是没想到,如今这世道,还有女人主动敲妓院门的。
金玉娘和我正面相对而谈的第一天,眉眼之间满是打量。
“安娘,你有出世之质,琴技绝然,没必要来我金玉楼。”
我将面前的茶斟了个八分满,递给了金玉娘。
“凭本事吃饭,在哪都一样,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金玉娘看了我半晌,最后接过茶杯一饮而尽。
此后,我就成了金玉楼的琴师。
金玉娘在楼里上下都交代,我只做琴师,前门房里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准找我。
我虽不解,却也没有过问。
人生如潮水,本就无迹可寻。
无问,便无答。
无答,便无果。
这日,我刚弹完琴,金玉娘递给我一个牌子,喜不自胜。
“安娘,你算是遇着贵人了!柳相爷递牌子让你今晚上去他府里弹琴呢!”
当朝宰相柳如释?
金玉楼平常不让女子出楼,但是碰着像柳如释这样的大官,自是不能有二话。
我到相公府的时候,柳如释已经坐在宴席上和来宾畅饮。
见我来了,大手一挥。
“其他琴师来我府上,都是蒙面示人,你为何不蒙面?”
我抱着琴低头行礼。
“奴家卖的是琴技,靠手艺吃饭,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柳如释听完哈哈大笑,让下人把我的位置搬到他旁边。
当晚结束的时候,柳如释捏住我的下巴,四目相对。
“从今天起,你就在我府上弹琴。”
我垂眸别开视线。
“相爷,金玉楼有规矩,不让奴家在外过夜—— ”
话还没有说完,柳如释一把掐住我的脖子,阴鹫般盯着我。
“我是在通知你,不是和你商量。”
脖子猛然传来的窒息感和疼痛感,让我顿时眼眶里面冒出了眼泪。
说完,柳如释松开手,轻轻用手在我脸上擦去眼泪。
“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我一听,立刻俯身跪下。
“奴家大众面貌,想是他人和我长得相似。”
柳如释倒也没有多问,看了我一眼便拂袖离开。
也许见过,也许没见过。
我回金玉楼收拾东西的时候,后院的妈子们又是一顿阴阳怪气。
“哟,说好的卖艺不卖身,这不还是被包府里了吗?谁知道每日在里面到底是弹琴还是干些别的勾当。”
吴妈狠狠淬了她们一口。
“编排人都编排到贵人头上了,被那位相爷听到,小心割了你们舌头。”
那群妈子顿时被吓住,面面相觑之后作鸟兽散。
我虽不在意,但有人替我出声,总归是温暖的。
我掰了一角银锭给吴妈,吴妈大惊失色。
“安娘,使不得使不得。”
我把银锭硬塞到她手里。
“吴妈,听龟公说你儿子腿摔断了,看病要花钱,收着吧,我平时有客人的赏赐,不用客气。”
吴妈背过身擦了擦眼泪,轻声喊了声姑娘。
我拍了拍吴妈的背,拿着剩下的银锭从侧门出了金玉楼,在街巷里穿了好几阵,终于看到一处简陋的棚房。
还未走近,就听见里面传来的破碎的咳嗽声。
“婶,最近好点没,我带了些楼里的卤猪脚,听说现在楼里的这个厨子是玉轩楼过来的,厨艺可不得了,你和叔快尝尝。”
潘母掩着帕子咳了好几声才顺过气,用干瘪的手摸了摸我的头。
“安娘,都说了你以后不用再来,展白已经去了,何苦还要把你的人生再搭进来。”
“是呀安娘,你和展白并未成婚,你正值年华,寻个好人家过日子,不用管我们两口子。”
我从潘父手里接过药碗,吹了吹,送到潘母嘴边。
“我自愿的。”

人生有很多不自愿,也有很多可以自愿。
我自愿赡养潘父潘母,也自愿困在和潘展白戛然而止的缘分里。
2
那年潘展白碰到我的时候,我正随着乞讨的流民刚来到此地。
我实在饿得不行了,从包子摊位上抢了一个包子使劲往嘴里塞,摊位老板是个壮实的成年大汉,见我偷他包子,拳头狠狠朝我砸来。
我不躲也不避,使劲往嘴里塞包子,包子吃完了都不知道是什么馅。
潘展白喝住摊位老板的时候,我已经被打得鼻子流血眼冒金星,但是我抬头的时候还是看清了他眼下的红色泪痣。
他把我带回家,给我养伤。
他说以前的名字不要了,以后就叫安娘,安稳周全。
潘家父母是对心善的老实人,把我当女儿养,吃的用的都先紧着我。
潘展白每天吃完中饭就去金玉楼弹琴,夜深回来的时候都带着吃食,有时是个酥饼,有时是个鸡腿。
我每每要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才肯睡觉,他不回来我就一直坐在哪里等。
潘展白笑我。
“小馋猫,你不用等我这些吃食也是你的,早上你醒来就到你嘴边了。”
潘展白不懂,我才不是因为吃食才等他的。
闲暇时,潘展乐就唤我坐在琴前,他用手臂环住我,按着我的手,一个音一个音的教我弹琴。
我每每都听不见琴音,只听得见胸膛里如雷的心跳声。
中秋那晚,分不清是夜色醉人还是酒醉人,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亲上了他。
那晚的月色真亮,亮得潘展乐眼里的欣喜激动分毫毕现。
我想退缩的时候,他一把拥住我用力地吻了回去。
他说:“安娘,我们成亲吧。”
潘展乐给我定了城里最好的嫁衣,打了最繁琐的首饰。
我们定好要生三个胖娃娃。
但是我们没有等到这个机会,甚至连嫁衣都没有机会穿上。
成亲前一晚,一伙官兵冲进院子,说有个逃兵逃到了这个巷子。
为首的官人衣着华丽,对着潘展乐轻轻一指。
“逃兵和他长得相似,就拿他回去交差吧。”
我们连个不字都没说出来,潘展白就已经捂着喉咙倒在了地上,血流不止,眼睛瞪得极大。
他们就这样把我无辜的夫君绑在马后,拖走了,丝毫没有管我们的撕心裂肺。
只因他们是官,我们是民。
三天后,尸体在乱葬岗发现,眼睛依旧瞪得极大,我亲手给他合上。
我紧紧抱着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尸体,流尽了眼泪。
那个从流民当中把我捡起,教我弹琴识谱,许诺成家生娃的爱人,死在了无人问津的夜晚。
我去到相公府的当晚,柳如释把我喊进了房间。
他解我衣带的时候我有些发抖。
他在我耳边轻笑一声。
“在金玉楼这种地方呆了这么久,怎么还这么不熟练?”
我打了个冷颤,哑声回话。
“相爷,奴家在楼内只弹琴,不卖身。”
话音刚落,脸上顿时火辣辣地疼。
柳如释这一巴掌把我扇倒在地,我脑袋都懵了好几秒。
“不给银子,那就不是卖了。”
柳如释一把把我从地上拉起,盯着我,面色冰冷。
“把你在金玉楼学的本事,在床上都使出来。”
我瑟缩着身子,生疏地对着柳如释嘴巴啄了一口。
柳如释很满意,把我衣服尽数扯下,我冷得打了好几个颤。
柳如释将桌上茶具一扫而尽之后,把我放在上面,盯着我的身子来回看了好几遍,眼睛里面闪着兴奋的光芒。
柳如释进来的时候我吃痛惊呼出声,闻声他更加兴奋了,掐着我的脖子。
“没想到金玉楼出来的,还能有雏。”
我没有力气回答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凑到他嘴边,亲了一下又一下。
这天晚上的痛苦程度,不亚于潘展白去世的那天晚上。
只不过一个身体痛,一个心痛。
第二天大早,相公府的丫鬟端着一碗浓黑的药过来。
我撑起浑身散架,酸痛不止的身体,问了一句这是什么。
丫鬟没好气地把碗重重放桌上一放。
“避子汤。我们相爷是人中龙凤,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给他生孩子的。”
我服下汤药,就这样,被柳如释放在了偏院。
柳如释权倾朝野,又深得圣恩,每日来他府上的人络绎不绝,因此府内每日宴席不断,我在席上弹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每日我就在旁边看着柳如释在众人的谄媚恭维声中觥筹交错,听着他们议论朝廷形势,每件事情伶出来都够我杀头一百次。
柳如释尝遍了各种滋味,反而对我这具未经人事的身体很感兴趣,夜夜弹完琴后唤我到他房内。
3
我什么都不会,只能一次又一次,吻上他,和他唇舌纠缠。
每次一边痛苦承受着他在我身上毫不怜香惜玉的冲撞,一边在心里暗暗打气。
安娘,再坚持一会,会结束的,一切都会结束的……
再难的因果,都会有结束的那天。
这天我刚调好琴弦坐好,柳如释便被众人簇拥着来到席中。
还未开始弹,却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故人。
对方显然也大吃一惊,看着我满脸惊讶。
我悄悄颔首,以示招呼。
对方楞了好几秒,匆忙向我点了个头。
我低头轻笑。
好久不见,萧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