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田单干后那些老弱妇孺怎么办!”田家英1961年初的时候坚决不赞成包产到户,他含着眼泪向毛主席写信说,工作是我们做坏的,现在又实行包产到户,把寡妇们丢开不管,良心上过不去。然而,1962年上半年,他奉毛主席之命,率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到韶山做调查,听到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触动很深,他对工作队的人说:“包产到户是农民的心愿呀!”流露出同情包产到户的情绪。 回到北京,他就向刘少奇、陈云、邓公汇报,并向毛主席进言。另外两个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的高层领导人是邓子恢和陈云。陈云估计,农业的恢复需要8年时间,用分田到户的办法可缩短到4年。等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引回集体经济。7月17日,邓子恢当面向毛主席谈了相同的意见,邓子恢还在中央党校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等单位做报告,主张允许部分农民包产到户。 1956年5月,燎原社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悄然拉开了中国农村历史上第一次包产到户试验的序幕。燎原社,这片土地上燃起了一场名为“包产到户”的燎原之火。对于这一前所未有的变革,社员们的反应如同初春的田野,议论声此起彼伏。面对种种疑虑,工作组耐心引领大家展开讨论,逐步澄清认识: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前提下,对农业生产管理方式的一次创新尝试。于是,一场以生产队为基本单元,社员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之风,悄然在燎原社吹开。 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其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他们根据种植品种的全周期管理需求,从播种、栽培、耕耘、积肥、施肥到日常管理,共划分出约400多项具体工种。随后,结合季节变化和劳动强度,为每项工种设定了日工作量及质量标准。劳力被科学划分为9个等级,从一等工的15分逐次递减至九等工的7分。为了更精准地衡量劳动成果,他们制定了分季按件对照表,将280项大小农活按照生产季节、内容、质量、数量定额及应得工分一一对应,精确计算到每一块田地。 各生产队再根据土地的远近、肥沃程度、水利条件及耕作难易,合理确定工分定额,确保责任到人、到户。这一系列举措,被精炼地概括为“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定额到丘,责任到户”。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试验巧妙地将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相融合,打破了“天天集体、事事集体”的僵化模式,让社员或家庭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劳动效率显著提升。至1956年9月,永嘉县已有200多个高级社跟进实施包产到户,占比高达全县总社数的24%,改革之势蔚然成风。 在潘桥农庄,对“分级定额、按件计酬”责任制的探索并未止步。当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印发《改进生产管理》小册子,提出“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的构想时,虽缺乏具体操作指南,却如同一股清流,激发了人们的思考。面对分级定额后生产秩序改善但劳动质量难以保障的困境,他们决定以一个生产队为试点,尝试实施“三包”逐件到田、分段专责管理的模式,即生产统一安排,劳动分段规划,简称“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 这一创新不仅强化了劳动管理,还通过责任落实,有效解决了小段包工、按件计酬制度下劳动质量监督的盲点,实现了个人劳动质量与报酬的直接挂钩,管理者的管理质量也与其报酬紧密相连。原本由生产队长独揽的管理责任,被细化分解至各专管地段负责人,形成了更加精细化的管理体系。1956年3月31日,永嘉县委正式发文推广“四包”责任制及按件计酬,这已是第三次重要调整,其核心已悄然转向以地段和劳动的实际产出为生产责任制的基石。 戴洁天在回顾这段历程时,感慨万千:集体化进程中的种种挑战,根源并非农民觉悟不高,而在于责任落实的缺失。责任需具体,事事有人管,方能成就大业。劳动质量的评判往往笼统,而产量则是实打实的硬指标,直接反映劳动成效。为此,他们创新经营方式,确保每一寸土地、每一份产量都有人负责,通过保留生产队框架,将生产与农户紧密相连,让产量与劳动质量成为每块土地上的共同语言,激发了每个人的责任感。 在这场时代洪流中,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亦未能免俗。1981年春,随着全国大包干政策的推行,南街人迅速响应,每家每户都领到了那本沉甸甸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从此,“责任田”这一全新概念深入人心,它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预示着连最朴实的农民也开始学会用理性的眼光审视自身行为,用“好不好”、“适合不适合”来衡量自己的选择。这股思想解放的浪潮,为南街人后来土地的分与合埋下了伏笔。 岁月如梭,转眼间,社会已步入年轻一代对合作社、生产队概念陌生的时代。人们在生活的奔波中逐渐钝化了对周遭变化的敏感,但当“南街人重启集体化生产队”的消息传来时,还是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尤其是在中央红头文件明确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南街村的集体化举措更显得格格不入,充满了政治风险。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南街村独树一帜,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其勇气与智慧,值得我们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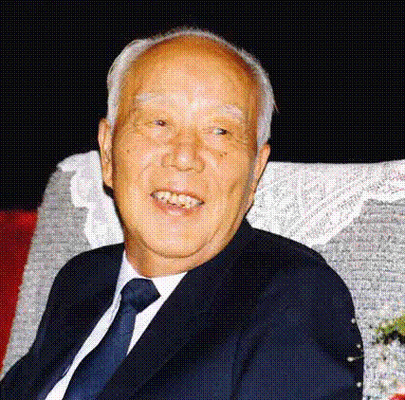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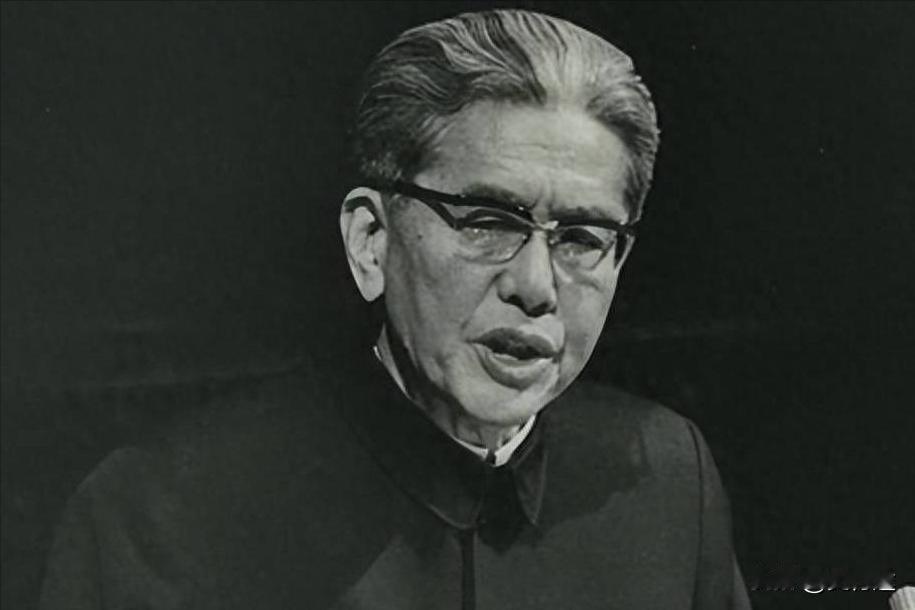


写的颠三倒四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