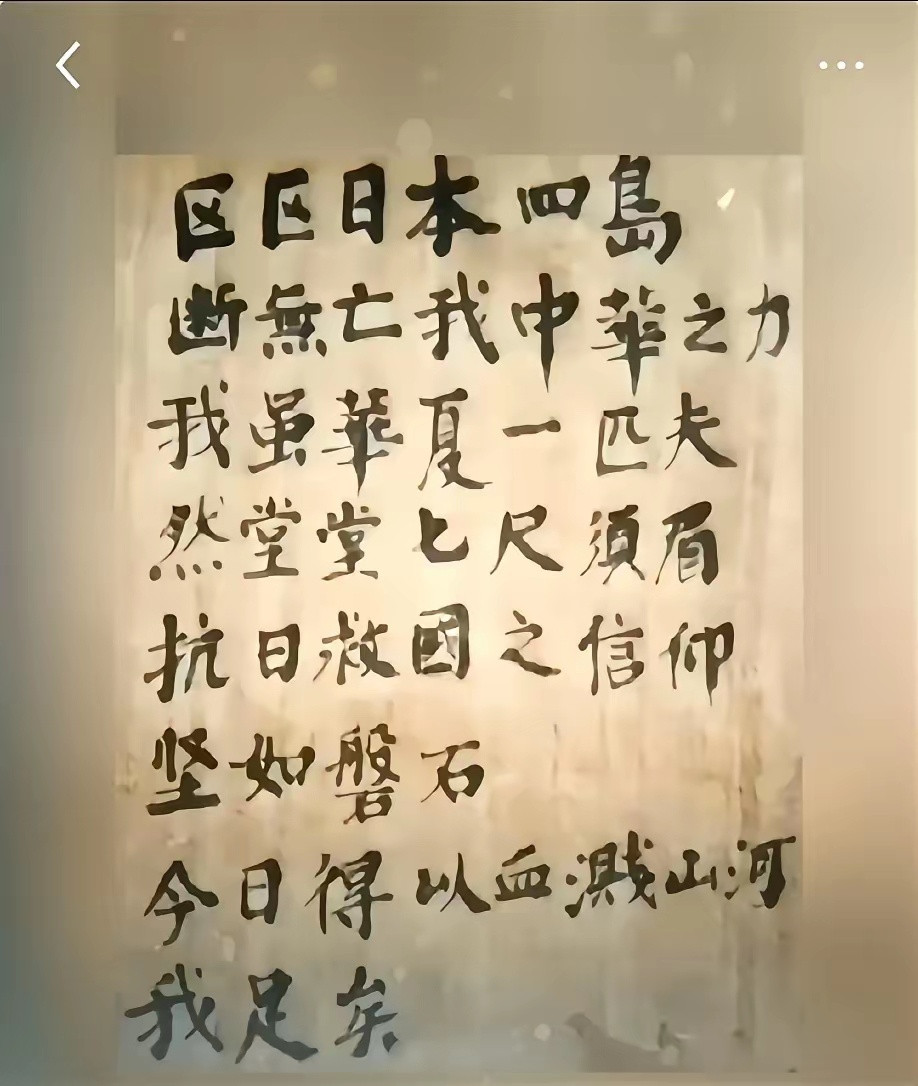1949年10月,蒋介石对陈诚说:“汤恩伯辜负我对他的器重,让他从金门回来。”陈诚询问汤恩伯到台湾后授予何职,蒋介石只是摇头,这时的汤恩伯在蒋介石的眼中,已成为多余的人。 蒋介石对汤恩伯由倚重转为冷落,又由冷落转为反感的态度,决定了汤恩伯在台湾的可悲处境。 赋闲于台北市锦州路家中的汤恩伯,十分苦闷。1951年11月,汤恩伯移居到台北郊外。他邀约在台旧部组织小型读书会,有时也举行座谈会,探研社会、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后来,汤恩伯感到组织旧部学习的方式不是很合宜,便放下一切。深居简出,很少同过去的同事、友人往来,而是潜心于文学艺术。 汤恩伯除了喜欢诗,还爱好戏剧,尤其对梅兰芳的京剧兴趣甚浓。他将自己三个女儿取名为汤国梅、汤国兰、汤国芳。 昔日风风光光的汤恩伯,移居乡下以来,逐渐到了需要节衣缩食的境况,陷入为生计而精打细算的苦闷之中。他在1951年3月2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至台后闲居一年,目前均感生活困难。我此次迁乡居住,本拟节省开支,不料修理房舍又超越预算,反增许多开支。不知住定后,能节省否。 到了年末,汤恩伯家中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只得辞退了安保人员。不过,据友人回忆,每当朋友光顾,汤恩伯一定留下来吃饭,并让厨房加菜,“打肿脸充胖子”。 有一次,旧友徐复观去三峡镇看汤恩伯,汤恩伯正在当地的一家小诊所里割治盲肠炎。徐复观问汤恩伯为何不到中心医院去做手术,汤恩伯无奈地说:“没有关系,这里便宜。” 郁郁寡欢的汤恩伯,胃疾复发且日趋严重,为了方便就医,他不得不迁居台北市。但是,治了相当长的时间,病情却不断加剧。请中心医院的外科权威医师张先林检诊后,发现除胃部溃疡外,还有十二指肠肿瘤。张医师认为台湾技术有限,应当及早出去进行手术治疗,否则,在半年内恐有性命之虞。 汤恩伯一听此言,一连四天四夜难以安然入眠。身在美国的夫人王竟白得知病讯,十分着急,电邀汤恩伯赶紧赴美就医,说美国的波士顿对此病手术是相当成熟的的。可是,汤恩伯在台湾的小老婆钱婉华却不赞同,要汤恩伯去日本医治。 汤恩伯反复考虑后,认为去美国治病,花销太大,而到日本医治,至多七八千元,还是可以应付的,于是他倾向于去日本。 其实,汤恩伯去年就想过要到日本治疗,曾向蒋介石提出申请。蒋介石看到汤恩伯的申请报告后,签了“就地医治”四个字,并生气地说:“有大过的人,还想去日本治病?” 后来,雷震动员汤恩伯到台北中心医院住院治疗,汤恩伯说:“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住院也无益。要治好,只有到日本。我申请到日本治,总统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着死!” 1954年5月,汤恩伯再次提出去日本治病的申请,蒋介石同意了。5月27日,汤恩伯飞赴日本,进入东京庆应大学附属医院,由岛田信胜博士担任他的主治医师。 第一次手术后,情况良好。谷正纲、胡健中两人路过东京时,曾到医院探望过汤恩伯,汤恩伯一见两人,便高兴地说:“我十二指肠上的瘤已经割去了,并因胃溃疡,胃也割了三分之二。” 然而,几天后,汤恩伯病情突然严重,主治医师曾为之连续实施了第二、第三次手术。体质渐弱的汤恩伯在6月29日第三次手术时,死在了手术台上。 汤恩伯死去的消息传到台北后,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被报复的结果。据陪护汤恩伯的亲属说,按日本医院的制度,护士每次到病房为病人注射后,都要把盛针药的空瓶放在桌子上,让病人家属知道注射的是什么药。但最后一次却一反常例,不见有针药瓶留在桌子上。注射完不久,汤恩伯便暴死在手术台上 在汤恩伯死后,蒋介石派陈良去日本视殓,陈良回台后报告称:汤恩伯的确是死于日本医师的疏忽,但是不是死于恶意,而恰恰是死于善意之举。汤恩伯到庆应医院后,许多日本友人就去关照医师,说要加倍细心治疗。因此,医师岛田信胜格外用心诊治,其他医护人员对之也特别客气,遇事予以通融,不完全依照医院规则。 正因为如此,铸成了一些错误:照理,割胃要放橡皮管,以便淤血流出,但医师怕汤恩伯有痛苦,就略而不用;动这么大的手术后,二个月内不应洗澡,但汤恩伯在首次手术半个月后,医师居然同意他洗澡的要求;动大手术后要绝对安静休养,一周内绝不准许接见客人,家属也不例外,医院却例外准许汤恩伯家属在房间照料,小孩进去也不禁止;汤恩伯手术后未能进食,口中乏味,很想吃些酱菜,医师也未阻拦。诸多善意相待,其实都不利于治疗和康复。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所谓的“善意”其实就是故意为之。 汤恩伯死后,胡宗南约友人前来,拿出汤恩伯在日本医治期间写给他的几封信,递给他们看。其中一封,已经潦草得不能成字了,这其实是汤恩伯的绝笔。信中大意是:汤恩伯无法支付医药费,恳请胡宗南在蒋介石面前为他想点办法。 胡宗南把要求补助药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手中,被批准拨给3000美元,可是,钱拨下来的时候,汤恩伯已死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