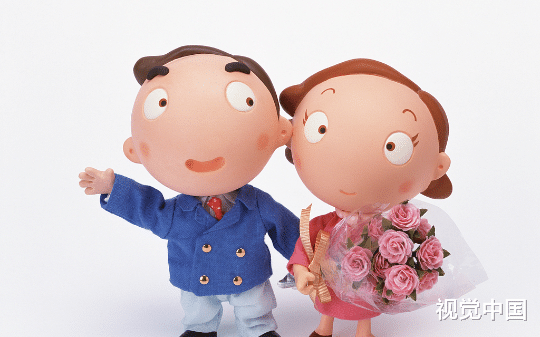我是宰相府的假千金,
在我即将嫁给太子的前夜,真千金归来,
她毫不费力地就抢走了我父母嫡兄的所有关爱,
一句枕边风,便让太子亲自动手取我心头血,再把我丢进牢笼。
我心如死灰。
后来,我成了青楼头牌,初夜竞拍会上,无数男子为我一掷千金,
我对上台下太子的视线,轻笑一声,
我的嫡姐,你可知自己的夫君今晚在哪里?
……
1
「那贱婢肥硕如牛,给太子当洗脚婢都不配,怎能嫁与他?」
我站在门外,低头看了看连大氅也裹不住的肚皮,一阵难堪。
「月儿啊,她只是为你十八岁之前挡劫的物件,何必伤心掉泪。」
「哐嘡」一声,我手中的灯笼滑落。
「谁?」
父亲推开门,立即变了脸色。
「听到了也罢,享了十六年不该享的福,是你该报答相府的时候了!」
「明日,你以女婢的身份,随月儿一同去王府吧!」
娘亲捻着佛珠走了出来,别过脸,不肯看我一眼。
我慌忙扑住母亲的手,音色颤颤:
「娘亲,我是您的女儿阿星啊。」
又钳住父亲的衣袖:
「我是阿星呀,爹爹!」
他们双双甩开我的手,因着身子沉笨,脚下没换过来,一屁股坐到了冰冷的石阶上。
身后传来一阵嗤笑:
「我叫楼曦月,是相府唯一的嫡女。你?不过是没人要的贱种。」
楼曦月。楼星望。
我明白了。
星望曦月。
我是为相府千金挡劫的星。
不是娘亲爹爹手里捧着的星。
我的身子终于沉了下去,如一滩恶心的肥肉囊在地上。
这才堪堪想起,十六年来。
父亲不曾教我执笔写字。
娘亲不曾训我顽劣耍滑。
长在相府十六年,却无父无母。
还有哥哥,他素来是疼我的。
我艰难爬起,笨拙地往院外跑,就在要够到门栓的那一刻,身前挡住了一人。
是哥哥。
楼颂翊。
我一时没刹住,重重扑到了他的脚下:
「哥哥,带我去找钰哥哥,求求你!」
他一脚踹开我,冷眼笑道:
「你还真把自己当相府千金了?妄想嫁给太子!」
原来,他也知道的。
楼曦月拽起我的头发。
「啪!」
狠烈的巴掌甩上脸颊,热辣辣的,嘴里蔓延出腥气。
「凭你也配跟我抢?」
凉光掠过眼前,直到被人摄住下颌,我才看清,是一把利刃。
「哥哥,按住她!我要割了她的舌头,看她还怎么跟太子告状!」
锐利的刀光闪过,刹那间,我口中血如泉涌,落在地面,绽出凄艳的红花。
再睁眼已是一片黑暗。
我想呼救,却发不出半点声,只能用力拍打着木板。
但微弱的声响,很快淹没在了欢鸣之中。
「你们俩,透个缝儿,别让她憋死了!」
一线亮光射入,我双手撑着就要往出挤,却被两个壮汉扭住了胳膊。
春玉啐了我一口:
「呸!都这般了还不老实,把她双手绑上!」
她全然没了往日的恭敬唯诺。
转而朝一身明华霞帔的楼曦月笑意盈盈。
「那丑八怪将嫁衣做得如此肥硕,故意要我在太子面前出丑。」
「小姐,您且将就些,成了太子妃,什么华服没有!」
从前她喊小姐的人是我。
我真傻,拿婢女当妹妹疼,想着自己要成婚,便也给她备了份嫁妆。
如今,楼曦月穿着我亲手绣了三个月的婚服,嫁给了我少时心心期盼的郎君。
我与一众嫁妆被抬到了太子府。
顺着那条窄缝,我看见了齐钰。
2
他仍一如往昔,身长玉立,爽朗清举,与天上的谪仙一般无二。
八岁那年,我因贪看蛐蛐,错过了晚食,饿得蹲在地上哭。
齐钰递来一块清莲酥,笑得如三月春风:
「快吃吧,要吃得圆润些才喜庆。」
自此以后,我没错过一顿晚食。每每吃饱了,还要多塞两个鸡腿。
二八年华,却将自己撑得圆鼓鼓,像个球。
暮色将暗,我被抬了进了太子寝殿。
还是透过那道缝,看着齐钰挑开楼曦月的盖头。
她娇羞颔首,轻声呢喃:
「钰哥哥。」
齐钰抚上她的脸,眼里尽是缱眷:
「太子妃今夜实在娇俏动人。」
我蜷缩在箱底无声地哭泣,像一只被主人丢弃的奴狸,孤独且绝望。
没想到,一别八年,他早已认不出我了。
此后的日子,我被锁在太子府的暗房。
白日里春玉给我送饭,夜里,听太子妃蘼音承欢。
一开始,春玉送来的还是白粥,后来变成馊饭,最后只剩蜈蚣鼠蚁。
如此不知过了多久,我宽松的衣带下只剩了一把骨头。
这日稀奇,春玉带了满满一食盒饭菜。
有米,有青菜,还有一整只烤鸡。
我颤着手将饭往嘴里塞,又贪婪地咬住一块鸡腿,却没力气嚼。
春玉用帕子捂着口鼻:
「没见过世面的东西!再过两个月就是太子妃十八岁生辰了,你可吃饱些,好有力气为太子妃挡灾。」
原来春玉也知道,我不过是替楼曦月避祸的祥物罢了。
「你不过一个没人要的野种,凭什么能在相府当千金?凭什么我得伺候你?」
她又嘲食盒里吐了口:
「你只配吃我唾过的东西!」
在饭菜彻底凉透前,我吃了个精光。
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见到钰哥哥,鼠蚁我都吃,何况区区口水。
吃了一个多月的饭菜,我凹陷的脸颊也慢慢膨胀起来,只是常年不见日光,皮肤如死人一样白。
这日,将将吃完最后一粒米。侍卫们鱼贯而入,整齐地分列在四周。
最后出现的是齐钰。
干涸的眼眶瞬间蒙上一层雾气,泪如泄洪而下。
我仓忙将嘴角的饭粒塞进齿缝,拢去遭乱的长发,又觉满手污垢,在破烂的衣衫上蹭了蹭。
这才咧开嘴,尽力发出「钰」的声。
只是囫囵在嗓间,听不真切。
他缓步走近我。
我满心欢喜,我的钰哥哥,终于想起我了,来救我了。
正当我要伸手扑向他的时候。
一柄锋利的刀,插中了我的胸口。
齐钰怒目低吼:
「我要你的心头血,救我的太子妃。」
我肮脏的手握上寒冷的刀刃,低头看艳红的血汩汩而下。
干哑着嗓子挤出模糊不清的三个字:
「为……什……么?」
齐钰却再将刀尖深入一分,我的血流了满满两大碗,他才满意地离开。
原是楼曦月生了一场大病,需要我的心头血作药引。
接连三日,每每正午时分,他都来剖心取血。
小暑时节正热,我却浑身发冷,如三九天里赤脚踩在冻裂的冰面上。
我蜷缩在地上,双手捂着脚心,浑浑噩噩地做着梦。
梦里是齐钰的束发礼,皇后看着翩翩玉立的他,打趣问道:
「太子喜欢怎样的女子?」
3
「儿臣中意的,是如母后一般,学识广博,八雅皆通的女子。」
我偷偷躲在红漆柱后,将这八个字牢牢记在了心里。
从那以后,女学未曾逃过一节,总是抢在最前头。
晚食过后还要缠着嬷嬷教我插花煮茶。
每逢休沐,偷偷跑去锦灵馆学音艺舞曲,不到日暮不肯回府。
转瞬,又到了齐钰弱冠之年,我远远一曲凤萧相贺,还未见着面,他便求皇帝赐婚宰相嫡女。
一瓢冷水泼下,砸碎了我的美梦。
又是熟悉的刀,插入已经麻木的胸口。
我如一具任人摆弄的木偶,仰着身子。
今日的齐钰皱着眉,似乎不满意。
「来人!」
一声令下,一盆湿黏黏的蚂蟥散落在我的胸口。
不过一会,它们长到拇指般粗大,被捡到了玉碗里。
就在齐钰转身离开时,我匍匐在地上,扣住了他的足踝。
喉头如塞满了石砾,发出涩哑的呜呜声。
他垂眼看我,还是如此的隽秀神朗。
「认命吧,我的太子妃是相府嫡女。」
我缓缓垂下手,合上眼帘,流下一滴血泪。
太子府的暗房,他怎会不知晓这里关着一个阴戾的女鬼。
他中意的不过是一个能配得上太子妃之位的女子。
宰相嫡女,身软声娇,自是匹配无双。
我以为会死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没想却被当做一把烂骨,扔到了城外的枯坟地。
我从腐烂的死人堆里艰难爬了出来。
胸口还渗着血,我扒掉刚凉的尸体外衣,缠在伤口处。
踉跄了几步,又折返回去,翻那人身上还有没有值钱的物件。
幸好,找到了镶在嘴里的金牙。
我摸上一块石头,砸下金牙,捂在手心里,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用金牙换了些银两,又用银两换了身衣裳,买了草药包扎伤口。
铜盆里倒映出我清瘦的脸,竟添了一丝妩媚,只是与眼底的凄凉阴森很不相称。
银两正好用光。
我掠进城中人气最旺的水粉铺子,穿梭在粉领绸缎间,让身上也沾了些香气。
趁人不备,捡了盒口脂揣在袖口里。
再镇定自若地离开。
没成想有朝一日,我会行偷盗之事,那刻在骨子里的圣贤礼浑都忘了。
我将口脂涂在唇瓣上,走进了银雪楼。
银雪楼是京中最盛名的烟花之地。
秦妈妈上下打量着我:
「脸蛋还不错,只是这身段,似乎瘦弱了些。」
我目光淡淡,取笔在纸上写下:
「银雪楼素来不缺漂亮姑娘,缺的是处子之身。」
秦妈妈眼眸亮了亮,身子不禁往前一倾。
我继续写道:
「琴舞书画,我还要强上头牌姑娘几分。」
秦妈妈捂嘴轻笑:
「姑娘口气倒不小,银雪楼伺候的都是京中的达官贵人,就连府上养了乐艺的裘大人,也是我们这里的常客。」
目光环绕一圈,我坐在古琴前,十指轻巧舞弄。一曲毕,引得秦妈妈连连拍手叫好。
「姑娘要多少银两?」
我顿了顿,抬笔写下:
「我分文不收,只有一个条件。」
秦妈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条件?」
4
我来银雪楼不是为了抢头牌,只是为了见达奚,学蛊术。
我要复仇。
秦妈妈实在舍不下这才艺精通的美人儿,勉强答应了下来。
她救过达奚的命,达奚为了报答秦妈妈,偶尔施蛊为银雪楼的姑娘招揽贵客。
才使银雪楼在京城这么多烟花柳巷中如此出挑。
这是我在锦灵馆学琴时,听女师傅说的。
见到达奚时,已是第二日。
她打开匣子,里面是一只小小的白色蠕虫。
她示意我张嘴,将白色蠕虫放了进去。
蠕虫钻到我舌根处,似用钳子夹着最细嫩的肉,又痒又痛,挠心不已。
可我还是强忍着,只是在手心印出了血色月牙。
如此三日又三日,我已能吐出略微清晰的词句。
直到我喊出秦妈妈三个字,她才问我,叫什么名字。
恰好路过的小厮端着秤盘,不小心掉下一枚香牌。
我将它捡了起来,道:
「就叫轻烟吧。」
秦妈妈对这个名字颇不满意,觉得不吉利,是死人用过的。
可我却觉得甚好,我何曾不是死过一次的人呢?
秦妈妈每日都逼着我练嗓音身段。
她说我讲话总是太过寡淡,身子也太过刚直。
要做头牌,一定要声娇体媚。
我学得很用心,但更用心的是跟达奚学蛊术。
我问她,如何才能让人失去记忆,失去意志,甚至失去生命。
她看我的眼神有些慈悲,说,除非以身养蛊。可如此,养蛊之人也是要没命的。
我不在意地跟她说,我啊,不怕。
达奚让我去找蛊虫,京中不比南疆的虫子好,但也勉强能用。
于是,白日里跟着秦妈妈扭腰媚笑,夜里就冷着脸去山里找蛊虫。
蛊虫没找到,倒捡了个瞎子。
那人没在草丛里,只漏了双腿。着实因为被绊了一跤,才发觉是个男人。
他胸口叉了一把刀,与我原来胸口叉的,一模一样。
我甩了背篓,换而背起了他。
幸好有一破庙,我日常找蛊虫歇脚的地方。
我将他背到破庙。一手按着胸口,一手利落地将刀拔了出来。
血溅进了我的眼,我也只是平静地擦掉。
流得多了,就不怕了。
我将他安置在破庙中,每晚给他扔些吃食。
接连找了半个多月,达奚才勉强在匣子里挑出一只乌青的甲虫。
她刮开我腕间的皮肉,让血滴了上去。
再教了我一段咒语,告诉我每日傍晚用猪油喂养,每三日滴一次血,如此九个轮回便成了。
除了吃食,我没给过瞎子一根草药,他的伤口愈合得很慢。
不过渐渐清醒的时候多了,也能与我说一说话。
「你叫什么?」
「没有名字。」
「那你来自何处?」
他沉默了片刻:
「不知来处,不明归路。」
我比他好一点,至少,知道要让那些骗我的,伤我的人付出代价。
我递到他嘴边一瓣橘子,他微微皱眉之后,还是吞下去了。
「酸吗?」
他点点头。
「那你记住,人生比这还要酸,往后再也没有甜的日子了。」
「人活着总要有名字的,就叫岁寒吧!」
我拍了拍手,起身走了。
那瓣橘子里,我下了蛊。
看他的身板,应是练武之人。一是为了试试我的蛊术练得如何,二是控制他为我做些事情。
我盘腿坐在床上,念着咒语,感觉到了岁寒的痛楚,我想,成了。
在秦妈妈的调教下,我媚眼如丝,身若凌波,脱胎成了勾人摄魄的尤物。
她早已散出各路拜帖,在中秋夜为我办一场盛大的见面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