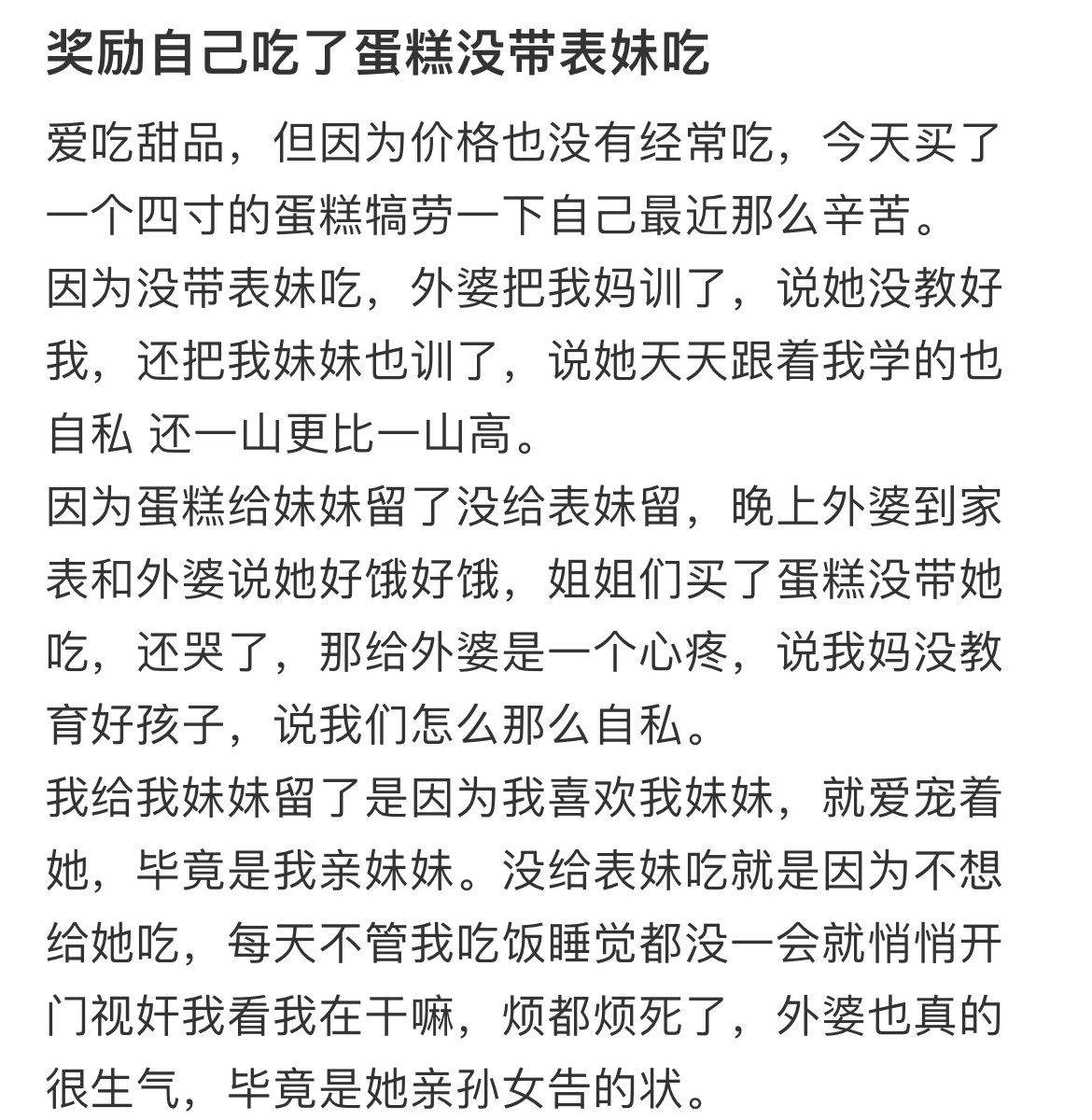▾ 敬请聆听 ▾


散文:飘香的红薯
文:老 愚
红薯,这一看似平凡的作物,却在我心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不仅是我童年回忆中的一抹亮色,更是岁月流转中的一味甘甜。
尽管现在还是春天,我家的饭桌上还是少不了红薯。把切块的红薯蒸在米饭上,饭熟了,红薯块那种甜香直往钻入鼻子里钻,于是人就有了旺盛的食欲。
记得那年,秋风乍起,天气渐凉。我在黄石街头漫步,一阵熟悉的醇香,从小巷飘出。我不由大叫:“烤红薯!”往那边巷道望去,果然有一烤红薯的铁烤炉,一老摊主悠然自得守在炉边。妻子不以为然,她说,这时节,卖红薯的多的是。可不?在我居住的小城铁山,也有这样铁烤炉,也有类似的老人做这样的小买卖。经受不住红薯的浓香的诱惑,我们拿上4个,一称,居然两斤有余。付帐,趁热吃,那甜甜的暖暖的滋味在口颊间散开,这就是一种家常的幸福。
每年每月,我家其实总会有些红薯。离现在间隔早些的往年,主要是乡下亲戚送来的。后来,这些亲戚进城或打工,或做小买卖,田地自然就撂荒了。于是,我们便买,较之以前,这些在乡下低贱得用来喂猪的红薯近年价位一直上涨,如同股票进入牛市,眼下应该两元一斤了。但是,这是早年就习惯了的食物,属于粗粮之列。现在吃粗粮倒成了一种讲究养生学问的时尚、幸福。刨皮,剁块,丢在米中,一起在电饭煲里煮。饭就粘上了特别的苕香,而那块状的红薯们更是成了家人眼里的美味。

小的时候,我在山村长大。当时,村里人似乎一年到头都在吃苕:煮苕丝、苕片,闷干苕……以至于那时流传一种说法:早晨三碗苕,正午苕三碗,傍晚苕过夜(“过夜”就是吃晚饭)。特别是冬末春初,在靠向阳的老屋墙下,一群老小每人满满的一碗苕,有的就着咸菜“呼哧呼哧”地吃,有的什么菜也没有“呼哧呼哧”地吃,这时有的老人会说:什么时候能天天吃白米饭就好了。那时,农民判断某家生活滋润不滋润的标准很简单,能吃白米饭就是最大的幸福。甚至有这样的段子:在北京,中央首长早晨肯定是吃油盐炒饭。
栽种红薯的季节,在四月末,阴雨天最好,种好苕种,生出苕藤。得及时栽好,浇水,忙完这些,它就“苕”长,看了叫人就喜欢。儿时,红薯是家乡地头最高产的作物。每到深秋,乡亲们会扛起锄头,走向那片片红薯地。阳光洒落,红薯叶随风摇曳,仿佛在低语。他们用力挖开泥土,一个个饱满的红薯便露出头来,它们有的长,有的圆,有的还沾着泥土,仿佛是大地淘气的孩子。春华秋实,也许就缘于这样类似的劳动场景吧!

那些年,乡下最多的粮食就是红薯,人吃不完,猪吃;猪吃不完,丢在苕窖里。每年夏季,红薯总要烂掉一些。当年,在大冶乡下,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的苕窖,两米多深,有一木梯供人上下,顶上盖了厚实平整的两块长方形大小一般的石板。现在,农民也种红薯,只是做杂粮,产量少多了,那外观不雅的苕窖派不上用场,如今应该文物一样稀罕。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红薯让当地的农民度过了饥荒,但吃多了胀气难受,所以上了点年纪的老人对吃红薯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现在,老辈人吃红薯则有怀念和回味的意味。而城里的小孩子爱吃烤红薯,一是图新鲜,二是如今的红薯品种优良、香甜可口。教之原先,现在的红薯仿佛人造美女,品起来味道的确比过去强了许多。
红薯的吃法多种多样。可以洗净后直接放入灶火中烤,那种焦香令人回味无穷;也可以切块煮粥,甜润的红薯与米香交融,温暖了整个假日;或者切片晒干炒熟,成为冬天里难得的家常小吃。
喷香的红薯,总能让我想起当年农民们对丰收的期盼和感恩;喷香的红薯,也如眼下简单而纯粹的口腹满足,温暖而持久。红薯飘香,让我沉醉,如同遥远的孩童时代山村生活场景幕幕在眼前中展现,韵味绵长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