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一篇文字,一位署名曹和平的北大教授,改了改胡适的第一篇白话诗,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1篇白话诗《两只蝴蝶》。
胡适的原诗是: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曹氏改诗的最终稿是:
两只蝴蝶上青天,
一黄落翅意阑珊。
何事扶摇说不成,
落向花丛却释然?

虽然这是他文中改诗的最终定稿,但显然这首诗改的并不怎么高明,而且这位教授自己对这首改定的诗也不十分满意,无奈的是,这一稿已经达到了他能力的最高水平,不说黔驴技穷,也是江郎才尽所以也只好写到这里。
然后他通过将自己的诗与胡适的诗相对比,胡适不应该被称为白话诗的开山之祖。他的原话是:
改到这,也算脑力一操,已抵本木讷的知识智力上限了。操毕,至少知胡不应是白话诗开山成派之祖一矣。
笔者不知道曹氏是从哪个维度认为自己这首改诗,比胡适的更好。

从审美上来说,胡适的诗不具有审美性,曹氏改来改去,最终定稿也是落于窠臼,显得俗套;从意蕴上说,我不知道曹氏写这首诗,是为改而改,还是情之所至,略动古人笔墨。
至少胡适是有真情在的,一是因为他提倡白话文无人理解,二是用外国女友远去他乡。
文章合时,诗歌合事,才有自己的意义。
从历史意义上来说,胡适的《两个蝴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第1篇白话诗歌,它的文学史意义和诗歌史意义,远大于它的文学价值和诗歌价值,这是治现代文学史的人都承认的。
至少在文学史上,没有谁说,胡适的诗好,是好在它的审美价值。
略微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明白胡适从来都不是一个诗人,他也从来都没有把作诗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就连文学,在胡适手里也只是开启明智的一个工具。
当年在胡适与鲁迅先生关系最好的时候,鲁迅先生曾劝他多写文学作品,胡适先是答应了,但最后还是没有走到专门创作文学这条路上。他想要做的只是开风气而已。
中国的新诗,也就是白话诗,始于胡适,奠基于郭沫若、闻一多,成熟于戴望舒。

这是连建国之后最主要的论敌郭沫若都承认的。胡、郭关系不和谐最根本处有一点就是胡适和郭沫若,谁应当坐“中国新诗的第一把交椅”。
曹和平地改诗,自以为高明,实际上不过是于贻笑于众。
黄庭坚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格始逼真。无论如何,胡适是开风气者,他创造了中国新诗体,至于后面尾随着改诗的只能是:
借前人“合时合事”之酒杯,浇自己“不痛不痒”之块垒。
杜牧《阿房宫赋》的最后总结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笔者认为曹氏改胡适之诗,是:
其人不暇自羞,而旁人羞之,旁人羞之而不鉴之,亦使旁人复羞旁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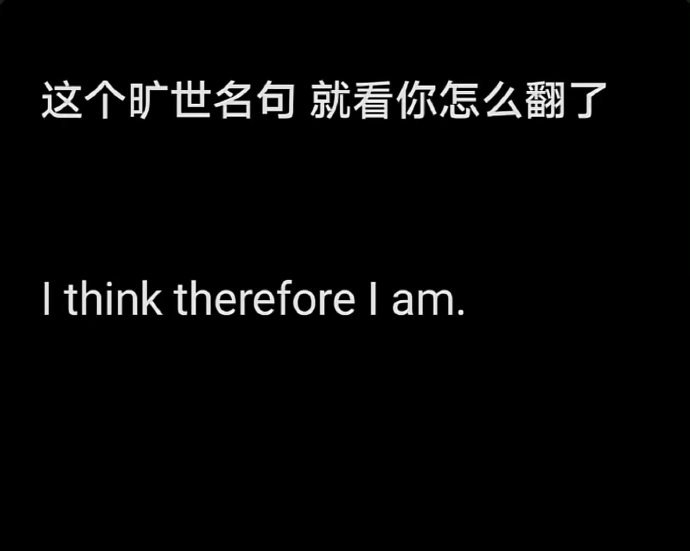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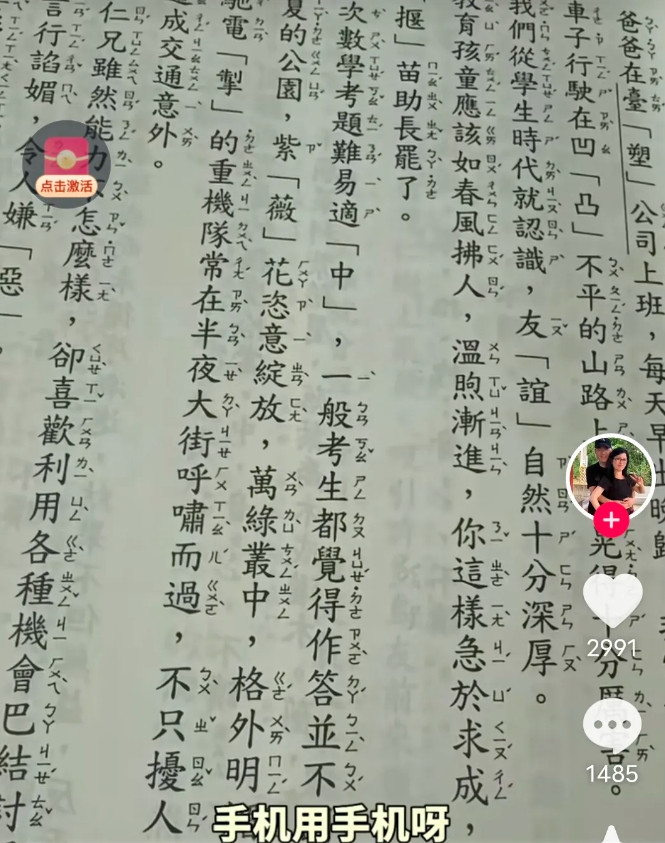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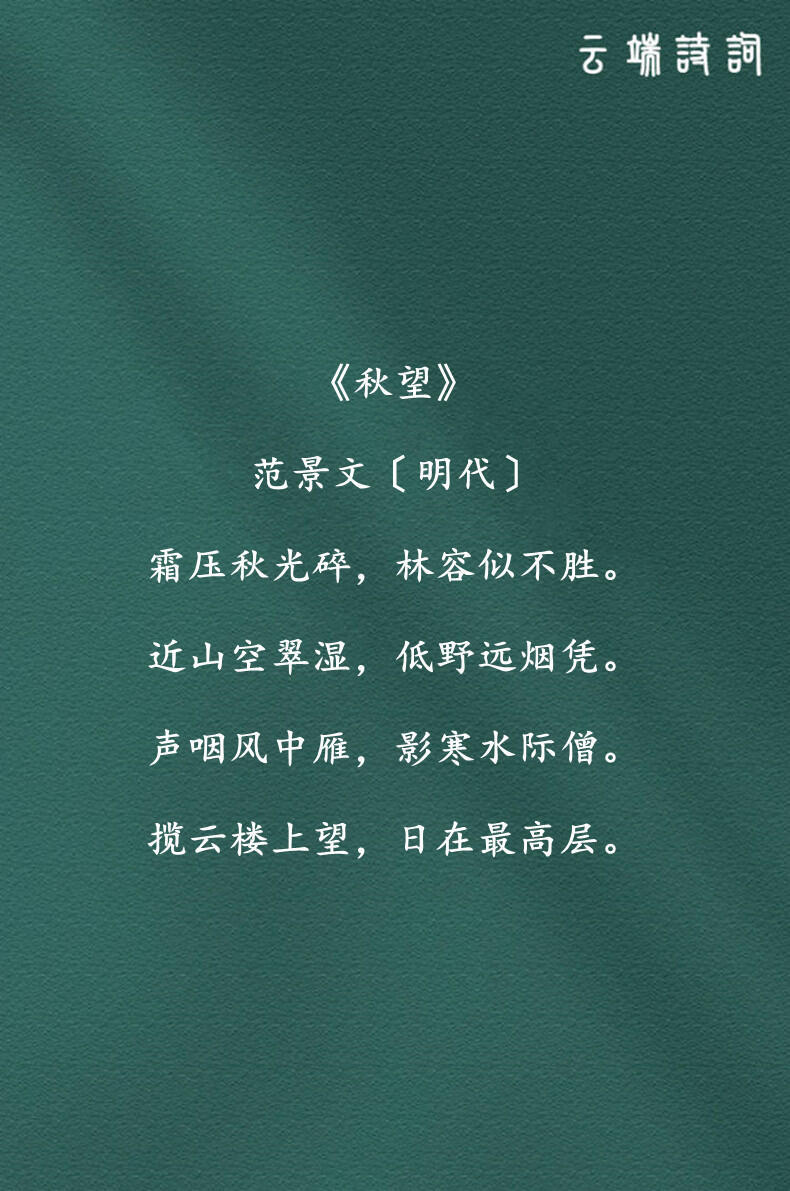




你TM真没脸!
胡适之是最早的矮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