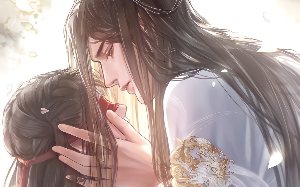1
我自幼就定了和祁墨的婚事。
拜堂那一年,我19岁。
祁墨16岁。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
可普罗大众适用的这句却独独漏了我。
不过无所谓,我本身就是金砖。
洞房花烛夜当晚,祁墨一袭红衣站在房门,满眼冷漠:
“你别以为和我成婚我就会高看你一眼。”
“恶毒的女人。”
随后不顾我的脸面,踏出婚房。
整晚照顾发了喘症的柔弱舞姬。
第二天,我成了整个京城的笑话。
......
我和祁墨拜堂成婚已有五载,今日便是当日时。
我一大早就起床跑去厨房亲手为我们做两碗面。
寓意我们的婚姻幸福长久。
端着两碗面来时,祁墨刚坐下。
瞥了一眼我手上的东西,眼神依旧冷淡。
“你不必亲手做面条,让下人来就好了。”
“太麻烦。”
我摇了摇头,“今天是我们结婚的第五周年。”
祁墨愣了一下,眼底闪过意味不明的情绪。
仍是一副冰山脸,但语气温和了些。
“辛苦了。”
放下其中一碗面,将另一碗端过给祁墨。
手腕相触的瞬间,林婉的侍女突然冲进来对着祁墨跪下。
“公子,小姐她喘症又犯了。”
“大夫说十分凶险,您快去看看她吧。”
祁墨伸出一半的手下意识收回半寸,而我恰好手抖松手。
碗碎了。
地上满是散落的面条,一片狰狞。
我看向祁墨。
祁墨眉头紧皱,眼底弥漫着焦躁,带着上位者的怒气。
“你是怎么照顾婉婉的。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我唯你是问。”
祁墨三步并作两步跑了出去。
林婉那个侍女临走前得意地看了我一眼,匆匆去追祁墨了。
唯余一片狼藉。
原来冷淡的人从来不是真的冷淡,只是他没有遇到真正让他在意的人。
刚才离得太近,砸碎的碗片隔着衣裙划破了我的小腿。
鞋上粘了滚烫的面条,脚下一片泥泞。
可他却丝毫没注意到我的狼狈。
我被浇了个透心凉。
我后退一步,摇头苦笑。
这便是我放在心上的人吗?连个念想都不肯给我。
罢了。
原来攒够了失望的人是再不会抱有任何希望的。
林婉,是祁墨的心上人。
我和她之间,我永远是被抛下的那个。
林婉本是青楼里的一名舞姬。
祁墨出门拜访我爹时,恰巧遇到犯了喘症的林婉。
出于热心救下了林婉,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馆。
林婉醒来后两眼含情水汪汪地靠着祁墨。
“君英姿雄伟,气度非凡。小女子无以为报,只得来世做牛做马以报君恩。”
得知林婉藏父卖身入青楼后,祁墨心软替她赎了身,安排了住处。
林婉美貌动人,温柔小意,却又不失坚韧顽强 。
是男人们都喜欢的类型。
借着救命之恩的由头三番两次找祁墨,同他谈星星说月亮。
一来二去两人接触日渐增多,情愫暗生。
彼时我跟祁墨的婚事已经准备到最后时刻。
若是退婚,两家必然遭到全京城的嘲笑。
尤其是我家。
世人不会推究是哪方过错,他们只会把女人放在火架上烤。
恨不得永世不得翻身。
我自然我所谓。
只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祁墨来找我商量退婚时,我正在房内绣婚服。
他真情实意地表达他与林婉的两情相悦,希望我主动退婚。
针刺破我的食指,滴圆的鲜血浸入大红的嫁衣中。
似乎未曾污染。
但脏了。
我沉默了片刻。
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由拒绝了他。
他沉下目光,冷淡地看了我一眼,留下一句“好自为之”径直走了。
祁墨说不想因他这边退婚让林婉遭人诟病,想让她清清白白地成为他的妻子。
可是他又是否在意,若是我主动退婚,我将遭受比林婉多十倍的流言蜚语。
他明明知道,我钦慕他已久。
这次的婚事是我强求来的。
2
我坐在床头把和离书递给祁墨,看清眼前几个大字后祁墨眼底闪过一瞬恐惧。
随后眉头紧皱,眼神怀疑:“盛柔,你又想耍什么诡计?”
“你不会是欲擒故纵,逼我离开婉婉吧?”
看啊,婉婉叫得多么亲密,却从来只肯指名道姓地叫我盛柔。
祁墨不相信我是真的想和离了,他只觉得我是在胡搅蛮缠。
他把合离书撕了,敛眉不悦地开口:“你在闹什么?”
“我不是已经听你的,没把婉婉安排进府吗?”
“多亏婉婉善解人意,体谅你,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你的正妻当得好好的?”
我气笑了。
林婉不进府是公爹的意思。
他觉得舞姬入府污了祁家清贵的门楣,发话说绝不许林婉入府。
眼下祁墨这是把责任推到我头上了。
我垂下眼眸,不愿与他辩解。
“随你怎么想吧,这和离书我是签定了。”
“你撕了一张,还会有第二张。”
“你就装吧,我不信你不知道和离的后果。”
“你怎么离得开我?”
祁墨信誓旦旦。
我当然知道。
黎国律法规定,女子主动提出和离,需受夹刑,并处白银千两罚锾。
我家是黎国最有钱的富商,区区千两自然不算什么。
只是除了夹刑,女子和离还要遭受数不尽的流言蜚语。
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
人要及时止损。
我语气不耐:“你要是不签的话,别怪我杀了林婉。”
“你敢?”
“你说呢?我家有的是钱。”
被我这么一激,祁墨跑去书房,亲自写了张合离书。
等第二天我家的马车一来,我立刻出府。
我的东西一样没拿。
他祁墨不是要娶林婉吗?
等她入府看到满院我的物件时,一定膈应得心绞痛吧。
祁墨站在府门脸色阴沉,活像我做了什么亏心事。
拦住我沉声道:“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诡计,但你要是出了这个门就别想再回来了。”
“婉婉我也会把她娶入府中,立为正妻。”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他站在我面前,一脸自信。
他在等我的道歉和我真情实感的爱意。
果然在最不爱一个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愚蠢。
我冷笑了一声,为我自己白白地付出而感到可笑。
哪怕我要走了,他依旧觉得我在无理取闹。
“不用了,绿茶配软饭,渣男配贱女。”
“你俩一辈子锁死吧。”
祁墨站在大门外目光沉沉地看我的马车走远,眼神意味不明。
“怎么了。”
明明未至府门,车夫却停下了。
“有个浑身是血的人躺在路间。”
我来了兴趣,闲着也是无聊,走到男人跟前。
倒是个长得标致的。
男人唇红齿白,容貌迤逦,脸上溅的几滴血倒是平添了几分妖艳。
我淡淡地看了一眼,便收回了视线。
我可没有多管闲事的善良美德。
径直略过他,朝外走去。
“救我。”
男人倔强脆弱的眼神直勾勾盯着我,像一只虎视眈眈的狼。
倒是激起我的兴趣。
我饶有意味地看向他:
“我救了你我能得到什么呢?”
我蹲下,指尖轻划过他的脸颊,不经意间为他拭去了眼角的血。
“愿听主人安排。”
3
“那我要是让你做我的面首你可愿意?”
黎国民风封建,好人家的男儿以伺候女子为耻辱。
只有家境贫寒或犯了事的人才不得不去当小倌。
眼前这个男人不仅长相对我胃口,更重要的是,他有武功。
而且还不低。
“三生有幸。”
不出意料地答应了。
我嘴角勾起,笑容轻快。
“阿柔,你是在开玩笑吗?”
“好端端地怎么和离了。”
爹和兄长对我合离的事实不解。
“就是发现不爱了。”
爹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他比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当初我对这桩婚事是有多么欢喜的。
最终他什么也没说。
沉沉叹了口气,“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妹妹,我给你介绍几个有趣的小倌,保准比祁墨更倜傥更好。”
“爹,不如我明天就陪妹妹出去玩个几天。”
兄长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
“去你的,你妹刚回家你就想撂挑子。”
我爹毫不留情直接踹了兄长一脚,怒目圆睁。
我带男人回家的事情当晚就被发现了。
我被迫迎着两道意味深长的视线。
“柔儿,你这是看上人家,把人家强抢来做我家的女婿吗?”
我揉了揉额头,刚要回答。
“我喜欢。这可比那个祁墨好一百倍。”
我爹一阵猥琐的笑声持续传来,仿佛能想象到外孙女的样子了。
“爹,你收敛一下,下着妹妹了。”
总算有个正常人了。
下一秒。
“妹妹,你们几时拜堂?兄长我好为你们准备嫁妆。”
我将他们都轰走了,径直走回房间。
打开床帐,里面躺着一个赤身男人。
男人身穿轻纱,花瓣好巧不巧盖住重点部位。
身上虽然缠着纱布,却平添几分脆弱的意味。
欲拒还迎。
勾起人心底里最大的恶意。
我没给他盖上被子,站在原地也没走。
“看来伤得不重,才被救回来就有力气了。”
我放下床帘,弯腰贴近他。
“为主人报恩,心甘情愿。”
男人红唇轻起,荡漾地笑着。
“是吗?今天你的出现怕不是刻意的?”
我的手覆上男人的胸肌,隔着轻纱。
不料男人趁机一把将我拽住,拉了上来。
两具身体面对面紧紧地贴住,严丝合缝。
“如果说我是为主人你而来的,你信吗?”
男人贴着我的耳朵吐气如兰。
我勾唇轻笑。
覆在胸肌上的手轻轻捏住某个红点。
男人身体一僵,呼吸逐渐沉重。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你在我身边半年,作为回报,我不问你的来历和去向,我的人脉你随意。”
“但你要向我保证,绝不会做出伤害我盛家的事。”
“主人你这么说奴家可要伤心了。”
男人眨着水润的眼睛无辜地看着我。
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我知道他已经答应了。
正事完成,也没有待着的必要了。
我撑起身,准备洗漱就寝。
男人却一手揽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把我贴得更紧。
“主人别急,正事还没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