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切掉阑尾,摘掉扁桃体,拔光满口牙齿。 她说:我要把身体上所有能引发炎症、影响我肝病研究的器官全部清除! 1972年那会儿,咱们47岁的陈菊梅女士,那是真豁得出去,做了个让旁人都觉得“哇塞”的决定:她要把阑尾给咔嚓了,扁桃体也给摘了,连满口的牙齿都不放过,一颗不留全拔掉。她老人家说了:“我这身子骨,凡是能扯上发炎、能耽误我研究肝病的零件,统统得清理出门户!” 你说那时候的中国,嘿,正处于一个挺微妙的当口。国家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政治动荡、社会变革那是接连不断,医疗条件呢,就跟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似的,啥都不齐全,科研环境更是简陋得跟个茅草屋似的。可就算是这样,咱们的那些科学家和大夫们,愣是咬紧了牙关,死守着他们的岗位,为了国家的明天,那是默默地搬砖加瓦。 鲁迅大爷有句话说得好:“希望这玩意儿,你说它有它就有,你说它没它就没,跟地上的路一样。本来地上啥路都没有,可走的人一多,嘿,路就这么踩出来了。”在那个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是咋样的年代,每往前挪动一小步,那都是金子般的珍贵啊。陈菊梅,这位看似平凡的女大夫,47岁那年,忽然玩了一把“人生大冒险”。她不光是治病救人的能手,还是个爱探险的医学狂人。她的这一步,可不是简单的“我爱运动”那么简单,这是为了她心心念念的医学事业豁出去了。在那个难题一堆的年代,她愣是用自己的胆识和决心,给“医者仁心”这个词加了个生动的注脚。都说“英雄为懂他的人献身,鸟儿以翅膀为贵”,陈菊梅这一下子,就是为了那些她视作知音的病人,为了那些等着她伸援手的人们。 时间回到1972年,陈菊梅站在医院的长廊,眼神里透着股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儿。47岁,按说该是享受成果的年纪,可她却因为常年累月的忙碌,把自己折腾得有点“摇摇欲坠”。但你猜怎么着?她心里那团对医学研究的火,愣是越烧越旺。她心里明镜似的,自己搞的肝病研究,那是好多人的“生命线”。张医生劝了她好几次,让她悠着点,她却摆摆手:“老张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这条命要是能帮医学往前挪一小步,那也值了。”“陈教授啊,您这身子骨儿,简直是风一吹就能倒,这时候还硬上,风险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张医生那嗓子,颤得跟秋叶儿似的,他心里跟明镜儿一样,清楚陈菊梅这一出是玩儿命的活儿。 “我心里有数,但这步棋,非走不可。”陈菊梅眼里那股子倔劲儿,跟钻了火苗子似的,“咱们这课题,等米下锅呢,我这把老骨头,豁出去了也得给它啃下来,身上的那些‘不定时炸弹’,得一一给摘了。” 手术室里头,灯光昏黄得跟老照片似的,空气里那股子消毒水的味儿,冲得鼻子直痒痒。陈菊梅往手术台上一躺,心里头倒是跟没事人似的。她这脑袋瓜子,开始过电影了——小时候那梦想,跟念经似的在耳边回响:“长大了,我要当医生,治病救人。”那会儿的她,书不离手,成绩好得跟吃了秤砣似的沉,满心满眼都是对医学的痴迷。瞧瞧现在,国内肝病界的大腕儿,头衔响当当的,可那颗心,还跟刚学医那会儿一样热乎。手术的大幕一拉开,那场面,简直是步步惊心。阑尾一刀两断,扁桃体说声拜拜,满口牙齿也来个集体离职。每一刀下去,都像是在她心头刻字,那滋味,啧啧,可不是盖的。但咱们的陈菊梅女士,那可是铁了心,咬咬牙,愣是一声没吭。为啥?还不是为了那些眼巴巴等着救命的病号嘛。 手术一完事儿,陈菊梅整个人跟被秋风扫过似的,弱不禁风。可你瞧她那眼神,嘿,跟打了鸡血似的,倍儿亮!她一股脑儿扎进实验室,跟研究较上了劲儿。她琢磨出的“鞘内注射法”,那可是医学界的一大响炮,给多少肝病患者送去了温暖的小太阳。 夜深人静时,她还爱自言自语:“眼瞅着病人受罪,咱心里能是个滋味?得嘞,得赶紧把这病给治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陈菊梅手里的“肝得安”横空出世,临床试验一出来,效果杠杠的,肝病患者们那是奔走相告,重获新生啊!这下子,陈菊梅的大名算是刻在了医学的丰碑上,成了医学生们嘴里念叨、心里崇拜的偶像。“肝得安”,这玩意儿可不简单,它不光是药匣子里的一味药,更是心头的一盏明灯,照亮的是医者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它告诉你,啥叫对生命的顶格尊重和敬畏。陈菊梅老医生常开腔:“咱干这行的,救死扶伤不就是分内事儿嘛!”这话,听着朴素,却像一把小锤子,不光敲打着她自个儿的心鼓,也震得咱这些同行心里头直痒痒,琢磨着怎么也得对得起这身白大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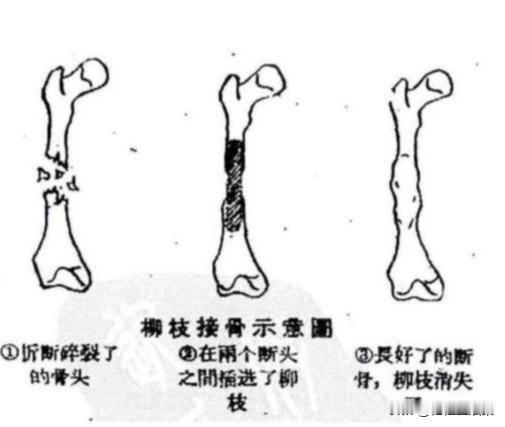



肝炎,肺炎,心肌炎,肠炎,胃炎等等,是不是都拿掉
信商医,得永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