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工作人数美国:5464,位列第一。法国:4398,位列第二。肯尼亚:3660,位列第三。 在联合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多边组织中,各国人员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状态。根据最新统计数据,美国以5464人位列第一,法国以4398人位列第二,而令人意外的是,肯尼亚以3660人位居第三。 这种国别分布也反映了联合国长期以来在人员招聘上的地域偏好。传统西方大国在高级职位上占据优势,而非洲国家则在中低级职位上数量可观。 联合国的职员体系主要分为三个类别:D类、P类和G类。D类是领导职务,主要是各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P类是专业人员,构成联合国工作的主体;G类则是一般事务性职位,多从当地招聘。 这三级职员体系在招聘机制上存在明显差异。D类职位除了内部晋升外,很大一部分来自各国直接派遣,因此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P类职位则主要通过YPP考试等公开渠道招聘,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发达国家候选人占优的现象。G类职位由于主要从驻在国招聘。 联合国虽然倡导"地域公平原则",希望职员构成能反映全球193个会员国的公平代表性,但实际运作中与这一原则仍有较大差距,许多国家面临"任职人数不足"的问题。 中国作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对联合国预算的贡献达到12%,但中国在联合国的职员仅占总数的1.2%,人员数量与会费贡献比例严重不匹配。 相比之下,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则表现出较好的匹配度。美国作为最大会费国,同时也保持着最多的联合国职员数量。法国则通过长期的战略规划和人才培养,确保了其在联合国系统中的人员优势。 不同国家在培养国际组织人才方面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战略。美国的"世界事务委员会模式"构建了从大学到联合国的人才输送管道,通过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实习项目和专门的培训机构为美国学生进入联合国提供了系统支持。法国则依靠其精英教育体系,特别是国家行政学院培养适合国际组织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则充分利用其区域特色和英语优势,培养了大量适合联合国工作的人才。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和其他主要高校开设了专门针对国际组织的课程,并与联合国驻肯尼亚的机构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这使得肯尼亚成为非洲国家中向联合国输送人才最多的国家之一。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转折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逐步深化与联合国的关系,从初始阶段的适应参与,到如今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在人员代表性方面,中国自1972年起向联合国连续推送了9位副秘书长,他们分别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沙祖康、吴红波和刘振民,为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专门机构中的中国高级官员也逐渐增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冯富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贡献。2006年,作为香港特区卫生署原署长的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成为首位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担任最高职位的中国人,并于2012年成功连任。她在任十年间处理了多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包括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和2016年的寨卡疫情,展现了中国医疗卫生专业人才的国际影响力。 目前,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有3位行政首长来自中国,分别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和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此外,中国籍的刘振民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夏煌任联合国秘书长非洲大湖区特使,徐浩良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开发署亚太局局长。 尽管中国在联合国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但仍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从数据看,中国在联合国D类职务中仅有14人,排在第8位,远低于美国的43人、英国的18人和印度的15人。 更为突出的是人员总量与会费贡献的失衡问题。2019年中国对联合国会费的分摊比重达到12%,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费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成为第一大会费国。然而,中国在联合国雇员总数中的比例仅为1.2%,约550人,排在第17位。在国际维和领域,中国的维和摊款比例达15.21%,成为第一缴费大国,但人员参与度与此不成比例。 这种失衡导致了中国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受限,国际事务主导权难以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形象难以有效彰显,也使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面临着隐性制约。 面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巨大缺口,中国正在探索创新型培养模式。"政府引导+高校主体+企业参与"的三位一体培养机制已经初步形成。政府层面,中国留学基金委加大了对国际组织实习的资助力度;高校层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国际组织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也设立了相关项目;企业层面,一些有国际视野的企业也开始参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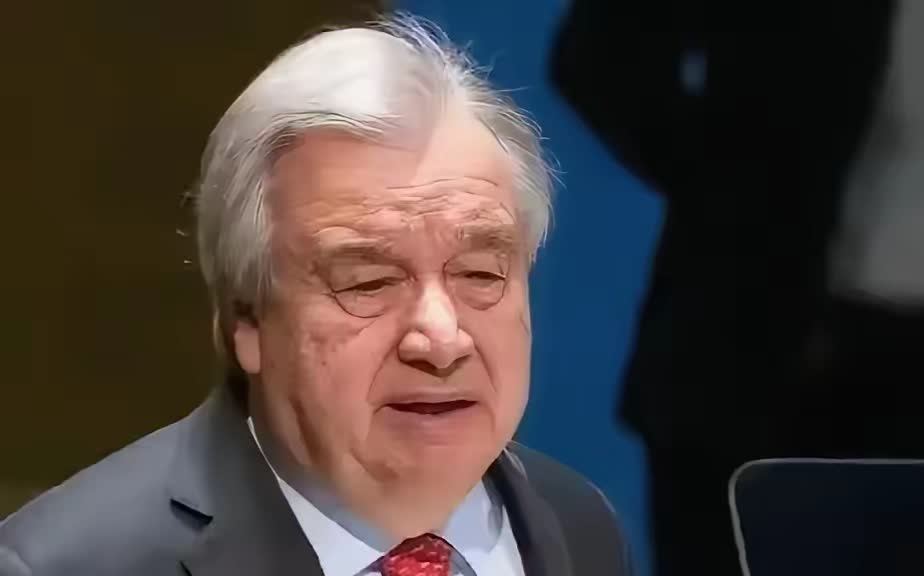







中国伟大复兴万岁
钱都流向美国,美帝还有什么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