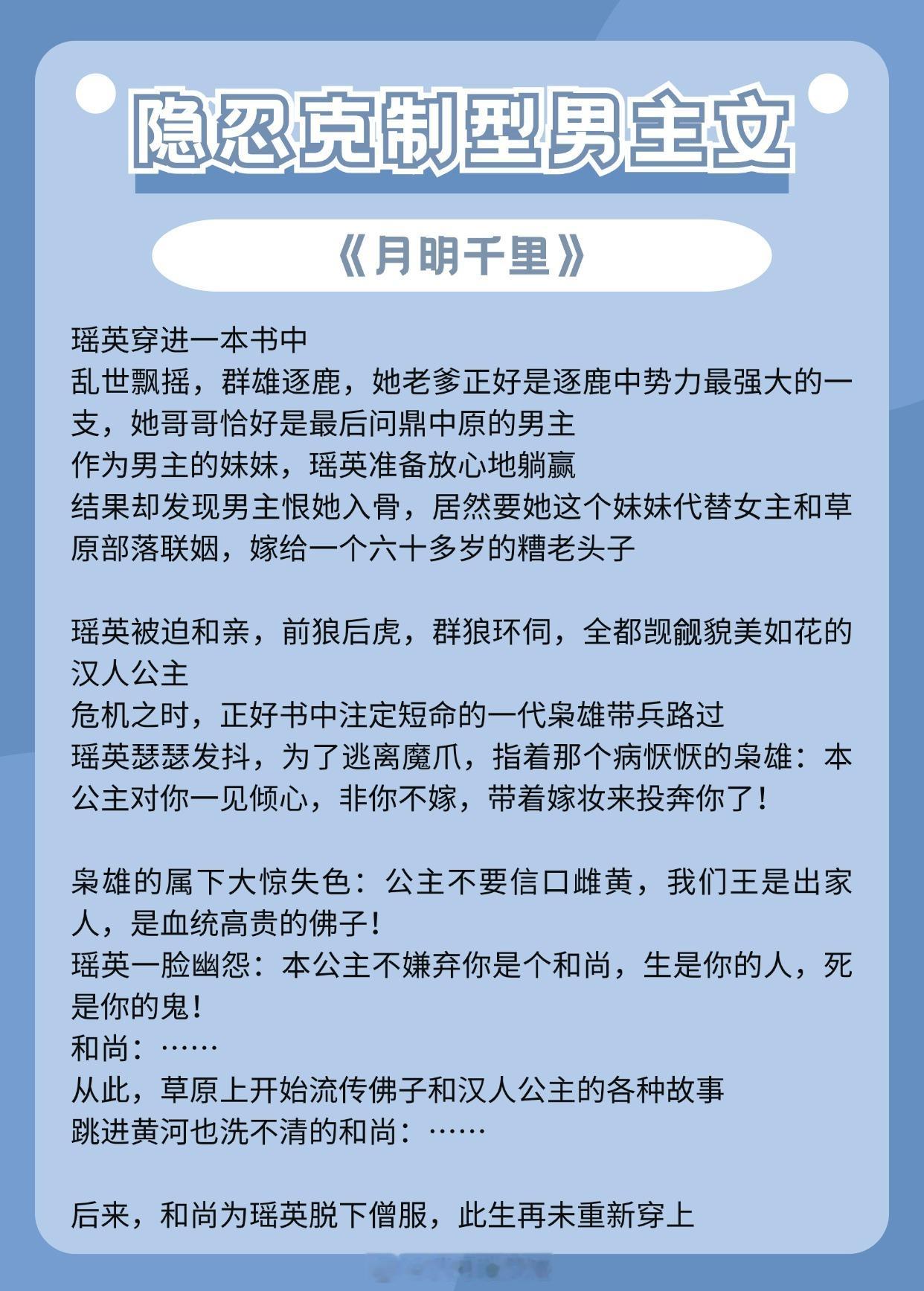再次见到谢晏宇,是我这个亡国女将,被人关进铁笼,受尽凌辱…
他一身染血重甲,自黑暗中踏步而来,阻止了这场闹剧。
可殊不知,我见了他,才是真正的肝胆俱裂。
果然回到牙账,他便用剑锋划过我破碎的衣衫
恨毒了般咬紧我耳垂低吼,“湛清,你为了那暴君抛弃我!可曾想会有今日?”

天启三十六年,大燕都城被北人攻破,我作为守城女将,殉国不成,被生擒。
当晚,打了胜仗的北国士兵将我从囚车中提出,卸了战袍,摁倒在篝火前的草地上。
“瞧瞧,这就是大燕国的女将军!真稀罕,女人也能带兵?大燕男儿都死绝了不成?”
“哈哈哈,自然是死绝了,派个女人来守城,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让她抬起头来!”
“对,抬起来!兄弟们好久见不着女人了,看不到脸,这接下来的戏没滋味啊。”
我被人揪着发髻抬起头,接着一桶凉水扑面而下,冲刷尽了我脸上血污,不干不净的一块帕子狠狠擦过,我听见周围发出阵阵倒吸。
“真有几分颜色,妈的!要不是军纪,还能便宜那畜生?”
“牵上来,快牵上来!老子等不及了。”
……
久在战场,人早已褪去人性,只剩兽性,对于当前发生的一切,我毫不意外,北人军中爱看人兽在笼中相斗,我亦有所耳闻。
我叫湛清,是大燕武将世家——湛家的女儿。
受父兄跟家族的影响与熏陶,我自幼习武,后来战事起,父兄接连战死沙场,朝中又无人可用,我便请缨担当守城的要职,大燕王同意,兼念我湛家满门忠烈,给了我将军头衔。
只可惜兵败如山倒,大燕早回天无力,最终也没能摆脱亡国的命运。
父亲曾告诫我,无国便无家,湛家儿女誓死不当亡国奴,所以当都城城门告破,我欲引剑自刎,可惜被手下叛徒拦下。
接着,便是当前的境况。
我在深秋的夜里,穿着一身湿透的单衣,忽而听见侧方传来几声猛兽的低呜,抬眼望去,那是一个巨大的精铁牢笼,由两匹战马合力牵引着。
就着面前冲腾的火焰,我看见那笼里关着的是一只双眼赤红、犬齿锋利、体格雄壮的巨狼!
我心惊地本能就要后退,可被身旁的人死死摁住,围着的一圈士兵笑得愈发得意下流,“哈哈哈哈,女将军,看见那畜生胯下了吗?你有过男人吗?今夜让你做新娘如何?”
“哈哈哈哈哈……”
我注意到了,那巨狼露出尖牙,眼神里透着鲜血般的猩红,它渴望着猎物。
他们要我扔进去,跟那畜生搏斗。
“……不,不要,放开!放开我!!!”
毕生没见过这种恶心下作的招数,我拼了命地抗拒挣扎,可寡不敌众,铁门在我面前掖开一条缝,又在我身后“珰”的一声上锁。
进了笼中,再哭嚎无用,我迅疾起身,闪避到牢笼角落,极力抑制住散乱的呼吸和颤抖,自袖中亮出一柄弯刀,与几步外拖着长长涎水的巨狼对视。
“她哪来的刀?”有人问。
押着过我来的男人在腰间摸了一空,“……”
巨狼的眼睛闪烁着凶煞的红光,散发着野兽特有的腥膻气,朝我走来。

这狼几乎跟我齐高,它的每一次扑绞都如笼在我头顶的死亡阴影,让我战栗不止。
但我不能接受像被一头畜生玩弄的另一头畜生那样死去,所以宁肯激怒它。
弯刀在闪避的分毫间刺入它皮肉,疼痛开始让它嘶嚎愤怒。我找准机会,在狼张嘴的千钧一发间,冒险将刀架在了它齿间,用力一错!立时有污黑的血喷溅而出,巨狼凄厉哀嚎。
好机会,我滚到一旁再补想刀,可弯刀拔不出来了!
巨狼调转身子,红着眼睛,低头隆背,散发着血腥的杀气,朝我高高跃起——
可我已经退无可退。
罢了,就这样吧,我闭上眼睛,至少死的干净利索。
可下一秒,我没有等来预想中的痛苦,反而是几支穿云箭的啸声,巨狼从空中重重砸落到地面,抽搐着死去。
“好热闹啊。”一句清冷的声音悠悠传来。
我骤然睁眼,猛地转头望向后方。
“殿下。”围观的士兵立刻起身噤声。
一个男人身穿染血重甲,拎着把弓箭,自黑暗中踏步而来。
“欺辱一女子,岂不有失我北国气度?”
男人对着下属说话,人却径直朝笼子走来,隔着几道铁栏,与满身肮脏血污的我对视,眼神坚冰般寒凉,又闪过一丝狠厉。
一瞬间,我浑身血液彷佛凝滞了一样,僵硬在原地。
谢晏宇……
“这女俘还有用,给她收拾干净,送到我牙账,我有话要问,立刻。”
冰凉的河水一桶接着一桶浇在我身上,冷冻刺骨,可我浑然无知,一遍遍回想男人刚刚的模样。
因为对他,我实在心有愧疚。
被捆缚着推搡进一幢白色牙账,谢晏宇已经脱去战袍,大马金刀地坐在一矮桌后擦长枪,头也不抬地挥手叫人退下。
“……晏宇。”隔着摇曳的烛火,他迟迟不说话,我只好先开了口。
他闻言抬起脸,先是沉默地盯了我片刻,然后讥讽地勾了勾唇角,“好久不见。”
“我当你披肝沥胆,为那大燕昏君,以死殉国了呢,那不是你湛家祖训?所以你怎么还活着?”
“……晏宇,时安……如今可好?”没理会他的嘲讽,我犹豫着向他问出我最关心的问题。
岂料,谢晏宇听了这话脸色骤变,提起长枪直直向我挑来,银光一闪而过,我衣不蔽体地被他抓着头发摁倒在虎皮榻上。
“你还有脸问我时安?!”谢晏宇口气凶狠,眼睛淬了毒一样,勃发着滔天的恨意和怒火。
“湛清,你为了那亡国之君,抛夫弃子,断情绝义!三年间,一丝音讯也无,前来刺杀夺人的暗卫倒是不少,如今死到临头,又想起你在这世上还有骨血了?”
什么刺杀?怎会了无音讯?我怎么听不懂了。
我挣扎着翻身,刚要开口,一根马鞭直接勒进我嘴里,上面马匹的血腥气呛得我眼泪直流,我昂头想要甩开,又被他一掌攥紧了喉咙。
谢晏宇压着我,动作粗暴无比,咬破了我的耳垂,但说出的话更令人绝望。
“时安很好,但我永远不会让你见他,更不会让他叫你一声娘亲。”

我和谢晏宇相遇相识在五年前的歌令山,彼时我们十七、八岁,正是鲜衣怒马少年时、意气风发。
我武艺半成后,便想随两个哥哥入伍参军,可遭到父亲严辞拒绝,“哪有女人当兵的?不许!”我一气之下换了男装出门游历。
路过歌令山,盘缠用光,恰时有个彩头不菲的擂台立在那儿,我不自量力地跳上台去,可男女天生力量有别,我被一看着清冷俊秀的年轻公子摁在地上打。
眼见挣脱不得,我情急之下抱着他胳膊咬了一口,年轻公子霎时愣住,盯着我有一瞬间的恍惚,我趁机翻身下台,也顾不得丢脸,骑马便逃。
可刚蹿出去没多远,我就感觉后面有人在追我,扭过头,还是刚刚那公子哥!
这人,我彩头都不要了,难道还要追着我打不成?
我犹豫着勒马停下,打算同他好好讲讲理,可这人开口的第一句便是,“姑娘,刚才我手重了,你没事儿吧?”
“!”
我倒吸了一口气,结巴着喝道,“你,你胡说什么?!”过了会儿,又实在有些好奇,心虚地小声接着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刚刚抱着我胳膊,你……我……”
话一出口,我俩同时有些红了脸,我嗫喏着说不出话。等回过神刚想羞恼地想骂他两句,少年却直接向我递来了那支作彩头的金簪。
暖风佛荡的夏日艳阳下,他望过来的眼睛载着柔光和笑意。
“我叫谢晏宇,敢问姑娘尊姓大名?”
帐中烛火发出“噼啪”爆破的声响,我从短暂的昏迷里睁开眼,猛地伏身呛咳、大口呼吸。
谢晏宇早松开了扼住我喉咙的手,但那窒息的感觉还在意识里残存。
他面无表情、眼神晦暗地翻身下榻,套上外袍,从桌上递来一杯凉透的茶水,我抖着手接过,喉咙火辣的痛感消退些许。
“刚刚有那么一瞬间,我是真的想掐死你。”谢晏宇突然看着我,失神般喃喃,“可那补偿不了我当年千分之一的痛苦。”
我狠狠闭了闭眼睛,回想当时,的确是我对不住他,“晏宇,是我欠你和时安的,我不想辩解什么,如今我已别无所求,只希望——”
可他忽然打断了我的自白,神色重新变换为阴沉冷漠,“湛清,我天启国对待女俘,有三条路,一是就地格杀,二是没入军中成为军妓,三是掳掠为奴,你想选哪一条?”
“……那还是杀了我吧。”
他冷笑了一声,“我为什么要让你如意?”
接着再次上前卡着我的喉咙把我提到他面前,面部因为咬牙切齿,都有些扭曲,“我偏要让你活着,痛苦不堪地活着,我替你选吧,第二条,怎么样?”
说着,他无视我的惊惧和挣扎,钳着我的胳膊将我从榻上拉下,尽管我不住哀求,可还是衣衫褴褛地被一路拖拽到帐门口。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脚步声,随即帐门被支起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