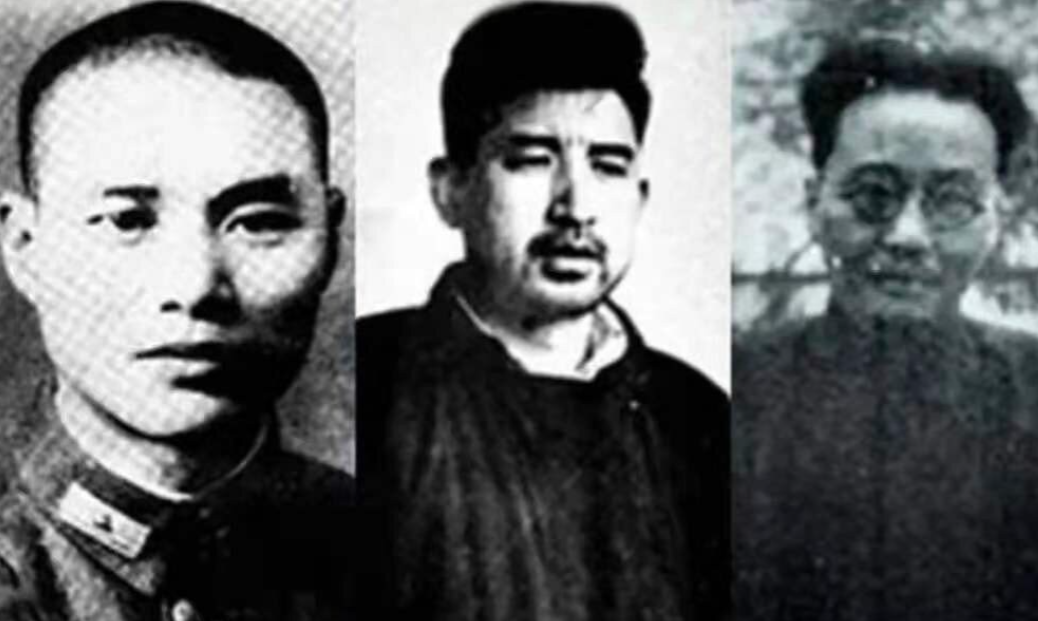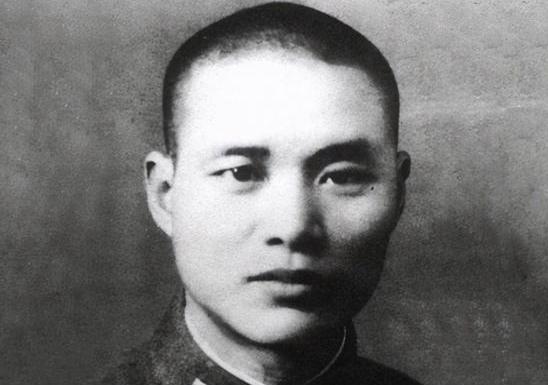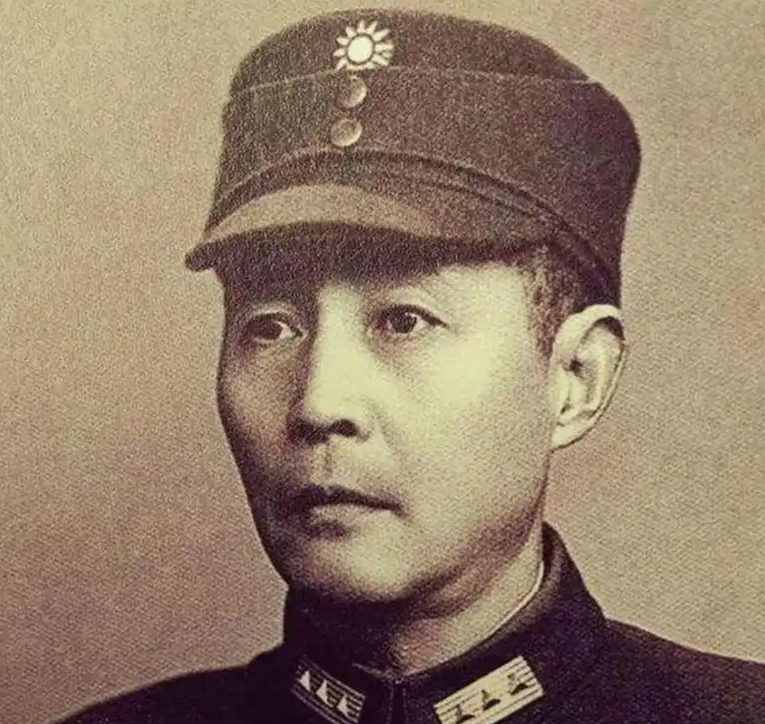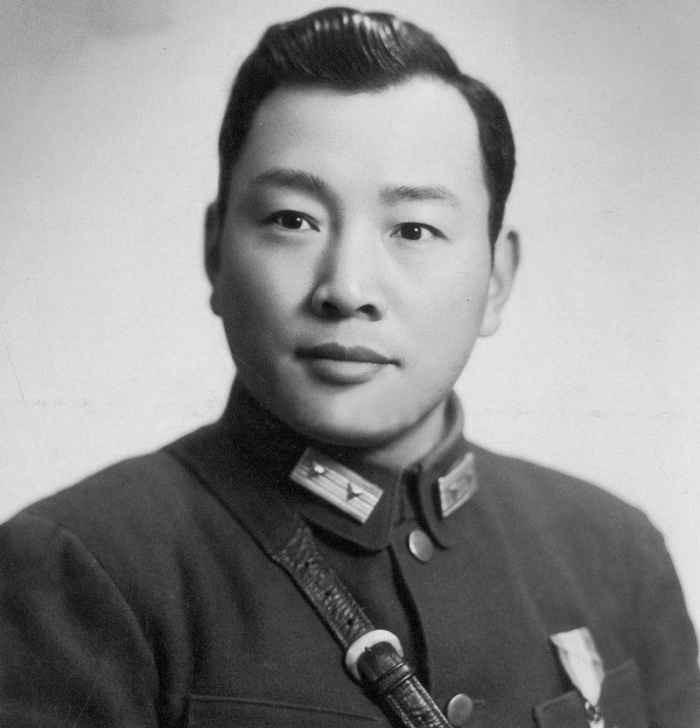1975年,大特务周养浩被特赦后想去台湾,正要动身,蒋介石却死了,蒋经国拒绝他到台湾来。周养浩滞留在香港,一时间竟不知去哪里。
沈醉、周养浩和徐远举,并称为 “军统三剑客”。但在改造期间,周养浩和徐远举却一度对沈醉心怀恶意,想要置他于死地。
有一次,徐远举突然抄起椅子,猛地朝着沈醉的脑袋砸去,一旁的宋希濂反应迅速、及时将椅子夺了下来,这才让沈醉躲过一劫。
倘若那椅子真的砸到沈醉头上,他就算不死也会落下残疾。要是那样,就不会有后来那部精彩纷呈的《沈醉回忆录》了。
周养浩虽然不像徐远举那样心狠手辣,但也曾有一次,将脸盆朝着沈醉扔过去,热水溅了沈醉一身。
后来,在管理所干部耐心的教育之下,周养浩和徐远举才终于收起了针对沈醉的心思。不过,平日里他们见面时,依旧是冷着脸,视若仇寇。
周养浩、徐远举和沈醉在军统共事的时候,关系其实不错,之所以会反目成仇,只有一个关键原因。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发动起义,将李弥、余程万、沈醉等蒋系的重要人员扣押。沈醉被抓之后,供出了周养浩和徐远举的住址。
彼时,徐远举作为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周养浩身为副区长,两人刚从成都乘飞机抵达昆明。他们住进了由沈醉安排好的住所,想着在昆明稍作休憩一两天,便转机前往台湾。
起义的第二天凌晨,周养浩还在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他起身去开门,门刚打开一条缝,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便猛地将门撞开,黑洞洞的枪口瞬间对准了他。
周养浩吃惊的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是不是抓错人了,我可是保密局的周养浩。”
带队的军官大声说:“抓的就是你,西南区副区长周养浩。”
周养浩一听,心里那个后悔啊,早知道编个假身份了。隔壁房间的徐远举,被抓的过程,和周养浩相仿。
眼看马上就能去台湾,和保密局长毛人凤会合,却因为被沈醉供出了藏身之地,成了阶下囚,周养浩和徐远举心中的愤怒与不甘,可想而知。
1960年,在功德林改造的沈醉,上了第二批特赦人员的名单,而周养浩、徐远举不在此列。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沈醉是军统元老,戴笠的亲信不假,但他担任的主要职务是总务处长,干的“脏活”不多,手上血债也较少,加上戴笠死后,沈醉在毛人凤排挤之下,被打发去云南当了站长;而周养浩、徐远举可称的上是血债累累,又是毛人凤的心腹。
二是,沈醉在改造期间,表现很好,加之在卢汉起义时,在起义通电上签字,虽然有被迫的成分,但多少也有态度在里面;反观周养浩、徐远举,改造期间属于和黄维一般的“刺头”,周养浩总是阴沉着脸,怪话连连,徐远举脾气暴躁,动辄和管理所的干部、改造的“同学”吵架。
1973年1月21日下午,在对战犯缝衣质量的检查中,徐远举同组的人批评他:“老徐,你看看这针脚,歪歪扭扭的,好多地方都没缝好,这扣子也钉得松松垮垮,根本不符合要求,得重新做。”
徐远举大声吼道:“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做这些本就不容易,你们还挑三拣四至于这么较真吗。”
徐远举越说越气,和同组的几人大吵了一通,第二天凌晨,他大喊头疼,痛苦不已,被管理干部送去北京复兴医院。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后,医生无奈地宣布:“抢救无效。”
徐远举这一死,让周养浩很是难受,因为在改造的战犯中,能和他说得来的,本来就没有几人。起初,周养浩以“顽固分子”自居,还想和另一个“顽固分子”黄维交朋友,不想黄维向来瞧不起军统特务,对周养浩一点好脸色都不给。
就在周养浩认为他要终老于监狱时,1975年,毛主席就战犯的问题,作了长篇批示,要求将所有在押战犯释放,在释放时举办欢送会,发放零用钱,对于年老体弱、身患疾病的,要给予精心治疗,要关心他们。
毛主席还明确批示,释放的战犯去留自由,他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有关部门应给予充分的协助。
大部分战犯都愿意留下,但还是有十人提出要去台湾,他们是:周养浩、王秉钺、王云沛、段克文、张铁石、陈士章、赵一雪、张海商、杨南邨、蔡省三。
人民政府尊重这十人的意愿,为他们办理赴港手续,还细心准备了适合香港气候的衣物和充足的费用,并安排香港的旅行社负责照顾他们在港期间的生活。
十人刚到香港,就传来了蒋介石病死的消息,他们想去吊唁,却被台湾方面告知“情况不明,暂不能来”。
十人又待了一段时间,发现台湾方面不仅没有接纳他们的意思,反而是戒心十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台当局见战犯们受到善待,被特赦,担心他们到台后说出真相,使得国民党在岛内民众面前失去 “颜面”。
在蒋经国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就公开说:“若此时接纳这十个人,无疑是自打脸,让我们陷入尴尬的境地。”
绝望的张铁石自杀在所住的酒店,周养浩等四人先后去了美国,张海商等三人返回大陆,蔡省三、王云沛留在了香港。
台当局的冷酷无情,让周养浩彻底寒心,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能和家人团聚,要感谢毛主席的伟大政策。”